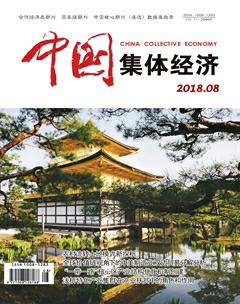農村流轉土地模式新探析
李嘉健 陳俊林 陳姿樺
摘要:文章分析歸納了“南海模式”的起源、演變及其固有缺陷。廣東珠三角地區創造出了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為基礎的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南海模式”,但存在外部制度環境的約束限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不夠完善等固有缺陷。提出了南海未來發展中必須解決好土地流轉與產業發展的關系、總體規劃與村民村集體的利益關系、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能否同等同權及村集體的組織管理職能與經濟發展職能能否有效分離等幾個關鍵問題。
關鍵詞:“南海模式”;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三舊”改造;“三塊地”改革
農村土地流轉是關系中國改革深化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構建農業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經營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保障。我國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以保護耕地、防止農民土地流失為基本出發點,改革開放前土地交易或流轉被嚴令嚴禁。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改革的深入,許多農村地區對土地流轉的需求不斷累積, 各地創造性地探索出了多種多樣的土地流轉模式,主要包括互換、出租、股份合作、入股、轉包等具體形式。本文針對廣東南海較有代表性的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為基礎的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模式展開研究。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在改革開放前是廣東省的一個縣,改革開放初期,南海大量鮮活水產品銷往香港,成為廣東的一個重要的出口創匯基地。1989年,南海農民開始將產出價值較低的農田改造為收益較高的魚塘,與全國普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同,南海實行的是基塘有償投包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以來,南海始終走在全國乃至廣東的前列。1992年,南海即創造出聞名全國的“南海模式”,在國家歷次農村土地改革試點地區名單上,南海均榜上有名。2015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區域,進行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改革試點,也被稱為農村“三塊地”改革,南海為廣東唯一試點地區。
南海作為經濟先發地區,在城市升級過程中,新型產業發展用地需求不斷增大,增量用地基本為零,盤活土地存量、孕育富有驅動力的新型產業發展模式成為“南海模式”新的突破方向。
國外大部分國家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化的土地管理制度,沒有土地產權流轉之說,只有土地產權交易的概念。科斯(1960)的研究認為土地產權是否清晰、完整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決定了土地交易成本的高低。Binswanger(1993)認為土地產權交易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土地資源開發投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周飛(2006)的研究發現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不夠完善,存在社會保障制度滯后、缺乏中介服務組織等問題。羅必良等(2008)認為土地流轉可以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支持農業規模化和集約化發展 。劉莉君、岳意定(2010)對多種土地流轉模式進行對比研究,發現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經濟績效最大。
一、“南海模式”的起源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南海走出了一條自發工業化、分散城市化的道路。伴隨著土地要素再配置和重組的工業化和城市化,1992年南海村集體將土地與資本結合,創造出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突破實現了集體土地進入建設用地市場,誕生了聞名全國的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南海模式”。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前提下,讓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進行流轉,所帶來的收益仍然保留在村集體內部,村集體成員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參與工業化和城市化,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當時,全國大范圍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同時擁有集體土地的使用權、支配權和收益權,集“三權”于一身。“南海模式”卻對集體土地實行“三權分離”,村集體通過土地股份合作組織擁有對土地的支配權,村民擁有收益權,對土地進行開發利用的投資者獲得使用權。
南海推行農村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做法是將土地折成股分,將股權按比例分配給村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仍然屬于村集體,由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統一經營,村民以股東身份獲取資產增值和盈利收益。通過引入外部資本或長期合作投資等方式對集體建設用地進行開發利用,具體有村集體自行開發經營、村集體以土地入股與投資者合資經營、村集體開發土地或轉讓部分土地獲取資金開發其余部分土地后出租或轉讓給投資者和村集體將未開發的土地長期出租給投資者進行開發利用等幾種形式。
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可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凸顯或提升了土地的市場價值,促進了當地的民營經濟發展,而民營經濟發展又為“南海模式”提供需求和支撐,目前南海90%以上的集體建設用地已經實現流轉,占農村集體土地的30%左右。
2000年之前,許多企業利用集體建設用地成本低、管制不嚴格、取得較為容易等特點迅速發展起來。2000年以后,珠三角地區出現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的趨勢,南海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產業高級化、城市都市化,導致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需求相對下降,也推動著“南海模式”發生轉變。
2007年,佛山市政府開始加快推進舊城鎮、舊廠房、舊村居的改造,南海先將原工業用地轉為商業服務用地,通過引入并借助社會資本、引進開發商或者向銀行融資進行“三舊”改造。南海通過集體建設用地轉為國有,以及政府長期租用集體土地的方式,來實現土地的集中和功能的調整。
20世紀90年代初, 農村土地由農業用地轉為集體建設用地導致集體土地制度的突破,這次通過土地國有促使土地集中,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土地價值,國有化成為此次變革主題。“南海模式”開始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通過參與土地國有化、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新的制度安排演變。
南海的土地國有化不是通過征地,而是集體建設用地轉為國有,土地使用權依然歸村集體,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相當大的比例屬于村集體,村民、村集體和政府共同受益,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依然存在,其經營的資產由集體所有土地變為國有土地。由此可見,土地使用權比土地所有權更加重要,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制度基礎和運營機制也隨之發生轉變。endprint
二、“南海模式”的固有缺陷及其演變
2000年以前,因集體建設用地成本低、管制不嚴、取得較為容易等原因, 珠三角地區承接了大量港臺轉移的低資本、低技術的產業形態,并形成集聚,迅速發展起來,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通過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進行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制度創新,即“南海模式”的出現。
在極大地促進了南海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南海模式”也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固有缺陷,這其中既有外部制度環境約束的因素,也有土地股份合作制內在的制度缺陷。傳統的“南海模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大量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粗放利用、分散、功能混雜、“碎片化”,企業檔次低、投資強度低、有大量高污染企業進入,土地開發檔次和建筑質量低下,公共基礎設施投入不足。
土地使用權的價值決定著土地的市場價格,開發商獲得的集體土地使用權是不完整的,大多數投資商是通過承租或投包的方式獲得土地使用權,承租期滿后,地上建筑物與土地一起被村集體收回。集體建設用地并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一樣做到同權同利,因而也不具有相同的開發利用價值,在流轉過程中就不能實現交易價值或村民村集體利益的最大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與國有土地不同,一旦發生爭議, 往往可能得不到現有法律有效保護,利用集體建設用地抵押融資也常常得不到金融機構的認可,集體所有性質的土地不能用于房地產項目的經營等,開發經營范圍常常受限。
農村土地股份合作體制也存在固有缺陷。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股權來源于集體成員,集體成員身份的認定及其變化調整存在內部產權的不穩定性,也導致了其產權的流動性差等特點。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股權部分來源于村集體,其日常運作也是在村集體的主導下進行的,存在村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現象。
早期的南海城市建設與產業分散在各鎮和各村,2000年以后,南海政府開始規劃建設南海城市中心區,以及以獅山科技工業園和丹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為代表的新型核心功能區。位于南海城市中心的千燈湖公園于2003年竣工,以此為標志,南海的城市建設開始由“工業南海”轉向“城市南海”,南海發展模式由分散的工業化模式,向集中的城市化模式轉變, 土地價值得以提升,土地要素供需結構發生變化,產生了對存量集體建設用地進行重組的市場需求。也出現了政府與村集體之間爭奪土地資源的矛盾,政府希望通過規劃和征收土地來實現對集體建設用地的控制,村集體存在著強烈的對土地開發的沖動,容易出現缺乏長遠考慮、運作不夠規范以及對土地利用粗放、開發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
三、“南海模式”未來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
“南海模式”的未來發展演變,必須集中注意處理和解決好以下幾個關系和關鍵問題。
(一)土地流轉與產業發展的關系
土地流轉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發展,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帶來土地需求,土地流轉與集中利用是產業發展的前提。伴隨著人的轉移、資本注入的土地流轉與產業發展,可以提高農業發展附加值,提供勞動力就業崗位,起到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須伴隨著產業發展而不斷深入,必須適應而不可能超越產業發展。能否蘊育出富有驅動力的新型產業發展模式,決定著南海的未來發展。
(二)總體規劃與村民、村集體的利益關系
城市形態和功能不斷向高端提升,對土地的使用效率要求更高,必須通過合理規劃布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帶動南海經濟可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由于產業相對發達,人口較為集中,必須以新型產業發展帶動都市社區建設,從傳統的專業鎮向產業社區過渡,形成自然生態、產業生態、居住環境生態協調發展的社會經濟形態。
土地開發建設必須堅持以規劃為引領,區域規劃要符合當地產業發展和城市升級的特點和要求,統籌平衡各方利益,協調好政府與村民、村集體的利益關系尤為重要。
(三)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能否同等同權
2003年以來,廣東省通過一系列地方性法規,開始允許并逐步規范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2008年以來,黨中央多次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等農村土地改革方向。
目前我國的集體土地流轉并沒有做到與國有土地同等同權,南海的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仍然存在種種局限,不能在更大的范圍和程度上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集體建設用地應該按照中共中央歷屆全會的有關精神,與國有土地擁有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的權利,讓農民能夠均等參與產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公平分享產業化和城市化的收益。
(四)村集體的組織管理職能與經濟發展職能能否有效分離
隨著村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南海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開始出現管理職能與經濟發展職能相分離的趨勢,成立村集體資產管理委員會負責村集體經濟資產的增值運作,并承擔相應的市場風險,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開始向現代企業制度方向發展,村集體承擔社會管理職責,僅負責村務管理和公共品提供。這一趨勢預示著“南海模式”的未來發展方向,也可供其他地區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借鑒。
2017年4月,黨中央決定通過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發展新模式,優化調整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2017年8月,國土資源部與住房城鄉建設部全面啟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工作,廣東省的廣州市、佛山市、肇慶市名列其中。
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表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歷史性機遇時期即將到來,“南海模式”必將繼續創新突破、煥發出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Coase.R.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03).
[2]HP Binswanger,K Deininger,G Feder. Agricultural Land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3(05).
[3]周飛.我國農地流轉的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J].經濟師,2006(05).
[4]羅必良.農村土地制度:變革歷程與創新意義[J].南方經濟,2008(11).
[5]岳意定,劉莉君.基于網絡層次分析法的農村土地流轉經濟績效評價[J].中國農村經濟,2010(06).
[6]蔣省三,劉守英.土地資本化與農村工業化——廣東省佛山市南海經濟發展調查[J].管理世界,2003(04).
[7]房慧玲.廣東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1999(03).
[8]劉憲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變與結局[C].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八集,2011.
*本文為2016年廣東培正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農村土地流轉模式新探析”的階段性成果之一,課題負責人:李嘉健。
(作者單位:廣東培正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