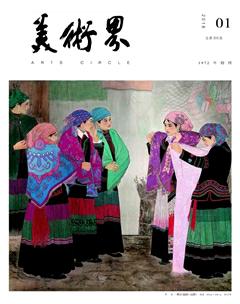芻議山水畫中的“正”與“奇”
梁澤浩
【摘要】本文通過對山水畫藝術的“正”與“奇”的創作觀念,即探討山水畫的一般形態與抽象(特殊)形態的對立統一關系,即正與奇的辯證關系。“正”與“奇”,如同學古與學自然,都是藝術創作過程中的一個過程和環節,臨摹是為了繼承中國山水畫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與高超的表現技巧,而奇是為創造與革新,今天我們辯證地理解“正”與“奇”的思想精髓,其意義在于,厘清傳統,開創未來,以期達到山水畫藝術的自然、神、妙的境界。
【關鍵詞】山水畫;陰陽辯證;正與奇
《周易·系辭》一書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是說奇偶、陰陽、乾坤、八卦等都由陰陽兩極組成,即是說世間的萬物有“陰”“陽”兩方面,它們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作用,互相轉化,這就是所謂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也就是老子提出的包含天地萬物、釋義萬千的“道”。這樣的辯證思想也反映在國畫藝術中,如東晉著名畫家理論家顧愷之在《魏晉勝流畫贊》一書中說:“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他認為表現對象必須要形與神的兼備,就如同陰陽正奇之統一,“正”,是指一切山水中的共通法則,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與規律性,還具有客觀性與約定俗成的法則或是“道”,而“奇”則指骨氣形似之外的“神”的抽象性與不確定的形態,這正是鄭板橋說的“趣在法外者”。正奇相生,讓觀者不僅可以感受到山水的“形”,還可以感受到畫者作畫時想表達的真“意”。
一、“正”與“奇”的辨析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博大精深,道家主張“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觀點與成語“大智若愚”,都是闡述萬事萬物都存在“正”與“反”面,即是“陰”與“陽”面,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而正奇之道恰若陰陽之道。
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孫子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孫子兵法》一書中提到“正”與“奇”的兩種交戰方式,“正”兵正面交戰,而“奇”兵是出奇制勝,如能掌握“奇”“正”兩種帶兵方法的將領,打仗的戰略戰術就會來變化萬千,他還說在交戰時靈活將“正”或“奇”兩種交戰兼容,戰略戰術就能游刃有余。孫子認為“正”與“奇”兩者之間能夠相互轉換、相互促進,這里指的“正”“奇”與山水畫中的“正”“奇”是一樣的道理。
“正”泛指常規的,“奇”泛指常規之外的,那么美學論作中有沒有對于“正”“奇”的討論呢?明代書法理論家項穆在《書法雅言》一書中曾說:“智永專范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傳之智永,內含剛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骳矣。”就是說李邕這個人呢,開始效法王羲之,雖然練得很熟練,但是沒什么新意,這樣的人就是只知道“正”,而不思變不通“奇”的人,后面師從虞世南行筆不凡,很飄逸,又少了幾分深沉和筆力。
項穆就書法中的“正”與“奇”的辯證關系,在他的著作《書訣》中作了回答:“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伏,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這就是說章法既要有書法技藝的“正”,還要有變化萬千的“奇”,才能洋洋灑灑地表現出書法的趣味性,而后又說:“正而無奇,雖莊嚴沉實,恒樸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而飛妍,多譎厲而乏雅。”這里強調如果一味追求“正”效果,就顯得莊嚴厚實而缺乏文采和才氣;而一味追求“奇”,過多的注重變化與偶然性的效果,不追求章法布置,則效果看著輕浮單薄難登大雅之堂,中國自古就認為書畫同源,書法的創作思想、審美方式、書寫方式與文化淵源同出一轍,對于山水畫的創作與表現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這就是所謂的“道”,同樣也追求巧妙多端的變化之“神”,因此,充分認識與梳理“正”與“奇”的辯證關系,才能真正深入的了解山水畫的精妙。
二、山水畫中的“正”與“奇”
“正”與“奇”不僅是藝術中學習傳統的“正”,還要求新求異探“奇”。因此,不善追求畫面變化的畫家,容易拘泥于“正”,而懂得靈活善變的畫家,也容易過于探“奇”,因此,畫家要善于掌控畫面的“正”與“奇”的“度”,那么山水畫藝術才能出現自然、神、妙的境界。若把“正”與“奇”對立開來,那么國畫藝術則會從厚重走向淺薄。正如唐代著名書畫理論家、畫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一書中所說:“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失去自然指的是超越客觀事物的表象,而得到畫的神氣韻味,令人覺得精妙,但是精妙過頭又變成謹細,反映了“正”和“奇”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即是“正(自然)”是“奇(神、妙)”的基礎,而過度追求“奇”則又“病”了。這正是古人評判國畫作品所說的形神兼備,亦是“正”與“奇”相互交融的結果,這一辯證的理念貫穿于山水畫創作的全過程。
首先,“正”與“奇”在山水畫中的表現,一是從創作方法上來說,山水畫中的創作需要感知客觀世界,創作的過程中,是基于現實客觀物象上的藝術加工和改造,在個景的造型上追求形似,具體作畫時在對樹的表現,需注意各種樹的姿態與精氣神,山需要表現出力量與厚重感,縹緲的云氣要表現出它的輕盈,水要表達出它的流動的快慢或靜止,正如南朝謝赫在六法說到:“三曰應物象形。”應物是作者對于眼中實物的感應,也就是所謂的“正”,從正面來觀察,而象形則是作者心中的腹稿,因此,畫家在立意時要打開思路,將自己的審美情趣、生活感悟與人生理想,還有對當代社會的理解等融進畫面的表現之中,還要將各景進行主觀營造。“正”與“奇”的思想觀念在山水畫的創作中,“正”是以客觀物象為基礎,“奇”是作者創作中將表現的“景”升華為“意境”的過程。
另外,從山水畫的構圖創作、設計經營位置、強調節奏關系、大小與呼應,以及如何安排畫面、如何突出重點、拉開遠近、布置虛實等,都需要不斷思考。如同清代學者鄭縝所說:“作畫須先立意,若不能立意,而遽然下筆,則胸無主宰,手心相錯,斷無足取。”山水畫的創作涉及到畫家的文化底蘊、專業功底與眼界這些基本條件,因為是基本的要求也是畫家的一般要求,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可以當做“正”,應物象形六法中的基礎法則,隨類賦彩是基于應物象形的基礎之上的法則,“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飄揚,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風不待五色而綷。”張彥遠這里說到,世間萬物變化萬千,本身并不能靠墨色與五種顏色表現出來,但是畫者之所以能夠用濃淡干濕的墨色加五色表現真實的山水變化,在欣賞的時候讓觀者得到身臨其境的感受,這便是中國山水畫的奇妙之處,計白當黑,用黑白世界表達彩色世間,從表面上看畫面色彩單一,即使是青綠山水,色彩也不過寥寥幾種,但是深層次的把握了山的特點,通過留白表達云霧,通過黑白陰陽生萬象,這便是中國畫實踐中的“奇”:通過黑白陰陽、構圖虛實來表達大自然的繽紛景色。構圖的“奇”,顯現在山水畫采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它是一種主觀的方式,可以讓你在山下看近景,在山腰觀中景,在山頭俯瞰全景,這樣的宇宙觀與時空觀,表現的大自然,是比真實的大自然還要壯觀的胸襟。這正是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景畫在觀察方式、創作方式、思想理念、材料工具、文化涵養等方面的不同,從而產生了不一樣的超自然的審美意境。
再次是從歷史進程來看,以董其昌為例,董其昌尚師古人,少時學黃公望,中年汲取董源、巨然之營養,他曾說:“豈有舍古法而獨創乎?他的畫中之經營,筆墨擺放,皴法,無一不有出處。”他還補充“雖復變之不離本源”,可謂之“正”,形式上為正,藝術追求上需找根本,以古法為依據,而馬遠、夏圭則是“奇”的踐行者,大膽摒棄了北宋以來以中鋒為中心的構圖習慣,大刀闊斧的選擇去表達山中一角。而李唐的《萬壑松風圖》更是大膽的頂天立地,不讓天地展示遠景和全貌,打破了北宋時期全景式構圖的舊例。但是董其昌在學古的基礎上也有自我的表達修養,并不是完全對古人的臨摹,而馬遠、夏圭沒有古法的基礎,也無法憑空創新。由此可見,“正”與“奇”相輔相成,馬遠、夏圭的畫里有古畫的法度可循,董其昌也有個人的創新。張彥遠還說過:“以形似之外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歷代名畫記》一書中以“正”為“奇”用,“奇”以“正“為基,再一次強調了二者統一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山水畫的學習中,我們既無法拋棄傳統的臨摹古人的練習,也無法回避造型之外的創新,我們要做師法道的圣人,亦要做通畫意的賢者,“正”與“奇”的思想觀念,可以幫助我們構圖立意,亦能幫助我們更好的學習山水畫。今天,我們深入了解“正”與“奇”辯證的關系,并將它更好地運用于山水畫的創作中,使我們以古人為師還不忘造化,“正”與“奇”也就是在臨摹中繼承,在創作中求革新,它的意義也在于,為山水畫的學習與研究,提供辯證的學習方法,而摒棄機械的求形似或者是神似的桎梏中。
參考文獻:
[1]史力生.易經科學新解[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
[2][東晉]謝赫.畫品[M].孟兆臣,校釋.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
[3][宋]蘇軾.蘇軾散文精選[M].王水照,聶安福,選注.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4]項穆.書法雅言[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全譯[M].承載,譯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6]彭萊.古代畫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