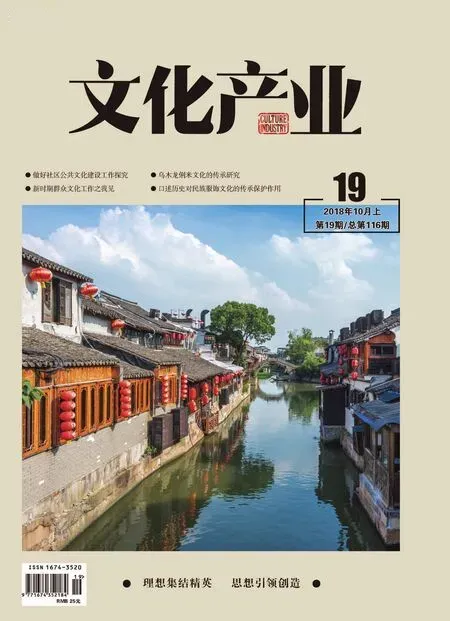淺談《吶喊》角色之“相術”
◎肖雪媛
(西南大學文學院 重慶 400715)
魯迅在《吶喊》中寫到的每一個角色,無論篇幅的多少、刻畫的詳略,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些角色的存在不再只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動力,而是成為了當時“混沌又躲避清醒”的社會現實的一種襯托,即人物角色本身及其表現成了時代的背景,他們的一言一行,甚至神態外貌都暗自透露著世態炎涼、世風日下。魯迅的高超之技便在此處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他基本上不用大段的筆墨來對《吶喊》中的大小角色進行完整細致的描摹,而是采取白描手法隨意又精準地勾勒出人物之形,以形讀心,將面相之術融于文學形象的塑造中,當這樣的藝術手法應用到《吶喊》中的人物甚至一掠而過的畫面小人物時,其戳人心扉、啟人深思的力量尤為強大。
一、中國相術
《說文解字》:“相,省視也。”本義即為仔細察視,而后延伸出人的相貌、面相之意。從它的意義發展中便可發現“相”是一個推理的過程——觀察主體通過對觀察客體外觀的考察以分析及認識其內在實質。而“相”在中國古代也被發展為“相術”,這門神秘的術法其實就是一種原始意識活動,是把外部感官感覺內化為心理認識活動的神秘體驗,并將這種體驗上升至自然禍福和人生命運的探討和預測。如此沒有科學理性思辨的自我意識行為難免會被現代人歸為迷信的范疇,但我們卻不能否定“相術”中顯現出的自身“正確合理”的“面相符號”,它用有限的外相分析來表達無限無形的天命概念,以相對的形式表達絕對的本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看相”對于分析人物的心性命理是有一定揭示作用的。
古之“相人”,乃根據人的容貌、氣色這類“外相特征符號”來預知人的吉兇禍福,即使戰國時期荀子曾言“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君子不道也”[1],相人之術也依舊深受世人追捧。而后“相人”從一般性的看相算命進入到寫作領域,演化為對人的外貌描寫,即作者通過觀察形貌言行以求“知人”。但這類有著看相性質的外貌描寫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對個人的某些形貌與其心性、命運之間的特定關系,形成了某些明顯的共性,才能夠使讀者看到其外貌描寫便對這個人有了與作者相通的判斷,比如《左傳》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說太子商臣“蜂目豺聲”,宣公四年楚國子文說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國語·晉語八》中叔向之母說楊食我“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此時“豺聲”這一人物的聲音性狀就成為人們公認的“惡人”之標志。
二、《吶喊》中的“相術”
魯迅在《吶喊》里對人物的描寫,也常采用“看相式”的白描手法。對于此技巧,他說:“‘白描’卻并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己。”又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2]不過多著筆,因此一筆就得點睛,畢竟觀察主體也大致只記得觀察客體的最突出特點吧。
在《故鄉》中,魯迅為曾經的“豆腐西施”楊二嫂看相——“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3]這段簡略的形象描寫中真正算的上是看相內容的只有“凸顴骨、薄嘴唇”,在面相學中,顴骨高聳的女人性格過陽,善于專斷獨行、權謀霸道,而嘴唇薄扁的女性則是很有個性、聰明有主張,但是心眼小、過于算計,由于天生的薄嘴唇方便說話,因此這類女人非常伶牙俐齒,但是缺少一些人情味兒。魯迅在描寫楊二嫂的外貌時,只狠狠抓住這兩個面相特征,總共也就六個字,但這兩個面相符號背后卻隱藏了太多對楊二嫂的個性分析,而魯迅并未像相術大師一樣為讀者一一指明,僅是通過最真實、客觀理性的面相觀察提供了楊二嫂簡單卻精準的面相特征,至于得出怎樣的面相分析結果則由讀者自行判斷。不過剛才已經提到在中國相術里,面相符號所對應的人物個性特征都是社會共識的結果,所以楊二嫂“凸顴骨”與“薄嘴唇”只需有印證材料即可,好在魯迅在文中好幾處地方都為讀者提供了佐證依據:第一,楊二嫂一出場便用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潑辣尖銳之氣頓時暴露無遺,在與迅哥兒的寒暄嘮叨中也是尖酸刻薄、毫不留情,好說些逼人墻角又令人無從反駁的話。第二,楊二嫂一板一眼的“要木器”,毫不做作的“偷手套”,惡人先告狀“在灰堆里埋碗碟給別人栽贓”,毫不遲疑地飛快“拿狗氣殺”,這類可恥的“偷雞摸狗”之事被楊二嫂一做倒成了有理有據的正義之舉了,隱隱中其自私霸道、愛占小便宜的本質屬性被揭露得十分深刻,這些舉證都印證出魯迅所相的“凸顴骨”與“薄嘴唇”的準確性,使楊二嫂小市民形象的庸俗嘴臉和惡劣習氣一覽無遺。但魯迅在文中也提到一個問題,在他的童年記憶里,楊二嫂并非現在這個樣子——“但是擦著白粉,顴骨沒有這么高,嘴唇也沒有這么薄。而且終日坐著,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么在魯迅離開故鄉的這幾十年,楊二嫂到底經歷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看到了她兩種鮮明的面相對比,感受到了她截然不同的性格變化,不過從一位年輕美麗的豆腐西施變為如今勢利虛假、尖嘴利舌的中年大媽與其謀生的環境也應是密切相關的,我猜想這段魯迅空缺的時間于楊二嫂而言大致也是人生的難多于生命的喜罷。
在《吶喊》中前后有著明顯面相變化的角色除了楊二嫂,那就當屬魯迅兒時的玩伴閏土了。先來看孩童時期的少年閏土的面相——“紫色的圓臉”。在中華傳統文化里,紫色和赤色一樣都是五行中“火”的代表顏色,代表著好運、健康、富貴,所以才有成語“大紅大紫”“紫氣東來”。而“圓臉”自然暗含著圓潤、有福氣的意思。所以從面相上來看,少年閏土“紫色的圓臉”說明當時的他積極有活力、健康、飽滿。但如此有福氣之面相也未能逃脫苦難歲月的摧殘,終究還是變成了蒼老、毫無神韻的相容——“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面色呈灰黃色則屬氣重有滯,氣重有滯的人大多形容愁楚,似愁似苦,舉止無力,言語聲微,凡滯由營養不足、精神壓力大等因素所致。這樣看來,閏土真正的面相變化主要在臉的顏色上,與之相應的他的性格也有了更變,從健康積極、天真爛漫的英俊少年變成了遲鈍、麻木、無言的中年,而促使這一變化的緣由也應和楊二嫂一樣,即消極地在生活中被扭曲、被毀滅、被改變,其個性棱角被苦難的生活漸漸消磨成圓角,沒了愿景也沒了希望,只可恭敬地喊出“老爺”了。由于小說容量有限,故事中角色的前后時間差又太大,很難在有限的作品空間中展示人物的精神、命運的歷程,而魯迅卻采用了“看相式”的人物描寫來刻畫出人物在不同時期的精神狀態,在前后對照中完成,以簡練的語言塑造出有特點的人物形象。
三、結語
“有心無相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由心滅”,實際上一個人的本心才是其性格命運改變的溯源之所。相術即心術,心性雖難以窮盡,相容卻可側面揭露。魯迅在刻畫人物形象時便是采用簡要精煉的“看相式”描寫,講出人物故事背后無盡的歲月經歷,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寓真實性于概括之中,置主觀評價與客觀描寫之中,短短幾言而意猶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