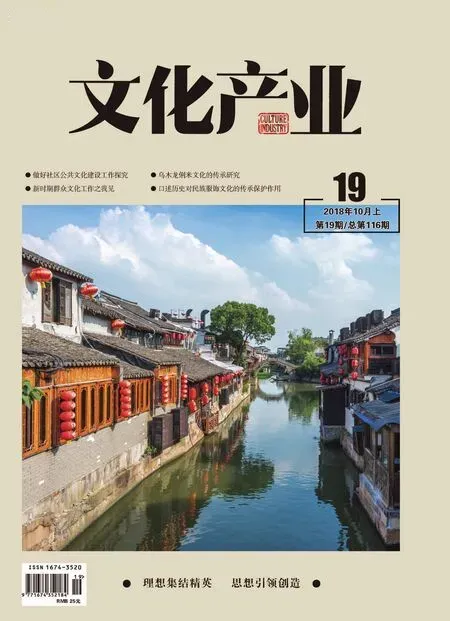論口述歷史對民族服飾文化的傳承保護作用
◎郭曉蓉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010024)
一、口述歷史與民族服飾文化現狀
(一)口述歷史的發展現狀
“口頭傳播”是傳播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在文字社會有文獻的傳播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歷史都是由人們口口相傳。現代口述歷史最早是在1942年由美國學者喬·古爾德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后被哥倫比亞大學采用,20世紀5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口述歷史研究部”,實施運用并推廣了口述歷史這一研究體系。此后,以美國為發端的口述歷史研究方法得到了世界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并在世界各地迅猛發展起來,各國涌現了大批的口述歷史研究專家與機構,口述歷史的重要作用逐漸的被人們所認識。
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是現代研究中國口述歷史的第一人,他從1957年開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工作,完成了口述史著作《胡適自傳》《李宗仁回憶錄》等,將這些珍貴的錄音和文字資料整理成書籍、影像發行,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新的重要史料來源[1]。
實際上口述歷史的這種記錄歷史的方法卻在中國已經有兩三千年的歷史了,在名著《春秋》中對于堯舜禹以及三皇五帝的記載,就都是憑后人的口述推演出來的歷史。但中國國內的現代口述歷史的理論建設與實踐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才真正的開始起步,鐘少華作為最早一批國內“田野調查”作業者之一,通過田野調查中的口述訪問,寫成了《中國口述史學芻議》。到了90年代,在受到海外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成果的影響下,國內歷史學者對于口述歷史這一研究方法也逐漸重視,口述歷史這一方法逐漸作為一種專業、官方的學術手段,開始更多地運用到了歷史文化研究之中,也有了一批值得稱道的不同主題的口述史學研究著作,其中也不乏關于民族服飾文化類型題材的研究,如《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走進鼓樓——侗族南部社區文化口述史》《留住手藝——對傳統手工藝人的訪談》等。
從目前的發展形勢來看,國內口述歷史正處在一個蓬勃發展階段。隨著科學技術發展,錄音、錄像器材的普及為口述歷史的推動提供了便利性,口述歷史的運用也變得更為普遍。當代,口述歷史這種方法已經成為歷史學家們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重塑歷史上與官方文獻史料有同樣重要的貢獻。
(二)民族服飾文化的現狀
在中國,許多少數民族服飾是少數民族文化的符號與載體,這些少數民族符號也被稱作為“無字的史書”,是一個民族歷史與過往的一段象征[2]。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現代文明的飛速傳播加快了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在許多的少數民族居住的村寨里,至今還有穿著本民族服飾的村寨已經越來越少,大多數的少數民族的人們穿著上了現代的時裝,本民族的傳統服飾成了只有在節日活動或旅游接客時才穿著的禮儀性的服裝。而這些傳統服飾中蘊含的故事情感以及工藝制作的技術在少數民族的年輕人中知道得越來越少,民族服飾文化正面臨著嚴重流失。
1.民族服飾制作工藝的衰退
在一項調查中顯示,在這些少數民族中,除了老人外,大多數的年輕村民只會有一兩套的民族服飾,只有在重大的民族節慶或接待游客時穿著,平時穿著的衣服大多是在縣城集市或服裝店里所購買。即使是民族服飾,其服飾用料也主要靠在市場上購買,自己紡紗、織布去縫制衣服的人越來越少。現代的化纖憑借其光滑、耐磨、快干且便宜省時的優勢占領了少數民族的市場,有些少數民族服飾在現代化的工業下也開始批量生產,但卻粗制濫造,少了手工藝人親自制作的那份精細與特別。傳統的紡紗、織布等服飾工藝在逐漸消失,紡車、織布機這樣的傳統工藝制作工具被人們置于廢柴堆中,一些少數民族特有的工藝技術在現代工業化的大環境下逐漸消失。
2.民族服飾藝人后繼無人
消失的不僅是紡織工具,在國內,大多少數民族服飾的制作從紡紗、織布、蠟染、挑花、刺繡等過程全部出自于當地婦女之手。對于服裝制作,少數民族女子從小便耳濡目染,培養了興趣和掌握了相應的技能。在這些村寨里,一個姑娘挑花、蠟染、刺繡等工藝的好壞,往往也代表著一個人的聰明與否,這些土生土長的農村婦女也正是我們所說的民間手工藝人。
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國家對于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開始重視,給了少數民族的許多的教育優惠政策,一方面,在這樣的重視之下,培養了許多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青年,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少數民族同時也接受了全新的審美價值觀念與異族文化。另一方面,在新思想的帶領下,年輕一代少數民族更希望接受教育,有沒有文化成為了一個人是否優秀的衡量標準。新一代的少數民族女性不愿意像她們的長輩一樣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挑花、刺繡這也樣的服裝工藝,而更偏向于去學習更多現代科學文化技術或早日外出打工掙錢,補貼家用。
過去少數民族人人都會的紡紗、織布、蠟染、刺繡等藝術,現在漸漸被化學染料、機器縫紉所代替,掌握傳統工藝的人年齡越來越大,懂得這些服裝工藝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民族服飾文化的斷層擴大,傳統服飾技藝面臨著失傳的嚴峻現狀。
3.口述歷史與民族服飾文化的關系
少數民族服飾的傳承其實從來沒有和“口述”分離過,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大多數少數民族都只有自己的語言而未曾有過自己的文字,現有的文字檔案極少有關于這些民族服飾文化的記載。由于沒有文字,少數民族的傳統藝術絕大部分依靠民間藝人的口傳心授,這一點在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中顯得尤為重要。民族服飾文化隨著文明發展得以時代相傳保留到今天,民間藝人一代又一代的口頭傳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以苗族為例,苗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千百年來,它的文化傳承靠的是一代代的口傳心授,靠的是傳唱的苗族古歌,靠的是婦女們繡在衣服上的刺繡以及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蠟染藝術。在沒有影像手段記錄的幾千年時間里,古老的苗族文化傳統仰仗口傳的方式依然鮮活地保留在人們的生活中,直到今天,這是口傳文化的力量[3]。苗家的傳統刺繡、剪紙、蠟染中所描述了苗族千百年來的文化、歷史、宗教、信仰、習俗和祖先起源。因此,苗繡也被稱為“穿在身上的史書”。由此可見,苗族刺繡的生存就是口述歷史活的見證。如果沒有口述的代代相傳,我們可能現在也聽不到優美的古歌、見不到精細的苗繡。
二、口述歷史在民族服飾研究中的應用
目前為止,口述歷史中對于民族服飾研究的專項較少,《口述歷史在土家族挑花研究中的研究》是已有的一篇關于口述歷史在服飾文化傳承中的應用中研究較為全面的一篇文章。筆者這里選擇以這篇文章為例,來分析口述歷史的采訪環節在民族服飾研究中運用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一)口述史料的搜集
口述史料是一種對史料的表達方式,與其他史料一樣,都是過去得記載或是遺留的遺跡。口述史料主要依靠書籍記載、后人流傳、民謠等途徑。在中國史研究中,這種口傳或后人記錄的傳話幾乎與實物史料同樣引起人們的關注,歷來為史家所重視,具有重要地位[4]。
口述歷史是研究者基于對受訪者的訪談口述史料,并結合文獻資料,經過一定稽核的史實記錄,對其生平或某一相關事件進行研究,是對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
再準備口述歷史采訪環節時,首先要聯系各界,廣泛收集相關資料。以《口述歷史在土家族挑花研究中的研究》為例,吉首大學在開展口述歷史研究工作之前先是與當地少數名族的地區民委、非遺文化中心等長期從事地方文化事業的機構聯系,并進行走訪,采訪了土家族研究專家12人,獲得了關于土家族挑花的眾多文獻及圖片資料。
(二)選擇訪談對象
口述歷史的受訪人選擇對整個記錄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常研究者會通過“田野調查”對少數民族中的村落進行走訪,調查對該項服飾工藝了解的知情人,經其互相引薦,在經核實后挑選出合適訪談人選。在《口述歷史在土家族挑花研究中的研究》中,采訪者就主要根據所獲榮譽與它挑花的淵源這兩點作為篩選受訪人的一個標準。
(三)口述歷史的約談方式
口述歷史有一對一的訪談形式,也有集體式的訪問。在確定采訪對象之后,我們要對受訪者建立基本的檔案,包括他們的簡歷與聯系方式等,并根據每個約談者的生活經歷和背景資料、興趣愛好等等方面的不同,制定有針對性的訪談提綱。
訪談時要提前安排好項目組成員,盡量精簡人員,口述時間控制在兩小時以內,以免對受訪者的干擾,保證口述資料的質量。注重訪談過程中的互動關系,采訪者應仔細傾聽受訪者的語言,不要輕易打斷受訪者的語言。
(四)口述史料的整理
在進行完約談之后,項目組成員要將訪談資料進行整理,轉化為文本形式,首先要對訪談筆記逐頁審查補充,保證記錄完整性,再將音頻、視頻資料逐字逐句的轉錄為文字,保持口述歷史的原始性,不能進行個人的歸納與總結。其次,在口述史料整理完成后,要將整個口述訪談內容進行整體的分析、詮釋。在涉及事件、人物的口述時,要求證知情人或查閱相關文獻資料以保證訪談內容的真實性。例如在《口述歷史在土家族挑花研究中的研究》中,針對受訪者所說的“拉花是湘西土家族獨有的一種技藝”,項目組為此求證了在土家族研究領域的專家,證實了受訪者所說內容的真實性。
三、口述歷史在民族服飾文化傳承的價值
(一)口述歷史的史料補充價值
過去,史學家對于歷史的研究主要是依據文字史料,其中包括官方文獻或民間記載。這些文字史料大多數為官方正史,記錄的是國家統治階層和社會各界精英的活動足跡,對于民間文化的內容記錄較少,某種情況下,只是一面之詞,無法反映歷史的真相。人類的活動無比豐富,即使是再詳細的檔案、文獻、史料也只能記錄下人類歷史活動的極小一部分,人們生活中的一些細微事物、活動以及認知,往往也不一定能夠載入史冊。并且由于種種的歷史動亂和社會變遷,導致大量的文字史料流失,更是常有的事。口述歷史通過對社會底層人士的探訪,獲取在官方文獻中無從找尋的那一部分信息,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側面的見證了歷史,將底層人民的個人經歷與歷史記載相結合,讓歷史更加全面、真實。
民族服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記錄一個民族文化的圖像史書,口述歷史讓民族服飾的制作技藝和歷史有了在了文字史料之外的另一價值與意義,通過老藝人的口述,來收集、搶救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服飾的制作工藝,可以彌補無文字民族的歷史記載的不足,加強對民族服飾文化的傳承。
(二)口述歷史的情感價值
民族服飾文化的傳承人是掌握、承載著民族文化的群體或者個體。作為一個有著獨立思想的民族文化的承載者,由于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原因,傳承人自己的獨特思想和見解,對民族服飾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他既可以使民族服飾文化健康長遠的發展,也可以導致文化消亡。
在少數民族的群落當中,口頭傳播文化秉承了他們的集體情感與個人情感。集體情感意味對本民族的文化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和使命感,個人情感意味著講述者對于講述的故事背后的個人情感。我們通過口述者的回憶性敘述,透過個體來看集體,洞察個體情感背后的集體記憶。
情感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手藝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技能。少數民族的服飾不僅承載著過往的歷史,往往也蘊含著每一個制作它的手工藝人的情感。國內著名的服裝設計師馬可曾說過一句話:“匠心的傳承,不僅僅是技藝的傳承,更是精神風骨的傳承。”服裝的史料記載的東西只是頂層人們的生活服飾,對于少數民族的記錄較少,并不會帶你去了解每一件服裝背后的故事與情感。少數民族的服裝絢麗多彩,沒有現代工業的影子,每一件民族服飾都可能是一個手工藝人長達幾月或一年以來的穿針引線之作,這可能是女兒的一件嫁妝、孩子的第一件衣裳,這些生于民、長于民的手工藝之美,如蘊含著手掌的溫度,傳遞著愛。所以筆者認為,當我們用口述歷史這一獨特的記錄方法時,直接從匠人、藝人們的口中獲取這些有關民族服飾文化發展、淵源甚至制作方法的資料是十分真實且有意義的,這些個體記憶和經歷也反映了整個民族的高尚品格與思想情操。
(三)口述歷史的文化價值
口述歷史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口述歷史的文化價值,而口述歷史給了民族服飾這樣的一個機會,服裝的演變往往與歷史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講述的人能夠在傳授技藝和方法的同時透露一整個時代的背景故事。口述歷史的文化價值是由各個方面體現的,它真實地再現了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真實地反映一個民族變遷的歷史記錄,是通過人們的記憶、經歷孕育出的精神產品,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用獨特的方式證明了不同民族文化在歷史中起到的作用,有著多重的文化和社會價值。
現在,口述歷史傳承著民族意識、民族傳統宗教和民族文化哲學等,是民族傳承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文化累積的重要手段,能從側面真實地反映民族的獨特魅力。將官方的文字史料和人們的記憶和經歷相結合,多方面、多層次地來重塑歷史是最全面的 記錄和傳承方法。口述的記錄手段已經更加專業,從對歷史的簡單重現深入到大眾歷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在“文獻上的過去”變為“記憶中的過去”。口述歷史能夠在重塑歷史的多層面結構作出自己得天獨厚的貢獻,這點已經被口述史學家所公認。
四、結語
近年來,在經濟文化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下,各個民族散落在民間的民族服飾文化正在消逝,但文化變遷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中國的民間服飾文化是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歷經滄桑的服飾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演變中所形成的具有獨特魅力的藝術瑰寶。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獨特的記錄研究方法,已經被廣泛的應用在各個學科,將口述歷史用于搶救藏于民間的民族文化,將這種方法用于保護和傳承民族服飾文化是當今的學者們和我們應該去繼續深入研究的。保護我們祖先的優秀文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