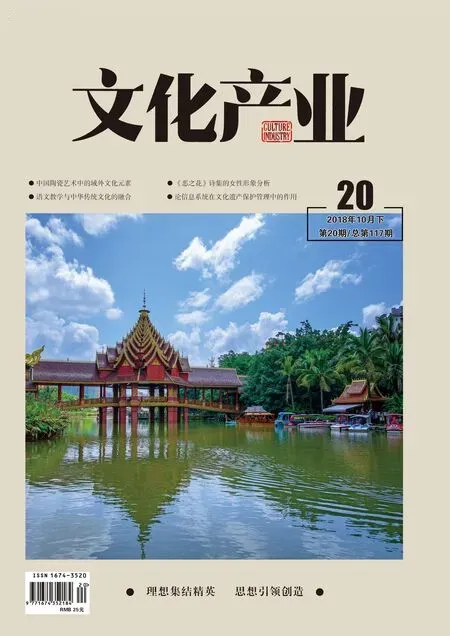《惡之花》詩集的女性形象分析
◎張瑋瑜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6)
1857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出版詩集《惡之花》。“惡”(Mal)在法語中有邪惡、丑惡、罪惡、疾病、痛苦等義,在詩集的獻詞中,波德萊爾稱詩集為“病態之花”,這種病就是“世紀病”,是當時的年輕人在腐朽黑暗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享受物質生活的同時,無聊空虛、憂郁孤獨,而又無力掙扎的心靈困境。
在《惡之花》詩集中,波德萊爾描繪了很多女性形象,如情人、女妖、社會中不同地位的女性等等。詩人作詩就是要“審丑”,通過描寫丑惡的事物以抒發對美的向往與追求。
一、對女性形象的描寫及其內涵
波德萊爾在生活上縱情聲色,從他自己記錄的詩歌中可見,他的性生活混亂放肆,“他蔑視世俗,蔑視功利,終日呼朋引類,冶游濫飲,宣泄生命,以求麻醉和解脫。”[1]波德萊爾一面是“惡”的批判者,一面卻也是“惡”的感染者,這既是詩人感染“世紀病”的病癥,也是他尋求精神自由,希望能從孤獨憂郁中解脫的冒險。但與庸碌世人不同的是,波德萊爾沒有在“惡”中沉溺,與之相反,當他“作惡”時,他一邊享受著快感,一邊又陷入清醒的痛苦之中,試圖在自我毀滅中得到真正的精神自由。
(一)對情人(愛情詩)
波德萊爾的愛情詩主要是寫給他的三個情人:娜·迪瓦爾、薩巴蒂埃夫人和瑪麗·迪布朗。
娜·迪瓦爾是一個黑白混血美人,是詩人肉體之愛的代表。曾被法院判決刪削的六首禁詩中,《首飾》《忘川》所描寫的就是娜·迪瓦爾。波德萊爾經常在詩歌中生動地描述他與愛人的熱烈纏綿,“她隨后就肉體橫陳,讓我撫愛/從沙發高處露出舒適的微笑/見我如此情深意綿,就像大海/升向懸崖那樣,向她步步升高。”[2]這種暴露直接的描寫,充溢著詩人在肉欲狂歡中的滿足。
當熱情消退,詩人便重回冰冷丑惡的現實中。于是,波德萊爾轉而追求精神的愛情,以緩解狂歡之后帶來的更大的失落與無聊。波德萊爾追求薩巴蒂埃夫人——一位銀行家夫人。由于兩人的身份相差太多,詩人只能通過寫信的方式表達他的愛戀。《給一位太快活的女郎》寫道:“然后,真是無比的甘美/再通過你那過分晶瑩/分外美麗的新的雙唇/輸我的毒液,我的姐妹!”薩巴蒂埃夫人是醫治他痛苦與孤獨之存在,為他帶來快樂與光明,因此應該是“純潔”的。
瑪麗·迪布朗則是詩人情與欲的中和品。《秋之歌》題名獻給M.D(即瑪麗·迪布朗),堪稱詩人愛情詩的絕唱。詩中寫道:“時間不長!墳墓等著;它真貪婪/啊,請讓我把頭枕在你的膝上/一面惋惜那炎炎的白夏,一面/欣賞晚秋的柔和的黃色的光!”該詩流露出脈脈溫情,體現出詩人在追求愛情的路上變得成熟平和。
(二)對女妖
《惡之花》中不乏對惡魔的描寫。詩人以為,惡魔引人沉淪,是死亡與黑暗的象征,而女妖或女惡魔的形象則通常與陰暗、縱欲相關。《兩個好姐妹》中寫道:“充滿褻瀆之氣的這種臥室與棺材/仿佛有一對好姐妹,輪流地給予我們/無數恐怖的快樂以及可怕的溫存。”詩中提及的兩姐妹,可以理解為淫神和死神,詩人借此表達自己在放蕩中等死的心境,短暫的生之快樂后將是長久的死之恐怖的矛盾。
而在《被冒犯的月神》一詩中,詩人寫道:“披著你的黃袍,舉步輕輕悄悄/你還要像從前,從夜晚到拂曉/去吻恩底彌翁的過時的玉貌?”月神愛上俊美的恩底彌翁,每晚都會去親吻他,而恩底彌翁作為一個凡人,生命有限,早已衰老化為枯骨。詩人對月神親吻枯骨的調侃,實際上是想表達美好總是短暫、幸福不能長存,間接地反映出詩人內心的空虛與孤獨。
(三)對其他女性形象
詩人在《惡之花》詩集中還描寫了很多其他女性形象,如詩人的母親、養女、社會下層女性和老太婆等等。
在詩集的第一篇《祝福》中,詩人描寫他的母親:“她親手堆積在那焦熱地獄里面/為懲治母罪而準備的火葬柴薪。”[3]波德萊爾和他的母親一直都有矛盾,這令詩人感到不被理解,同時他又將這種孤獨和煩惱當作是一種精神考驗和祝福,讓他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挖掘丑惡、批判丑惡。
波德萊爾對老太婆充滿同情,他在《小老太婆》中寫道:“我的復雜的心品味你們的一切罪惡/你們的一切美德使我的靈魂發出光芒!”那些街上佝僂蹣跚的老太婆們曾經也是美麗動人,可是一旦年老色衰,則變得卑賤無助,詩人借此批評世人膚淺忘本、喜新厭舊的本性。雨果在給波德萊爾的致謝函中寫道:“你給藝術的天空帶來說不清的陰森可怕的光線。你創造出新的戰栗。”那種道不清說不明卻撼動人心的東西,就是丑惡,更是丑惡背后詩人想要追尋的美好。
二、女性形象與審“丑”
1857年,巴黎法院判定《惡之花》違反侮辱公共道德罪,因為“被指控的詩篇中,這些畫面由于一種粗俗的、有損于廉恥的現實主義手法而必然會去刺激讀者的感官”。詩集中驚世駭俗的詩句在當時并不被人們普遍接受,但真正讀懂波德萊爾的人,他們都知道詩人內心的孤獨與掙扎。戈蒂耶在《環球導報》中說:“他(波德萊爾)正是罪惡,但把它視為他非常了解的一位敵人,并與之斗爭。”[4]丑惡的內容為現實主義不容,但“審丑求美”的精神則成了象征主義的先河。
波德萊爾筆下被賦予濃烈感情與深刻內涵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丑惡”的女性。這些扭曲、變態的女性形象,是詩人在告訴世人,“他只會遇到不可避免的罪孽,也就是說,隱藏在黑暗中的魔鬼的目光或在煤氣燈下閃光的梅薩琳的肩膀;他只會遇到純粹的藝術,也就是說,惡的特殊美,丑惡中的美。”[5]這就是說,詩人盡情地描寫“丑”,是因為“丑惡”與“美好”一樣,都來自于現實生活,都是一種藝術的表達。
大量丑惡的女性形象的描寫,是波德萊爾刻意的“審丑”的藝術創作,主要原因歸為三點:一是因為他見到的資本主義社會處于腐朽糜爛的氛圍中,“丑”就是一種在全社會彌漫的病;二是因為詩人盡管能夠發現問題,卻依然無法掙脫“世紀病”帶給他的憂郁、無聊、空虛、孤獨和痛苦——肉欲與激情只能帶來短暫的歡愉,卻無法使他真正解脫;三是因為詩人要在這種壓抑與絕望中反抗,通過描寫“丑”以揭露、批判現實社會的空虛黑暗,表達對美好與光明的追求[7]。
戈蒂耶曾評價道:“我們找不到比波德萊爾的詩篇更加強烈和熱誠地反映對純凈的空氣、對潔白無暇的喜馬拉雅山霰雪、對一碧如洗的蒼天、對永不暗淡的光明的渴求了。”[8]這是對波德萊爾《惡之花》很高的評價。詩集描寫的是極致的“丑”與病態的生活,但正是極丑之中,孕育著至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