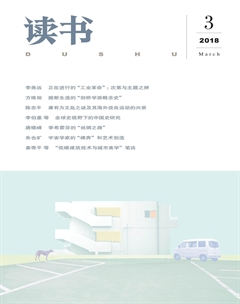不合時宜的軍事空間
鄭興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以對戰爭的特別關注而聞名。在他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處女作《地堡考古學》中,維利里奧考察了“二戰”時期由納粹德國沿歐陸西海岸修建的著名防線——“大西洋壁壘”。這條防線綿延數千公里,設置了混凝土炮臺等種種防御工事,曾號稱是“不倒防線”,然而,它終究還是未能阻止盟軍的登陸。那么,維利里奧為何要在“二戰”結束后考察這條早已廢棄的防線?這片戰爭殘垣對他的思想歷程,乃至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意味著什么?
一、軍事空間的轉換
討論“大西洋壁壘”,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條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防線,何以不堪大用?從具體軍事角度的回答當然已有很多,比如工程的完成度不高等等。維利里奧并沒有糾纏于這些具體的戰術戰略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條防線根植于已然過時的空間哲學,其失敗從一開始就是注定的。
維利里奧認為,關于戰爭,人們會談論戰爭史,談論戰術,談論死亡,卻鮮有人深入探討戰爭中的空間問題。戰爭首先應該被視為一個自有其特征的幾何學空間。在古代的戰爭中,防御不是加速,而是減速——減緩敵人的速度,保護自己的安全。古代戰爭的準備就是城墻、碉堡和壁壘。無論是圍墻還是壁壘,都是古代戰爭中組織空間的重要方式。人類社會就是在面對戰爭的種種威脅中,設法分配、運籌自身的地理空間,最早的人類城市就誕生于這一過程之中。
壁壘,就是古代戰爭中空間哲學的典范表征。在冷兵器時代,它們確實發揮過作用,中國的長城即是一例。但是,在《地堡考古學》中,維利里奧指出,古老戰爭的空間哲學不合時宜了,因為戰爭中的速度越來越快,無論是各類運載工具的速度,還是各種武器的速度,都在不斷攀升。速度其實意味著一種空間的相對關系,速度越快,穿透空間的能力也就越強大。戰爭的范圍越來越大,所耗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整個人類的棲息地其實都處在不斷地相對“縮減”的進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試圖以“減速”為防御的指歸,試圖用“壁壘”的形式分割防御空間,難如登天。
維利里奧的“競速學”理論在此處已經初露端倪。他看到,是速度的演進,在空間組織方式的變更中,占據著關鍵地位。他在另一本著作《速度與政治》中,更是賦予速度以本體論意義,速度不僅決定著軍事領域,更是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決定歷史的關鍵力量,在黑格爾那里,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那里,是經濟基礎,而在維利里奧這里,是速度:從馬車到火車到飛機的運輸革命,是位移速度的提升;從書本到電視、電影、網絡的傳輸革命,是信息傳遞速度的提升;從奴隸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組織速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戰爭空間的維度也更為復雜了。在古代,戰爭的空間基本上是局限在陸地維度。工業革命以后,海洋的維度開始越發重要。隨著飛機的發明,特別是“二戰”以后,則宣告了天空的維度越發處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說,“二戰”以后,戰爭空間已然是陸地、海洋、天空三個維度。僅僅把握其中的一個維度,無法真正掌控戰爭空間。將防御的希望僅僅寄托在陸地的維度,另外兩種空間卻缺少相匹配的措施,也是不現實的。《地堡考古學》告訴我們:
希特勒從來沒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從來對征服海洋沒有信念,這是德國戰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德國空軍從來沒能趕上盟軍的空中戰略,盡管他們有著更為先進的飛機;德國海軍有著更高質量的戰艦,卻在戰爭早期遭遇了挫折。這些都是一種軍事空間哲學的結果,一種困縛于土地和地表的軍閥哲學的結果,一種損害空中和海上的努力,卻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產政策的結果。
如維利里奧所說,“軍事空間正在經歷一種激進的轉換”,即便投入再多的混凝土和鋼鐵,安置再多的火炮,“大西洋壁壘”依然只是古老戰爭的空間哲學在借尸還魂。在現代戰爭的語境下,再堅固的壁壘所能發揮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失敗的命運從建造的第一天開始,就已經注定。
二、“戰場即是知覺場”
不過,問題可能還不止這么簡單。
要知道,在“二戰”開始的時候,是德國人將“閃電戰”運用到了極致,速度的重要他們難道不清楚嗎?也是德國人,他們繞過曾經號稱堅固無匹的“馬其諾防線”,令法國人措手不及,他們難道不清楚類似的防線難堪大用?即便里程更長,工事更多,又能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不還是重蹈覆轍?
《地堡考古學》中更有意思的是,它指出,希特勒未必顢頇到完全依賴“大西洋壁壘”去保障防御,之所以還要建這一防線,是因為除了防御,它還別有用途。這可以歸結為維利里奧的另一重要概念:“知覺后勤學”(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維利里奧認為,戰爭的關鍵是“后勤”。傳統的軍事后勤當然指的是,戰爭組織者動用各種手段,使武器、物資和人員實現獲取、調動與流通,以維持戰事的持久保障。但是,維利里奧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另一種“后勤”,亦即關于“知覺”(包括視覺、聽覺、心理等層面)的后勤。每一場戰爭都是知覺的場域,戰場首先就是“知覺場”。在戰爭中,除了物資、人員和武器的供應,“知覺”的供應也一樣不可或缺。在視聽層面,知覺供應就是要盡可能獲取一切與戰爭有關的信息,洞察敵我的方方面面,以在戰場上占得先機,而“大西洋壁壘”則更多意味著一種心理層面的知覺供應。
首先,這條防線提供給納粹帝國的士兵和民眾一種安全感。如此驚人的長度,如此巨量的投入,如此威武的炮臺,加上戈培爾對這條防線大肆宣傳,稱之為“不倒防線”,德國的民眾和士兵就算未必真的了解這條防線,在心理層面一定對它信賴有加。維利里奧寫到,德國人在建造這條防線的時候,采取“大雜燴”手法,無所不用其極,將古往今來所有能用的防御手段,從最古老的木樁障礙,到最先進的電子手段,都傾其所有。用維利里奧的話說,在當時,“地堡成了一種神話”。既然是“神話”,就不必在事理層面計較其是否荒誕無稽,在當時,只是為了制造無懈可擊、完美無缺的表象,為了制造一種正面的心理反饋——“我們的國界是不可穿透的。”endprint
在納粹眼中,“大西洋壁壘”還能提供一種集體認同感,使整個納粹帝國更具凝聚力。一方面,它是防線,當然提供了安全感,但反過來說,如此浩大的防御工程,不正證明了,防線后的帝國正處于強敵環伺之下?當時的納粹帝國,除了德國以外,還有不少其他地區、民族,語言、文化差異巨大,加上其他國家都是受侵略國,難有集體認同。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將這些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動員起來,成了一個難題。但是,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當不同的人群面臨著共同的生死存亡的危機,差異、敵意也許會暫時被擱置、忽略,油然而生一種集體認同。
為了使這種知覺效果得到發揮,一方面,納粹德國竭力抽調帝國內部各個地區的人力,將他們投入集體苦役之中,修建“大西洋壁壘”。另一方面,為配合這一工程,納粹還在帝國內部的平民之中人為制造恐懼感和危機感。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帝國官方“建議每戶民眾在自己后院里、庭院里挖塹壕,以保護自己的家人”。他們還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作出各種帶有毀滅性場景的照片,讓民眾觀看。災難被提前預想出來,“好像巴黎已經被摧毀一樣”。這些手段,顯然會“增加被占領民族的恐懼,使這樣的恐懼超過被解放的希望”。當危機感和恐懼感無處不在,人們就被納入到一個共同體之內。納粹就是以這一方式,制造集體認同,試圖以此激發出帝國最大的戰斗力。
一系列圍繞著“大西洋壁壘”的種種舉動,如同做戲一般,難怪維利里奧會說,“最后的要塞是一個劇場……透露出他們的戲劇效果,透露出他們所必要的、奇觀性的一面”。納粹所需要的就是這種主客渾融一體、共同參與的“奇觀”。因此,“大西洋壁壘”到底能在多大層面上左右戰局,不是納粹關注的唯一維度,他們還需要讓帝國官民一起“入戲”。這也正是直到“二戰”尾聲,防線工程依然沒有停止的原因,因為“知覺后勤學”的需要,一直都存在著。
三、從“總體戰爭”到“純粹戰爭”
維利里奧開始考察“大西洋壁壘”的時候,“二戰”早已結束,為什么他還要如此細致地考察這一殘留的防線,單單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嗎?而且,“二戰”距離今天已過半個世紀,更是早已滄海桑田,因此,本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維利里奧對“大西洋壁壘”的考察,對今天的我們而言,還能有什么價值嗎?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維利里奧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結束。”
維利里奧曾在《速度與政治》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總體戰爭”(Total War)的誕生。國家將不再如以前那樣,區分為“民用”與“軍事”兩個領域,指望軍隊和敵方在某個封閉的戰場內捉對廝殺,而大部分民眾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生產,兩不相干,已再無可能。新形勢下,整個國家的經濟和人員都將動員起來,統一為戰爭目標服務,以便讓國家的戰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大西洋壁壘”的建造,就是舉全國之力而造就的產物,正是這種“總體戰爭”的典范。
當“總體戰爭”付諸實施,用維利里奧的話說,整個國家就被鍛造成一個“軍事-工業集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是一個工業為戰爭服務、軍事和工業渾然一體的國家機器。“二戰”結束后,“總體戰爭”結束了,大面積戰事不存在了,但是,戰爭的內在邏輯還一以貫之,以更隱蔽的方式延續著,“總體戰爭”已經演變為“純粹戰爭”(Pure War)。“純粹戰爭”是另一種形態的“戰爭”,它不再體現為具體的沖突(比如“二戰”),也不再體現為具體的對立雙方(比如東方和西方),而是定位于“軍事一工業集合體”的內在邏輯,這一邏輯早就根植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直至今天,都未改變。
“純粹戰爭”之所以存在,“軍事-工業集合體”之所以能在世界大戰結束后還延續,是因為,面臨敵人的恐懼一直存在著,使得現代國家時刻不敢放松神經。在“二戰”的時候,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和軸心國為敵;“二戰”結束后,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為敵;冷戰結束后,伊斯蘭世界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互抱敵意……但是,不管怎么“城頭變幻大王旗”,恐懼永遠存在,“軍事-工業集合體”的步伐也就不會停止。現代國家其實一直都生存于戰爭的陰影之下,潛在的滅絕和殺戮從來都若隱若現。
《地堡考古學》還為我們刻畫出兩種“軍事邏輯”的對立。它告訴我們,“軍事-工業集合體”將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它們害怕戰爭的耗時越拉越長,所以,它們需要發展各種技術,去使戰爭時間不斷縮短。縮減戰爭時間,是現代資本主義“軍事-工業集合體”的主導性軍事邏輯,它所主要針對(也即最恐懼)的是所謂“落后國家”的另一種軍事邏輯:持久戰。后一種軍事邏輯對現代“軍事-工業集合體”的威脅將會一直存在。“黑鷹墜落”隨時可能再度發生。所以,現代“軍事-工業集合體”會不停地鼓吹所謂零傷亡戰爭、鼓吹快速戰爭,就是為了制造“戰爭無害”的錯覺,試圖使戰爭趨向合法化,那么,為戰爭而竭力發展軍事技術也可因此而被合法化。
維利里奧還進一步指出,在這種“軍事-工業集合體”宰制之下,現代科學技術必然會被帶入歧途。科技進步曾經更多是“民事”意義上的,使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發生質的改進,但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后,“軍事-工業集合體”的邏輯主宰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今天,經濟、工業的發展雖然披上了“科技進步”“文化發展”的溫情外衣,其實,主要還是為“軍事”服務,為“縮減戰爭時間”服務。“民事”的福祉并不因為這些經濟、技術的發展增進多少。就像維利里奧所說的,“戰爭在科學中運作……每一件事都在敗壞科學的領域”。
可以看到,維利里奧之所以在“二戰”結束后還關注廢棄的“大西洋壁壘”,是因為他從這一防線中看到了自“總體戰爭”到“純粹戰爭”的演進,貫穿其中的是“軍事-工業集合體”邏輯,這一邏輯至今仍未改變。今天的我們依然處于“純粹戰爭”的陰影之下,在這個意義上,“‘二戰并未結束”并不是維利里奧的危言聳聽,也正因此,《地堡考古學》對今天的我們依然啟發良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