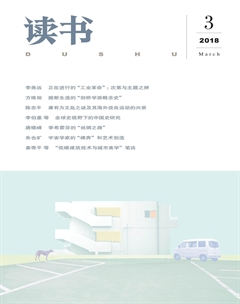紀錄片如何抵達歷史真實
楊弋樞
撬動歷史真相有時候就像打開潘多拉之盒。二0一六年四月,印尼總統顧問委員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辦了名為“剖析一九六五年悲劇及歷史研究方法”的反思研討會,聚焦于印尼五十年前針對印尼共產黨和左傾人士的大屠殺事件。正如五十年前的印尼,作為大國冷戰意識形態的前沿戰場,在外部推動力與內部復雜的政治派系力量的雙重作用下,導致了被害人數超過一百萬人的大屠殺(因相關檔案未解密,相關研究未進展等原因,具體數據依然不詳)一樣,討論大屠殺事件的當下會場,依然是一個充滿了論爭和撕裂的現場:印尼政府成員、前領導人和被害人家屬、大屠殺幸存者、不同宗教代表、學者、人權活動家、軍方代表等同時出現在討論現場,會場外則是擔心共產主義在印尼復活的抗議者。幸存者要求道歉,官方否認了道歉的可能性,以證據不足否認屠殺人數,人權領導者呼吁美國政府解密檔案,公布其在印尼大屠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女權主義者則控訴屠殺者對女性的摧殘。顯然,這個打開的歷史之盒還遠不能揭開真相或達成和解,但,它至少打開了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記憶封口與黑暗地帶。
五十年里,大屠殺是印尼社會的禁忌話題。《想象的共同體》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經發表過題為《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印尼政變的初步分析》的論文(這篇論文通常被稱為《康奈爾文件》)。作為第一個討論屠殺真相的學者,安德森頗為同情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前總統蘇加諾,他和同事一起揭示導致蘇加諾下臺的蘇哈托軍人政變的謊言,質疑其政權的正當性,也因此,此后二十余年被印尼政府禁止入境。在大屠殺五十周年的二0一五年,有關大屠殺的文學活動、書籍發布、公開紀念、電影放映、研討會仍然在被禁之列——準確地說,被禁止的是與官方意識形態相違的討論。實際上蘇哈托政權在一九八四年就支持制作過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宣傳電影《印尼共產黨“九三0”叛亂事件》(Pengkhianatan G 30S/PKI),影片從印尼共產黨成員拿著鐮刀和斧頭偷襲殺戮晨禱的穆斯林信徒開始,以扮演、文獻與解說結合的半紀錄半劇情的方法,將印尼共產黨描述成挑起了“九三0”叛亂、殘暴無比的國家敵人,作為英雄的蘇哈托將軍平息了叛亂,并建立起印尼新秩序。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學上,影片深沉的畫外音、充實的史實資料、自然的表演、現實感的場景、藝術化處理的暴力畫面,將宣傳語言包裹在幾乎無可挑剔的電影語言里。影片在影院、學校、公共電視臺(每年“九三0”)不斷播放,成為印尼蘇哈托專制時代觀影人數最多的影片。印尼屠共大屠殺和德國納粹種族大屠殺、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相同的是,屠殺都是由殺人集團操縱國家機器、將特定人群劃為國家公敵、以輿論灌輸、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組織執行。印尼屠共和其他屠殺不同的是,納粹和紅色高棉的屠殺行動因自身軍事行動的失敗,在短時期內即被終止及審判,而印尼屠共行動者則在軍事方面取得勝利,也因此獲得對屠殺行動的闡釋權。電影《印尼共產黨“九三0”叛亂事件》正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它提供了一個研究電影與國家意識形態建構之關系,以及在冷戰意識下第三世界國家如何用法西斯美學原則重塑現實、大屠殺與民族想象這類問題的范本。
當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姆推出令人震驚并廣泛傳播的《殺戮演繹》(二0一二)、《沉默之像》(二0一四),在某種意義上終結了印尼主流社會關于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歷史想象。但是,與二十世紀以來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背景里的多次大屠殺一樣,屠殺本身從未終結。事實上,談論大屠殺是艱難的,對于那些經歷流亡或劫后余生的人,比如經歷過納粹統治的阿多諾、本雅明、漢娜·阿倫特、詩人策蘭以及眾多幸存者而言,尤其如此。就德國納粹種族大屠殺來說,第三帝國的覆滅并不能消除恐怖,二十世紀以來最無厘頭的歷史設想是:假如希特勒贏了……美國作家菲利普·迪克一九六二年出版小說《高堡里的人》,假設德國和日本贏得“二戰”,這部小說先后三次被改編成廣播劇,并在二0一五年改編成被譽為“神劇”的電視連續劇;美國軍事歷史學家彼得·特索拉斯則聯合十一位英美歷史專家寫作了反轉歷史的著作《希特勒勝利》,這些對歷史的顛覆性假想,其實是深入幾代人潛意識的一種恐懼,“希特勒贏了會怎樣”的恐懼不僅包含了對世界秩序之偶然性的擔憂,還包括了對歷史書寫本身的疑慮——極權政治將如何書寫歷史并賦予其正當性?
奧本海姆在印尼第一次見到屠殺者,他感覺自己仿佛見到了活著的納粹,這種感覺大約像是以上那些虛構歷史的現實版:屠殺者洋洋自得,他們界定歷史,將屠殺書寫為正義之戰,被屠殺者則作為十惡不赦的國民公敵形象透過宣傳機器被一再強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屠殺的發動者和執行者占據權力位置,致力于將自己界定的現實塑造成真理——確實,殺人者自己也相信了自己構建的全部現實,并以恐嚇和權力壓制那些微弱的反抗聲音。拍攝于八十年代的《印尼共產黨“九三0”叛亂事件》可以視為印尼軍人政權的歷史正當性訴求以及專制統治時期對屠殺成果的維護,《殺戮演繹》和《沉默之像》正是對這一宣傳的辯駁。除了還原當年的歷史現場,我們甚至可以由這兩部紀錄片復原出意識形態神話的編織過程。兩部影片分別以北蘇門答臘省基層屠殺行刑者(自稱流氓的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成員)和受害者弟弟(一位配鏡師)作為影片主角,前者找回當年行刑的組織成員、領導人,共同演繹過去的殺人現場;后者和年邁的母親一起回憶哥哥被殺的過程,尋找地方屠殺組織相關負責人,希望聽到他們道歉。影片里,奧本海默既未對大屠殺做宏大歷史敘述,也未拍攝發動大屠殺的軍方高層政治人物,但就是在基層行刑者身上,我們看到上層政治意識的完全滲透,上層組織的有效發動。很難用平庸之惡來形容這群行刑者,這些高度政治性的劊子手們并非無思考、不判斷的意識形態機器齒輪上的盲目服從者,而是將個人仇恨(作為底層票販,他們痛恨共產主義者禁止美國電影;作為穆斯林,他們痛恨共產主義者的無神論等等)裹上意識形態外衣(共產主義毀害國家,共產黨是國家公敵)的主動行動人。藏于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暴力及排他性,被賦予合法性,被激勵,被授予權力,是印尼大屠殺發生的基礎。因此,這毋寧說是一場頂層和底層的共謀。endprint
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深刻地論斷,大屠殺并非人類前現代的殘留物,而是現代工具理性文明的一體之背面,現代工業成就與官僚制度組織成就是大屠殺發生的必要條件。盡管后殖民地第三世界國家印尼,其屠殺的現代化技術方面遠遠落后于第三帝國,但它發動底層流氓階層,將意識形態對立轉化為民族和信仰矛盾,由國家機器自上而下進行刺激與思想灌輸,以現實利益作為誘餌,以植根于印尼社會基礎的組織方式有效地執行了對印尼共產黨的滅絕性屠殺,這同樣是現代民族國家某種必然性的一體兩面。
那么,紀錄片如何表達大屠殺這樣一個沉重的主題?極端地說,在大屠殺面前,文明建立起來的所有常識都是虛妄的,沒有什么通常的方式能夠表達大屠殺。我們看到那些震撼性的關于大屠殺的紀錄片都不謀而合地采用了某種超常的寫作方式,某種極致的表達形式,如阿倫·雷乃的《夜與霧》、朗茲曼的《大浩劫》、潘禮德的《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殘缺影像》。在長達九個多小時的《大浩劫》里,朗茲曼拒絕歷史資料影像,重復使用看起來單一的影像畫面,以鏡頭為眼睛,以運動的攝影機為身體,一遍遍重走納粹集中營舊址,親歷者直面鏡頭講述親身經歷,這種質樸和有限的影像手法是對通常歷史紀錄片形式的抵抗:非常規的影片長度、摒棄貌似證據充足的論證方式、不營造假裝作者不干預的客觀感和真實感。潘禮德同樣以自己獨特的影像語言回到歷史,《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讓屠殺者演示當年的場景(這一點和《殺戮演繹》頗相似,而《殺戮演繹》更極致),演示集中營內的生活細節,《殘缺影像》是《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的延伸,以一個家庭的命運貫穿始終,更全面地講述紅色高棉對柬埔寨社會的摧毀,在歷史視野中剖析紅色高棉殺人機器的形成原因。潘禮德超常的形式在于影片里那上萬個上色的泥塑人物和一個個搭建的場景,交織在從廢棄的膠片中拼湊出的殘缺的黑白資料畫面里,以替代已找不到的歷史影像,重構記憶中的生活場景,在此,紀錄片電影史中關于紀錄片之“真實”的觀念被重寫。
《殺戮演繹》《沉默之像》在形式上和以上幾部影片一樣具有僭越性,《殺戮演繹》和《沉默之像》首先是一種鏡像書寫,是讓屠殺者充分自曝的影像記錄。情景再現的方法并非《殺戮演繹》首次使用,但讓當年的行刑者重演殺人場景這種片中片的方式,卻是第一次出現在紀錄片里,片中片并未指向紀錄片這一電影類型的形式實驗,而就是現實本身,直指向在片中拍攝電影的人——殺人者,他們在自導自演的片中片里扮演被殺者。殺人者不斷透過鏡像看自己和被攝影機看,攝影機透過車鏡拍攝殺人者,殺人者看鏡子里的自己,殺人者看影像回放在電視機里的自己,受害者看導演拍攝的殺人者的錄像被剪輯成數段作為影片的基本結構,殺人者恣意狂妄的言行在攝像機、電子產品、電視機上回放……鏡像與回放影像將殺人者的講述和演繹轉變成觀看與審視的對象,兩種表述相遇,構建了一個鏡像與鏡像反射的雙重歷史空間;《沉默之像》則以一個受害者的視角,以他尋找對親哥哥行刑的親歷者結構影片,他試圖讓殺人者談論過去并對過去道歉,我們看到依然位居權力位置的殺人者對幾十年前的行為的得意、對被害家庭的欺凌和強勢,受害者在人身安全焦慮的情形下展開追尋,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奧本海姆讓施害者自證其罪的意圖是明確的,而吊詭之處,也是這兩部影片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實現的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意識形態認識的偏差所造成的對“罪與非罪”的理解——殺人者在最初甚至是將拍攝這部電影視為自我書寫和樹碑立傳。正是因為誤解,奧本海姆的紀錄片獲得一種幾乎無法復制的經驗,多聲部復調敘事使意識形態假象、歷史及歷史在當下生活的幽靈、道德審判、社會深層矛盾、人與現實的想象關系以及人性的復雜都在殺人者們重演過去的場景或對著鏡頭洋洋自得的陳述里無所遮蔽。
與朗茲曼、潘禮德一樣,奧本海姆在影片里并不隱藏作者的存在,他的拍攝誘導了殺人者自曝,也是他的鏡頭鼓勵了受害者追問暴行行刑人,他和眾多被拍攝對象對話,甚至和殺人者探討將證據提交海牙軍事法庭的后果。作者的強烈介入,使紀錄片的真實性問題,也是一個紀錄片根本特性問題躍然而出:紀錄片拍攝者的立場如何影響他的取合?作者選擇什么被看到?在無數親歷者中所選擇的拍攝對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全體?通過回憶復現現場、人物、事件,如何能保證記憶的可靠性?每一個個體在記憶與個人偏向方面的差異,讓我們如何回到對“真實”的認識與界定?而“真實”本身,在哲學意義上依然無解。那么最終,如何認識紀錄片與歷史真相的關系?當然,為避免陷入悖論的僵局,紀錄片觀看經驗通常視這類問題早已解決,用紀錄片書寫歷史,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特征,需要遵循時間容量與影像表現力的限定,紀錄片的真實是在被默認的揀選性、有限性的基礎之上。也許比“真實”更確定也更緊要的,是“誰在說”。無論是親歷過災難歷史的朗茲曼和潘禮德(朗茲曼參與過對納粹的游擊戰,潘禮德從紅色高棉勞改營逃出),還是作為旁觀者在印尼做田野調查研究的奧本海姆,他們的認同,首先是建立在對無辜受害者的同情之上,是以不與任何強權政治共謀的、不進行意識形態編碼的、在雞蛋與石頭碰撞的荒誕世界里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的、為無法書寫不能發聲的被壓迫者的、在政治想象與權力控制之外真正開始記憶的……一種超越政治發自基本人道主義的良知寫作。這些作者的身影毫不隱藏地介入事件的紀錄片,恰恰是要表達作者的看,與那些無人稱、全知視角、精心縫合意識形態話語的宣傳影片相比,這樣的影片從根本上抵制了法西斯美學,它們將判斷交給觀眾。
《殺戮演繹》和《沉默之像》的現實影響顯然是不可低估的,對于影片中的人物,他們在重演當年的情景時,多次意識到“我們才是殘忍的一方”,影片的主角最終發出了仿佛來自良心的某種不安,他對支撐自己幾十年的正義的信念產生了懷疑;而對印尼社會,這兩部影片所產生的撼動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意義上,紀錄片所拉開的,是一個文化戰場,歷史在這里被審判。在這個戰場里,那些匿名參與影片拍攝的印尼本土電影工作者是不能忽視的存在,我們毋寧說是,被壓抑的歷史自身需要被講述。
二0一六年六月定稿于棲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