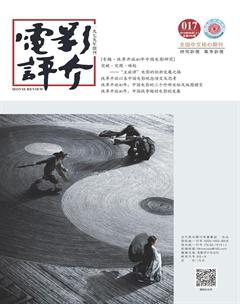改革開放40年:中國電影的三個外部坐標及版圖嬗變
孫佳山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歷史帷幕的開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同時,中國電影的外延也在這一波瀾壯闊、波詭云譎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變化和調整,這種外部空間或外部他者的變遷,不僅直接影響著中國電影版圖的疆界,對于中國電影的內涵也同樣產生著既是潤物細無聲,也是蝴蝶效應式的影響。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好萊塢電影、回歸前的香港電影,這三者共同構成了標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外部的基本坐標,它們在改革開放已經走過的40年偉大歷程中的不同歷史階段,對于中國電影的內涵和外延都產生了復雜的作用和影響。
因此,就作為中國電影的外部坐標的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好萊塢電影、回歸前的香港電影,進行重新回望和梳理,對于從整體上重新審視和反思中國電影,在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教訓,以及預判和展望下一歷史周期的發展方向,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和警示意義。
一、 從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到FIRST青年電影展
1988年,《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是中國電影獲得的第一個國際A類電影節的頂級獎項;但其在給中國電影的“第五代”“加官進爵”的同時,也為“第五代”作了“蓋棺定論”。因為歷史已經殘酷地證明,他們的起點也是終點——“第五代”自身的藝術經驗和其所依托的特殊的歷史時期的不可復制性,不僅沒能再維系“第X代”這種虛妄的代際傳承,同時也沒有在隨后的1993年、2000年、2002年,中國電影在制作、發行、放映等領域不斷加快的市場化、產業化、院線制改革步伐等不同歷史節點,拓展任何具有現實操作性的藝術探索的有效空間。
因此,只有當歷史拉開了足夠大的距離,從改革開放40年的整體觀照出發,我們才可以更進一步地呈現和挖掘在那一歷史階段中國電影的結構性內在分裂。顯然,除了碩果僅存的《英雄》等幾部影片之外,“第五代”并未在中國電影的市場化、產業化藍圖內,獲得穩定的、可持續的票房空間。中國電影市場化、產業化改革之所以在這二十余年里繳納了高昂的歷史學費,付出了令人咋舌的行業代價,就是因為這一本末倒置的悖謬結構在中國電影的市場化、產業化改革的起步階段就已埋下糾結的歷史伏筆。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全方位深入,中國電影外部坐標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著時代性的變遷,并直接影響著其內部結構的重新整合,這種尷尬的局面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后終于有所改善。2011年之后在西寧開始成為穩定沿襲和規模的FIRST青年電影展,成為打破了這一結構的引爆點,而且這一引爆點的動力結構正是來自外部空間或外部他者的牽引。由于“提名—入圍”等專業評價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選片范圍的廣泛拓展,《心迷宮》等高品質代表作的不斷涌現,FIRST青年電影展“意外”地成為了匯集海峽兩岸眾多青年導演、編劇、演員的中國藝術電影創作實踐的樞紐。在《八月》斬獲2016年臺灣金馬獎最佳影片之后,2017年更是有8部曾在當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進行過展映的影片入圍臺灣金馬獎;而且這種影響和輻射是雙向和均等的,來自臺灣的《川流之島》《強尼·凱克》,也正是通過在FIRST青年電影展嶄露頭角,才在臺灣金馬獎獲得華語電影主流的進一步認可。[1]
不難發現,在改革開放這一風起云涌的大的時代浪潮中,中國電影市場化、產業化改革在20年左右的盲目摸索之后,也在快速地新陳代謝和更新換代,并終于為在其市場化、產業化的初葉曾有著濃墨重彩一筆的藝術電影的創作實踐,找到了一個相對符合自身國情和特點的,并能夠為整體性的產業結構所接受和吸納的內部循環機制。
二、“北上”的香港電影,為中國電影帶來了什么?
早在1974年,許冠杰、許冠文兄弟的港式草根喜劇片《鬼馬雙星》一炮走紅,使得香港電影終于擺脫了粵劇電影和古裝武俠片的束縛,進入到了專門為以香港為中心的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新興中產階級,制作商業類型片的香港電影“新浪潮”。而且,在那一階段的香港電影如日中天之際,恰好也正是改革開放大幕開啟的時刻,其在內地大眾文化的潛在影響之深,對于當時還處于青少年階段,但今天已經活躍在中國電影舞臺的很多內地中青年導演、編劇、演員,都有著烙印般的影響,乃至是那一代人的一部分集體無意識。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由于地緣格局和話語空間的結構性歷史變遷,尤其是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等一系列協議、協定的制度性框架,香港電影曾經的表意策略和文化功能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調整。香港電影與中國電影的關系,也發生了時代性的翻轉。從那時起,香港電影拉開了大規模的“北上”的序幕。
只是從那之后的10年左右時間,香港電影的“北上”之路并不順暢。由于內地電影市場在2002年開始實行徹底的院線制改革,內地電影市場的規模、體量開始爆炸式增長,在票房平地驚雷式的迅速躍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時,中國電影版圖也在潤物細無聲地發生著跨時代的階躍,內地的電影觀眾也由傳統的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二線城市開始向三四線城市和主流媒介基本不了解的更為遼闊的眾多縣級市擴散,這一切都遠遠超出了香港電影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原有認知結構。
直到2005年之后的《神話》《寶貝計劃》等影片的出現,香港電影才開始穩住陣腳,并逐漸找到適應內地電影市場的共振節奏。經過隨后《霍元甲》《投名狀》《十月圍城》等影片的不斷探索,2013年,真刀真槍地處理內地公安題材的《毒戰》的出現,標志著香港電影開始真正有機地融入到中國電影的內部結構。一直號稱要“北上”賺錢的香港電影,還是通過其最為擅長的港式警匪片類型找到了突破口。盡管還是有一部分香港電影人將《毒戰》的成功,歸因于是所謂的突破了內地影片的審查限制;但只要對中國電影稍有基本認識,就能充分意識到該片真正的示范意義,即香港電影的成功商業類型元素,在香港回歸近20年之后,終于匯入到了中國電影的核心和主流——近2年來的《湄公河行動》《非凡任務》《紅海行動》這些新階段的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電影的成功商業類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講述這個年代的中國故事,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因此10億、20億、30億的票房蛋糕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從目前看,香港電影在已經完成了持續10年左右的階段性調整之后,依托內地“坐二望一”的巨大市場空間,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俠片、港式愛情片等為代表的幾種成熟的類型影片,開始逐漸摸索出了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三、 好萊塢電影再度盤整,中國電影如何抓住歷史機遇?
就像并不存在一個本質化的好萊塢電影一樣,好萊塢電影內部也并非一個同質化的整體,其也有鮮明的周期性發展的特征,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他們也并沒有始終都在統治著世界電影票房,也存在著階段性的內部調整和整合。如前文所述,香港電影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葉,曾經獲得至少是區域性的廣泛影響的一個重要外部原因就在于,從80年代初期到《侏羅紀公園》《玩具總動員》《泰坦尼克號》背后的數字化革命浪潮,也就是今天被習以為常的好萊塢特效大片時代之前,好萊塢電影在全球范圍處于相對弱勢,這才使同為商業類型片的香港電影更接大中華區“地氣兒 ”的優勢得到不斷地放大。
經過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數字化革命浪潮,好萊塢電影再次統治了世界電影票房,并在2009年的《阿凡達》達到了最高潮。這一大致15年左右的時段是如此漫長,因為它們一度都是中國電影關于電影認知的凝固常識。然而,也同樣是在2010年前后,內置于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的輪轉和重塑,美國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也隨著美國國力的興衰而亦步亦趨,在《拆彈部隊》等影片之后,好萊塢電影的表現力和影響力出現了全球性的日漸衰退。好萊塢電影進入到新一輪調整周期的標志,正在于以奧斯卡金象獎為代表的,即“高舉高打”式的《黑鷹墜落》《拯救大兵瑞恩》等我們曾耳熟能詳的風格、套路,開始逐步調整到眼下的無論是《水形物語》《三塊廣告牌》,還是《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逃出絕命鎮》等,從女性題材到同性戀題材以及種族主義題材等一部部反思式、悲情式的,帶著濃厚藝術電影氣息的影片矩陣。長久以來,好萊塢電影一直與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有著商業與藝術的明顯區隔;但近年來,在奧斯卡金象獎中卻出現了明確的藝術電影的苗頭。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好萊塢電影正在調整和校正自己的表意區間。
無論是“黃金時代”,還是“新好萊塢”,好萊塢電影都有著扎實的商業類型片積淀,可以為不同年代的電影觀眾提供合格的文化娛樂消費產品。堅實的商業類型片基礎,是好萊塢特效大片能夠收割全球票房的真正土壤。對于改革開放走到第40個年頭的中國電影而言,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情境:來自三四線城市和廣大縣級市的、40歲以下的、未受過高等教育、收入不高、也并沒有穩定工作的新的電影觀眾,既不是相對精英的迷影文化主體,也不是適用于好萊塢電影框架的新興中產階級。或者毋寧說,好萊塢也未曾處理過如此復雜的文化情境,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好萊塢特效大片,對于21世紀第二個十年浮出歷史地表的“小鎮青年”,并不具有曾經所預想的摧枯拉朽的殺傷力。面對這樣的市場格局,中國電影產業能否抓住好萊塢正在盤整的戰略機遇期,在內部實現商業類型規模化的突破,通過對不同題材進行不斷類型化的推陳出新,向三四線城市和廣大縣級市的那些還在不斷增長的新的電影觀眾,批量生產具有穩定質量、品質合格的電影文化工業產品——即便是放置于整個世界電影史而言,這都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戰。
結語:40年后再出發,歷史深處的挑戰
眾所周知,從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開始,我國就已經明確將文化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型產業來培育,包括電影在內的我國文化產業的各個門類,都將迎來一個持續性的快速發展窗口期,中國電影的內涵和外延也注定還將被新時代所改寫和重構。
在此刻的當下,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風云變幻,可以直接影響中國電影的新的外部坐標正在生成。當下被熱炒的中美貿易戰,不過是正在重構中的全球版圖的一個序曲,隨著民族國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調整各自不同層面上的疆界,中美間的貿易摩擦早晚都會涉及到影視領域。作為公平、開放的自由貿易的堅定踐行者,我國會分階段實現2001年加入WTO時的相關承諾,好萊塢電影也不可能無限期盤整。如果說數以億計的“小鎮青年”,這些中國電影的新觀眾構成了中國電影內部的新維度的話;那么在未來,當中國電影的新的外部空間或外部他者,清晰地浮現出歷史地表后,無論對于中國電影,還是對于整體性的中國文化產業而言,都將是一場恐怕會延續在整個21世紀的歷史性挑戰。
參考文獻:
[1]李行.FIRST青年電影展的11年:回歸電影本體[N].中國新聞周刊,2017-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