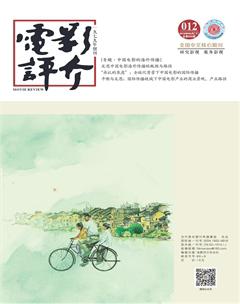鄉村轉型與變遷中的脫貧敘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有7億人實現聯合國標準下的脫貧。貧窮、戰勝貧窮,以及觀察、體驗減貧力量,是文藝創作的主題。劇情片中,張藝謀“關于農村、貧窮及文盲問題”的《一個都不能少》(1999),楊亞洲執導的《美麗的大腳》(2003), 宋海明執導的《水鳳凰》(2008)等,都以較高藝術水準或極大教育意義被觀眾記住。
在展現中國貧困問題的影視紀錄片作品中,有前不久在國際上聲譽甚佳的電視紀錄片《為什么貧窮》系列之《出路》(陳為軍導演)等。今年3月上映的電影紀錄片《出山記》(焦波執導),因拍攝者“嫻熟地運用紀實美學的方式,捕捉和呈現了大時代背景下真實的社會生活”[1]而備受關注。這部紀錄片“讓人們看到數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脫貧故事,這面鏡子照得如此生動”[2],也讓我們看到了鄉村轉型與變遷中的艱難現實和熱烈渴望。
一、 思考“世界的另一面”
《出山記》拍攝于貴州省務川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此地流傳著一個順口溜:“為人不住高山山,秋冬四季把門關,一天三頓包谷飯,腳上烤起火斑斑。”描繪了石朝鄉地勢高寒、生產落后、群眾窮困的歷史圖景,在極端窮困年代,干部進鄉都會被這里的貧窮“同化”。[3]
本片把鏡頭對準大山深處的底層貧民,通過呈現貧困這種特殊環境里的人類活動與集體情緒變化,表達了貧困群體在尋求改變過程中的內心糾結與生存矛盾。電影所描述村莊的百姓生活變遷,能給人以現實世界中貧富懸殊的真實質感,其影像展現的山里境況,與觀眾日常接觸的現代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出山”所表達的思想變革與生活方式轉變,為觀眾打開了一扇思考當下鄉村變遷的觀察窗口。
不管對貧困群體生存面貌是否有所了解或體驗,觀眾都能夠透過影片管窺“世界的另一面”——貧困境地所形塑的頑強人格,久經掙扎后,依然對外界生活產生強烈的排斥甚至恐懼心理。雖然結局“皆大歡喜”,但在影片之外,留給片中人物和大山之外觀眾的憂慮,恐怕并未隨著對電影本身的贊譽而消逝。
當然,在主旋律輿論影響和精神塑造層面,《出山記》流淌出激勵人心的精神營養,釋放出精準扶貧政策引導正確、基層干部干勁足方法對等可在更大范圍內產生作用的引導性信息。影片以一個村莊居民通過不同方式實現脫貧為主線,來闡釋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的政治主題。從一定區域和范圍內的反響來看,的確成功強化了大漆村及基層干部申修軍和村民申學科、申周等人在“出山”路徑選擇上的榜樣力量。
宏大主題用普通人的小故事來支撐,才更有說服力。這種說服力來源于“普通人的故事”中所蘊含的真實情感力量,如用唾罵來體現人物之間的矛盾,用一家人對“出山”后生活前景的爭論來體現貧困群體代際沖突,實際上都是普通人在變與不變之間進行選擇的情感常態。《出山記》的一個折射點是,現實生活里,正是因為需要深刻扭轉、改變貧困山區民眾對外界抱持的焦慮與排斥等情感常態,才使得對現狀進行突破變得十分棘手。
扭轉與改變的過程,既紛繁復雜又充滿激情,或存在人性較量與善惡交鋒,或遭遇維持“壞狀態”的固化思維,從而在變與不變之間形成強烈對抗。因此,遏制住持續“變壞”的歷史慣性,比如通過干部積極作為促進政策落實、消解貧困民眾慣性的小農守舊思維,就可以認為是積極變革的力量取得的勝利。也正因為有這樣復雜的變化歷程,所以《出山記》的小人物故事才令人動容與深思。
二、 探討人與自然共生關系
在一定范圍內,貧困與環境惡化往往有著天然聯系。思考人類與自然的相處之道進而擺脫貧困,是《出山記》等諸多記錄片作品所傳達的重要社會責任。
輿論所宣稱的“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區”,其特征之一是水土流失等環境破壞嚴重,生態修復難度大。人們在這些地方維持生存的基本方式,是簡單從土地上獲取生活資料。長期的濫砍濫伐、刀耕火種,導致貧困落后與生態損害之間出現惡性循環。因此,在有限的環境承載能力上,人類如何才能有更高的生存質量,如何才能通過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貧困人群生存狀態改善,是需要深度思考的問題。
從《出山記》的場景描述以及其他媒介形式提供的信息看,大漆村貧困群眾至少面臨三大困境。首先,土地耕作收益低。很難從貧困地區發展歷程中梳理出致貧原因為普遍不勤勞這種結論,恰恰相反,祖祖輩輩深居山中,在難以實現現代化耕種方式的山旮旯謀求生存,本身就是勤勞的證明。但與外界富裕生活相比,他們從貧瘠土地上獲取的財富實在不值一提。其次,交通閉塞導致資源變現困難。這是大多數邊遠貧困農村的共同難題。因為自然地理原因導致交通不暢,進出兩難,長此以往就形成“死守一畝三分地”的生產生活習慣,鮮有主動尋求改變者。因為村民零散居住,考慮到高昂的道路建設成本和低效的道路功能,難以產生較強市場激勵與政績激勵,不少地方因此變為地區整體脫貧進程的“最后一公里”。
最后,久居深山形成的守舊思想難以破除。山里貧民對走出大山謀求生路的憂慮與排斥,是很自然的一種自我保護,加之教育欠缺,對新事物缺乏足夠認識,突破守舊思想防線十分困難,所以才有申修軍苦口婆心勸導村民的場景。
農村依托自然資源而存續。在反貧困過程中,不管是政府機構還是民間組織,所付出的努力大都集中在兩方面:變革依托資源稟賦進行財富挖掘的生產方式、變革貧困民眾在現有環境中的認知行為和生存模式。在當前精準扶貧政策語境中,政府部門誓言以“啃硬骨頭”的決心,希望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強化教育投入、產業培育等途徑,改變耕種效益低、交通環境差的狀況,促進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出山記》所記錄的搬遷進城與農村市場培育過程,正是政策力量推動下的生存空間和思維理念“大遷徙”。這種變革軌跡也反應了多數貧困群眾共同的脫貧經驗。
由政策推動的“大遷徙”,更進一步觀察,也是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有效方式。環境友好的一層內涵,是人類活動沒有對優良生態構成威脅,自然生態保持著本身所具備的生物共生特性;當前政策語境中易地搬遷所蘊含的變革含義,通常就是交通通訊、生產技能等要素大改進,以及生產生活空間區域大轉換,因而從另一層面看,人類本身需要在自然環境中獲得生產持續進步與生活不斷改善的資源營養,如果環境承載能力超過了人類所需,資源營養的吸取就需要通過改進交通、通訊、生產技能以及區域大轉變來實現。
換條道路,換個活法,是《出山記》所表達的樸素情感。這需要“大遷徙”來幫助實現。“大遷徙”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理念,兼顧了要素改進成本與生產生活區域轉換二者之間的融通。
三、 脫貧路上的人文關懷
作為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最佳作品,《出山記》展示了貧困大山里脫貧攻堅、波瀾壯闊的畫面;講述了貧困的山民翻越腳下大山,戰勝曲折大山的故事;《出山記》告訴我們,貧困路下的山再高、路再遠,只要攝像機捕捉下來的角落,都不會是脫貧路上被遺忘的遠方。[4]
與商業記錄影片如《我們誕生在中國》的最大區別,在于《出山記》沒有刻意追求擬人化和象征性表達方式,而用直白畫面來表現時代洪流中邊緣人群的“求生”過程。直面人心的敘事手法,很好體現影片的人文關懷,呈現出維護貧困群體話語權的藝術力量,村民面對鏡頭時十分真實自然,甚至讓人感覺不到攝像機的存在,如果說攝像機是一個脫貧攻堅過程的“見證者”,那么對于大漆村的村民來說,攝像機的存在反而起到了喚醒農民主體意識的作用。[5]
政府的政策導向,是要求把各方資源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合理傾斜,促進城市與農村資源相互流動,“使過去在農村被抵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6],從而改變貧困人群的物質與精神面貌。而藝術作品的魅力,在于通過片段式表達方式,把這種面貌改變本身及其過程、把尚未被政策關注的部分呈現出來,把人物在變革過程中的內心活動表現出來,為人們更全面、更深刻認識社會現實創造一個審視維度。
《出山記》立體式呈現了一個村莊貧困群體的內心掙扎,甚至一家幾代人對“搬出大山”的態度對立,不少人對政策的懷疑、對基層干部勸導的反感、對走出大山后自身生存能力的不自信等等,都以情緒宣泄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展現在大銀幕上。
這種情緒宣泄中的意見與表情,也是底層民眾最質樸的生存態度。他們需要公正、誠實甚至“榜樣引領”,來應對“出山”后的不確定性。影片給足了這種矛盾沖突充裕表達空間,把貧困群眾最真實一面表達出來,構建起一個關照內心和情緒交流的藝術通道,展示了走出貧困前夜的變革力量。作為文藝創作,《出山記》“正視和承認利益訴求和主觀感受的多樣性”,的確沒有必要掩飾這種多樣性,因為“多樣性并不意味著對主流價值觀和社會統一體的消解,對個體的關注也并非一定是對集體的弱化”。[7]
信息不對稱導致對變革產生憂慮甚至恐懼,是普遍的社會情緒。久困于貧困境地的民眾,缺乏對自身憂慮、恐懼進行充分表達、釋放的通道與載體,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缺乏更趨向于現代化的生存手段和技能,另一方面是外界所提供的表達機會,難以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顧及這個群體。電影記錄片這種傳播媒介,也是“關于社會領域的各種思想和觀念傳播的一種強大動力”[8],所以,為“被遺忘的遠方”填補情緒表達的信息鴻溝,本身就是人文關懷的具體行動。
結語
從社會變遷角度看《出山記》的時代背景,正是“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劇烈變化時期。這種轉向意味著一系列習俗、制度和社會關系的巨大變革,大規模人群離開村莊,以非農為生,并且可能不再會回到鄉村,這樣一次轉型具有不可逆性,而所謂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化,就是中國從原來的鄉土社會轉向城鄉社會。[9]
包括易地扶貧搬遷在內的城鎮化道路,應該是這個轉向和變革在貧困地區的非常關鍵的方式。各方力量努力促進尚處深山之中的貧困群眾參與這場“大遷徙”、參與這場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鄉土變革,顯然不僅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能從整體上推動社會轉型進步。《出山記》用紀實眼光和藝術手法,為大眾思考這種轉型提供了一面“鏡子”,呈現了鄉村變遷的進步特征與時代力量。
參考文獻:
[1]梁君健.《出山記》:精準扶貧的影像記錄[N].光明日報,2018-05-03(16)
[2]聶寬冕.白巖松.《出山記》是生動的扶貧“鏡子”[N].北京日報,2018-01-27(10).
[3]鄧國超,岳振.務川石朝春來早 極貧鄉鎮作戰忙[J].當代貴州,2018(10):24-25.
[4]孫遠桃.《出山記》獲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記錄單元最佳作品獎[EB/OL].人民網,(2018-04-18)[2018-06-15]http://gz.
people.com.cn/n2/2018/0418/c222152-31475774-2.html.
[5]胡譜忠.“出山”與新時代鄉村振興之路——紀錄片《出山記》觀感[J].中國民族,2018(4):67-69.
[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邁向高質量發展:戰略與對策[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169.
[7]梁君健.《出山記》:精準扶貧的影像記錄[N].光明日報,2018-05-03(16).
[8](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社會理論與大眾傳播[M].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40.
[9]劉守英.從轉型角度審視農民、土地和村莊的關系[N].21世紀經濟報道,2017-12-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