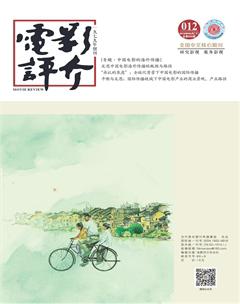科技異化、生命平等與生態主義
蔣瑩 李潔
自1993年侏羅紀系列的第一部《侏羅紀公園》上映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22年。《侏羅紀公園》的出現可被稱作是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作品,它填補了電影作品對于“恐龍”這一物種的表現,而隨著電影的熱映,《侏羅紀公園》更是在全球掀起了關于恐龍的熱潮。雖然從今天來看,《侏羅紀公園》系列中對于恐龍形象的還原還存在很多錯誤,但瑕不掩瑜,《侏羅紀公園》系列的開創之功,絕對不可忽視。同時,該系列自誕生以來,就以生態主義作為主旨,雖然是商業片,但卻兼有大量的人文主義關懷和理性批判,因此影片能在擁有娛樂性的同時,又不失內涵。
《侏羅紀世界2》是電影《侏羅紀公園》系列的第五部,劇情承接上一部《侏羅紀世界1》的內容繼續展開。從整體故事來看,《侏羅紀世界2》的故事在延續前幾部敘事主題的同時又有大膽地創新和深入,在《侏羅紀世界2》的故事中,諸多主題的探討被愈加重視起來,因而對于主題進行探討的劇情在整個影片中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分量。而通過《侏羅紀世界2》對于前作的再延續,我們看到,《侏羅紀世界2》中存有大量進行隱喻的鏡頭和劇情敘事,而總結這些主題,可以分為以下三點。
一、 科技的達摩克里斯之劍——科技的異化主題
科技的異化這個主題一直是電影界經久不息的探討對象,早在阿道夫·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中,就已經對科技的異化做出了極為深入地探討。在《美麗新世界》的故事中,科技對人類社會的異化已經到了一種極端的程度,人類視母胎生子為惡事,認為這是一種臟污的存在,在《美麗新世界》的科技社會里,所有的新生兒都經由工廠流水線制造,而被工廠流水線制造出的這些新生兒,自出生起,就被規定了社會分工,其智商也從胚胎開始就已經被規定好了。在作品中,科技對于社會的異化進一步對人性造成了扭曲,故事中的野人,是一個突然沖入這個新世界的外人,他在孤獨中走向瘋狂,最后更是在瘋狂中走向了死亡。這種科技的濫用造成的異化可以說令人毛骨悚然,而在科技高速發展的現在,人類對于科技會被濫用的焦慮越發增長。針對這種焦慮,近幾十年來,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電影在其敘事主題中表達了對科技濫用后果的反思,這其中比如改編自菲利普·K·迪克《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這本小說的電影《銀翼殺手》便講述了一個人類制造的復制人逃回地球,試圖在銀翼殺手的追殺下求存的故事,克隆人存在的意義一直是影片中揮之不去的未解謎題。此外又如電影《逃出克隆島》,在陰郁變換的場景中最終讓主人公意識到自己是被制造用來提供替換器官的克隆人的事實。在這些電影作品中,人類無一例外都對科學進行了無節制的濫用,這種濫用,無一例外最終都造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主題的探討使得敘事內容被凝聚在一起,而由這個主題所產生各種探討,也一直令觀眾著迷不已。
作為具有批判意義的電影系列,《侏羅紀公園》系列一直貫穿著對科技的異化這個主題的探討,在電影《侏羅紀公園》中,人類從琥珀封存的蚊子中提取到了恐龍的DNA,并由此制造出了大量恐龍,電影中的侏羅紀公園也由此成型。但人類終究會因自己對待生命的傲慢和隨意而付出代價,在這一部電影中,侏羅紀公園中的恐龍最終失去了控制,一場由暴虐暴王龍掀起的追逐戰由此爆發,而在電影的結尾,侏羅紀公園被政府無限期封閉,喧鬧一時的恐龍制造也落下了黯淡的帷幕。
《侏羅紀世界2》較之前作對這一主題有了更為深入地探討,在本作中,小女孩梅西成為了承載這一主題的重要人物。梅西是一個克隆人,但從《侏羅紀世界2》目前展現出的內容來看,梅西并不僅僅是一個克隆人那么簡單,梅西應該是一個混有恐龍基因的“混血種”,因此在故事結尾,也是梅西選擇了放生恐龍,恐怕也并不是僅僅出于人天性的同理心,而是出于另一種更加可能的原因,她體內的恐龍基因促使她做出了放生恐龍的選擇。于是,在繼擅自制造已經滅絕的生物之后,人類再次擅自觸碰了生命的禁區,充當了造物者的角色,而這次,卻是更加危險的對人類自身的改造。對這一生命禁區的觸碰,再次對人類造成了無盡的惡果,小女孩梅西的選擇讓整個人類社會都被重新拉入到侏羅紀世界之中,在未來即將發生的故事中,必然是人與恐龍的生存戰,突破了原系列島嶼的模式,本作大膽的將人與恐龍的矛盾沖突地點升級到了整個人類社會,在這場注定曠日持久的沖突中,人類肯定會付出比之此前更加慘重的代價。
二、 恐龍角色的“人類化”處理——生命平等的主題
在好萊塢的電影中,讓動物擁有“人性”,或者說讓動物趨向“人類化”是屢見不鮮的創作手法,這種創作手法能最大程度上的引起觀看者的共鳴,造成極為有力的共情效果,最明顯的便是那些本身會說話的動物面孔而擁有人類內核的動畫類電影,這類電影比如前期大熱的《瘋狂動物城》《馬達加斯加》《海底總動員》等,但與《侏羅紀世界2》還不同,前面舉例的這幾部電影它們的主角是動物,但其內核還是人類的內核,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披著動物皮的人類電影”。而在本作中,恐龍的形象是與前者不同的,大多數的恐龍仍然是冰冷的動物形象,它們并不具有典型的人類情感和人類行為,而是個別的恐龍在發展中逐漸展現出了“人類化”的一面,與《侏羅紀公園》的前三部對比,本作在恐龍形象的豐富上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對于觀眾們來說,恐龍不再是蒼白的單一形象,而發展為更加復雜,更加多樣有個性的角色。這種創作手法顯然可以讓觀眾更好地共情,而這種共情讓影片的部分劇情趨于溫情化,敘事節奏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被拖慢,這也造成了部分追求驚悚感的觀眾的耐受不良。
在《侏羅紀世界2》的故事中,部分充當重要角色的恐龍被進行了“人類化”的處理,觀眾可以在主要恐龍角色的身上看到人類情感的縮影。比如在“末日大逃亡”的最終,那只因沒有登上船的腕龍,它死前的哀鳴便是一種極為人類情感化的處理,而本作中的布魯則更是展現出了非凡的智商,對人類的脆弱展現出同情和保護,此后更是和男主人公歐文建立了深刻的羈絆,這種羈絆明顯帶有著人類式的情緒。和日常寵物相處模式不同,布魯的形象則更接近一個“人”的形象,電影結尾處布魯與男主人公歐文的互動和最終放棄跟歐文離開,則顯示出了它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有個體思維的存在。此外,本作中的暴虐迅猛龍,這一由人類混合不同基因后制造出來的新種恐龍,產生了非同尋常的“人類化”表現,在雇傭軍頭子進入籠子試圖拔出一顆暴虐迅猛龍的牙齒的時候,暴虐迅猛龍竟驚人地展現出了“戲弄”“欺騙”這種人類才會出現的行為,相較于此前《侏羅紀公園》系列中的獵食者恐龍形象,本作的恐龍形象可以說變得更加多面且更加“人類化”。恐龍在本作中真正成為了也能表達喜怒哀樂的言說主體,雖然不免有人類自我的感情擅自加諸動物身上的成分在,但這種對于恐龍角色的“人類化”處理,讓觀眾意識到人類并非唯一的擁有智慧和感情的群體,這無疑是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的批判,進而強調生命平等這一主題。此外,羅伯特·麥基在其《故事》一書中寫到:“真正的選擇是兩難之擇。它發生于兩種情境。一是不可調和的兩善取其一的選擇——從人物的視點來看,兩個事物都是他所欲者,他兩者都想要,但環境迫使他只能二者擇一。二是兩惡取其輕的選擇——從人物的視點來看,兩個事物都是他所不欲者,他一個也不想要,但環境迫使他必須二者擇一。”[1]在最終毒氣遍布的地下室里,也最終產生了一個兩難之境:放走恐龍,整個人類社會都將自此陷入險境;不放走恐龍,那么這些生命就將死在主人公一行人的面前。在人類的傲慢與對生命的輕視的前提下被制造出來的生命,卻要接受這種命運,實在是對良心的一種拷問,而影片最終對于所做出的決定,也能體現出對于生命平等這一觀點的表現。
三、 人與恐龍的關系——生態主義主題
事實上,和生命平等的主題并行的還有生態主義的觀點,生態主義強調非人類中心主義,“人們首先從自己與寵物的情感認識到人與動物之間可以和諧友好的相處,進而擴展到人類更應該與野生動物建立互相幫助、和平共處、和諧共生的美好關系”[2]。生態主義從最初的“動物福利論”發展到現今,對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做出了相應的界定,人類應當與自然和諧相處,應當尊重自然規律,而不是肆意破壞自然的規律。2017年上映的《猩球崛起3:終極之戰》中也有對于生態主義的表達,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掠奪,對于大猩猩的濫殺,對于自然環境的破壞,所有的這一切都最終反作用到了人類身上。與之類似,《侏羅紀公園》系列對于生態主義的表現也可謂貫穿始終,《侏羅紀》系列中試圖征服改造自然,試圖枉顧生命發展的客觀歷史,擅自復制出早已滅絕的恐龍,這便是一種違背自然規律的做法,而在《侏羅紀世界2》這部中,對這種生態主義的主題有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前面已經說到,影片最后,小女孩梅西放出了那些恐龍,因而使得人類社會自此重回侏羅紀時代,人類的這種違背自然規律的做法讓整個人類社會都陷入了惡果的承擔之中。人類試圖征服自然生命的做法最終將人類從生物鏈的頂端拉下,造成了恐龍入侵的后果。而在故事中,人類出于自身享樂的目的重新制造出了恐龍,然后又把這些恐龍投放到公園里,用來牟利,然后在公園不能繼續牟利之后,人類又試圖將這些恐龍培育成戰爭機器以用來牟利。影片中克萊爾和歐文以為是前去島上拯救恐龍,結果卻被關在了公園管理處內,差點死在火山爆發中,而實際上和他們一起的雇傭軍是被雇來抓捕恐龍用來拍賣的,而影片中的暴虐迅猛龍,就是一頭專門被制造用來進行戰斗的恐龍,人類再次枉顧生命的自然發展,將不同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妄圖制造出一個聽話的戰爭機器,這種行為無疑會讓人類自食惡果。而影片無疑是同意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人與動物應該和諧相處這個觀點的,影片中布魯和歐文之間建立的關系,便是這種和諧關系的一種代表,而影片最后的開放式結尾,讓未來人與恐龍的關系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羅伯·特麥基.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84.
[2]丁愛偉.從沉默的客體到言說的主體——“新家庭溫情電影”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