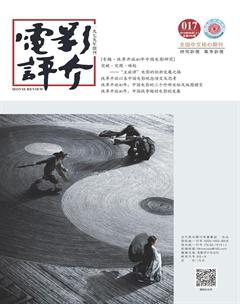中外影視中的失憶癥隱喻研究
常凌
不管是成功學中宣稱的“實現自我”,還是媒體常見的強調“尋找真正的自我”標題,強烈的“自我”意識對于當代人來說,似乎是一個“與生俱來”之物。福柯的《詞與物》宣布了“人”之死和“自我”的虛幻性。他說:“對于人類知識來說,人既不是最古老的問題也不是最常見的問題……正如我們思想的考古學很容易證明的,人是一個近期的發明。而且他或許正在接近其終結……人將會像海邊沙灘上畫的一幅面孔一樣被抹掉。”[1]福柯還宣稱:“在古典知識中不存在人。在我們發現人的那個地方存在的是表現事物秩序的話語的權力,或者說表現事物秩序的詞語秩序的權力。”[2]他對“自我”的評判是:“我們的自我是面具的差異。”[3]“自我”是面具的差異,意味著“自我”對他人的依賴和與己身的分離性、虛幻性。福柯對于“人的自我”這個概念的分析體現了強烈的批判性,“自我”是一種想象的權力關系,是需要得到清理的建構性之物。
一、 自我的建構性
“自我”的確是建構出來的,“自我”也是各個領域形成權威、霸權的最早最深層的源頭機制。從微觀層次上解構現代社會的霸權,以便把人從制度、結構、實踐、話語等微觀的政治和壓制中解放出來并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任務。技術、意識形態等文化力量對人的異己統治是內化于“自我”之中完成的。通過作為個體自覺主動進行思考、行動的動力源泉的“自我”發生異化的機制是彌漫無形的,像一個看不見的巨大磁場——或者說是無數分散變動的小磁場更為恰當。
“自我”是時代自戀人格的核心,這也是美國學者克里斯多夫·拉斯奇批評自戀主義社會的危害不在于它的反動性而在于它的腐朽性,不在于它的攻擊性,而在于它的迷幻性的原因。但是,這里也要為“自我”正名,盡管經由“自我”機制完成了很多對主體的異化,但是這不意味著“自我”沒有存在的必要,是要進行完全否決的,“自我”也是主體通過反抗起作用的機制,“自我”更像一個場所,各種力量進行爭奪較量的場所。但是,“自我”的貌似理性、貌似天然合法性、隱蔽性和強烈剝奪性,尤其是在“自我”形成時就存在的異化性使它極其容易被權威深層占據,辨析“自我”的中立很難,因此,盡管理論上不能否定“自我”,具體分析實踐上須以批判態度為主,謹慎細致的來考察“自我”的深層力量流動和那些隱蔽、變形的主體抵抗力量的表現。本文的目的正是以失憶癥主題的影視劇為具體對象進行對“自我”的描述、勾勒、剖析和批判。
與影視劇中失憶癥的泛濫不同,現實生活中失憶罕見。心理學認為,記憶是既往事物經驗的重現,是一種非常基本的精神功能。俗稱的失憶癥在醫學上稱為記憶障礙,分為器質性和心因性兩種病因。在近期熱播的內地電影《深海尋人》《記憶碎片》《記憶大師》,電視劇《情深深雨蒙蒙》《仙劍奇俠傳》,香港電影《異度空間》等作品中,主角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失憶癥,在臺灣電視劇《王子變青蛙》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失憶。失憶癥雖泛濫,但觀眾并不厭倦,這折射著時代的集體心理癥候。這種現象讓人聯想起榮格有關“集體無意識”的哲學和精神病理學分析,失憶癥是對自我空虛性的猜疑,是身份認同危機的征兆。在以自戀為社會心理特征的后現代時代,人們對于自我認同有著難以擺脫的深重焦慮。
失憶癥是出于心理方面的障礙,心理學認為這類疾病本質上都是“自我”出現了不正常導致的,即后天的心理類疾病都是關于“自我”之病,和原生家庭的童年時代緊密相關。影視文化熱衷以屬于“自我”之病的失憶癥的主題敘事無疑是內投于“自我”的關注和疑問。這并非與社會環境脫離,“在它最無意討論社會時,正是它最多地說明社會的問題的時候”[4]。那么,這些只關注“自我”挫折、喪失和錯亂的現象,恰恰是時代癥結的突出表現。我們時代的自戀人格核心——“自我”本質的虛幻性就是癥結所在。
拉康的鏡像學說,從精神分析的基礎論證了“自我”的妄想狂結構。自戀的妄想結構包含了個人、他人和欲望對象,而個人的內在沖突就是主體與“自我”的沖突,自戀認同把主體構造成與“自我”爭奪的對手。與鏡像認同之前的嬰兒處于無法分清自身和外圍世界的狀態中,正是鏡像讓嬰兒主體確立“自我”的同時,還發現自身和外界存在著差異,因此,主體才需要借助“自我”的統一感來抹去差異。鏡像的虛幻性和根本上是作為他人存在的特點決定了基于鏡像的“自我”本質是虛幻性和他人性。這意味著鏡像階段不僅建立了統一性的“自我”,更體現了“自我”從開始就存在著向他人的異化、分裂性,與此同時還建立了“自我”與外界的關系,這個關系建在虛幻的統一鏡像之上,因此也是虛幻的。從此,虛幻性、破碎性、異化性作為永恒的威協存在于“自我”的統一性之下。
“自我”的統一性和虛幻性構成了一種基礎權力關系,在這個關系之上,“自我”成為各種元素發生矛盾、爭奪、對抗、平衡、波動進而產生現實影響的場所。主體是天然破碎、殘缺的,它必須以完整的“自我”為衣裝才能現身,主體既需要“自我”的統一給予完整感,但由于“自我”的他人性、剝奪性,作為本質是破碎之物、是永遠不能得到滿足的欲望的主體又在進行著永恒的對抗。在這里,“主體”這一概念與許多學者說的人的非理性一面和真實的發自內心的需求、本能感受接近。如某學者說:“批判理論家認識到,在20世紀被管理的噩夢中社會總體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真正的主體性和自由的力量已分崩離析……一切合理的要求只能以緘默的否定形式出現,理論是向誠實的人們敞開著的實踐的唯一形式。”
主體對“自我”的抵抗正是通過“自我”行動的失誤和口誤、緘默脫落、否認拒絕、遺忘和錯覺、停頓和遲疑、敘述的失實處、規則應用的不一致、遲到和故意的缺席、指責和批評、恐懼和憤怒、偏好的幻想和夢幻中不可思議之事流露出來。主體與“自我”既被自戀認同牢固地強行粘合在一起,又因為不一致、虛幻而互相背離。因此,想象的“自我”與處在想象界之外并被“自我”所異化的主體之間的存在著永恒的沖突。
二、 失憶:對“自我”機制的猜疑
失憶癥是人們對“自我”存在著難以擺脫的焦慮體現。如果說耽溺于回憶是因為對過去的迷戀,那么多到泛濫的失憶癥主題敘事意味著我們對那個認同的“自我”有了懷疑和不信任感,但又無從分別哪些是“自我”,哪些是主體自身,從而渴望在徹底喪失“自我”的場景中獲得認同自由;也是對社會文化給定的環環相扣變化而來的邏輯因果的缺乏信心,所以渴望徹底切斷和歷史的聯系,在這一點上,是自戀主義者缺少延續的時間感的典型表現,“當前的時尚是為眼前而活——活著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后代”[5]。失憶癥是對“自我”虛幻性的猜疑,更是對“自我”依賴性的體現。下文將以敘事程式分析展開對失憶癥隱喻對“自我”機制進行剖析。總體來看,失憶癥在大眾文化的具體敘事情節中表現為兩種功能:在懸疑作品中是推進尋找“自我”的動力來源;在言情作品中是考驗愛情的試金石。下面就兩種功能分別進行敘事程式歸納。
(一)尋找“自我”的敘事程式
以21個影視劇①中的失憶癥主題敘事情節作為歸納程式的樣本:
1.丹克因車禍而嚴重失憶,找回記憶卻發現一切都不是原來所想。
2.簡則因車禍而失憶癥慢慢痊愈,發現原來的自己只是個犧牲品。
3.約翰找到記憶才知道一切記憶都是外星人胡亂拼湊的,自己追尋的都是徒勞。
4.杰克恢復記憶后發現自己被利用。
5.下山豹在力圖找回自己失去的記憶時,發現真實的自己遠不是記憶中那樣。
6.阿琳的失憶被冒充丈夫的人利用,卻難以說清是失憶是有心還是無意。
7.阿萊追尋記憶和殺害妻子的兇手時發現,記憶全不可靠,兇手可能是自己。
8.大衛最后明白失憶癥是自己委托夢境公司刪除自己的記憶所致,找到記憶的時候,大衛決定不再繼續夢境,寧可自殺得到真實。
9.貝蒂開始時幫助失憶并被人追殺的麗塔尋找記憶,這其實只是兇手戴娜的夢境,戴娜在夢中化為貝蒂,麗塔就是她殺死的同性戀人米娜,戴娜夢醒的時候自殺。
10.彼得因失憶被當成魯克,當他作為魯克生活幸福的時候,失憶痊愈,回到彼
得的身份,卻令所有人受傷害。
11.失憶的間諜伯恩找回身份時發現自己做過許多不道德的事情。
12.詹寧找到記憶的時候也發現自己是個為錢不顧一切的貪欲者。
13.失憶的查沃總認為有人要殺他,找到的記憶告訴他,他是個殺害孩子的兇手。
14.記憶錯亂的馬克最終發現自己過去一直被腦中的芯片控制。
15.失憶的伊萬恢復全部記憶時明白自己是個根本不該出生的人而自殺。
16.患有失憶癥的志遠找到記憶后發現自己曾葬送好友的生命。
17.阿倫負責剪接人死后的記憶,他發現自己曾害死過朋友,女兒被人侵犯過,
最大驚恐是自己也被植入記憶芯片。
18.男人發現自己在地獄般的地方醒來并失憶,幻覺消失后明白自己殺妻后自殺。
19.失憶的富明一直覺得自己害死好友,恢復后明白好友背叛過自己,并被自己另外的背叛者所殺。
20.五個陌生人在陌生地醒來并都已失去記憶,恢復記憶后他們明白自己是綁匪和人質,綁匪中的臥底警察發現自己因和人質之妻子通奸而想借機害死人質。
21.失憶的高靜恢復記憶后明白自己誤殺了男友。
O代表失憶后的失憶者,A代表無辜受迫害的失憶者,B代表有過錯的不道德的失憶者。21個敘事中,第6個的結構沒有推進,主人公沒有進行尋找;第19個的結構是O → 追尋B → A,剩余19個的結構都是O → 追尋A → B。那么,O → 追尋A → B是尋找“自我”的典型敘事程式。
失憶后的當事人處于空無狀態,沒有記憶、身份、只有生物學意義上的一具肉體,漸漸地從自己殘存的夢境碎片、別人的評價和遺留的一些物品構建出一個想象中的自我即理想自我A,在不斷求證A對A的追溯認同中,真相顯露,發現真實自我B與理想自我A是完全相反的。在親身感受鏡像自我和真實自我的分裂時,主人公往往因為身份認同危機跌入黑暗深淵。
(二)作為愛情試金石的敘事程式
以24個①影視劇的失憶癥言情敘事情節為歸納程式的樣本:
1.其芳失憶前已婚,失憶后與他人相愛,恢復記憶后發現還是最愛丈夫。
2.高潔失憶前愛張大勇,失憶后沒遇到其他人,恢復記憶后更加愛他。
3.田寧失憶前愛自力,失憶后愛志強,恢復后選擇志強。
4.可云因被男友拋棄失憶,失憶中還在愛男友,恢復記憶后不再愛了。
5.俊相失憶前愛柔真,失憶后愛上別人,恢復后選擇柔真。
6.有女友的道明寺失憶后愛上別人,恢復記憶后還是愛女友。
7.阿旺失憶前有未婚妻,失憶后娶別人,恢復后誰也沒有選。
8.月娥失憶后不再愛丈夫季常,恢復記憶后選擇丈夫。
9.有妻子的葛朗患有短期記憶癥,還是愛上伊蓮,靠筆記本保持記憶,在筆記本丟失后,葛朗忘記了一切,妻子愛上別人,依蓮選擇了葛朗。
10.阿當失憶前深愛女友,失憶后一次次忘掉她,但最終還是愛上女友。
11.張三豐失憶前與小蓮相愛,失憶后愛上別人,恢復記憶后說只愛小蓮一個人。
12.程顥失憶前與雪結婚,失憶后愛上冰,恢復記憶后回到雪身邊。
13.露西失憶前愛上男友亨利,失憶后亨利靠每天錄像維持著愛情。
14.博史與女友遭遇車禍而失憶,后來解剖死去女友的尸體時恢復對女友的記憶。
15.克萊和約爾因吵架都選擇清除記憶,失憶后的他們還是重新相遇相愛。
16.秀真失憶后忘了男友,男友費盡心機安排重遇,秀真恢復了記憶認出男友。
17.雅行得了阿茲海默癥,最終記憶完全消失,妻子選擇一直陪在他身邊
18.李逍遙失憶前已婚,失憶后愛上月如,恢復記憶后還沒選擇月如就死了。
19.均昊失憶前有女友,失憶后愛上天渝,恢復記憶后忘記天渝選擇女友,但最終對天渝的記憶恢復,而選擇天渝。
20.俊浩慢慢失憶,忘記愛了十年的女友,忘記后又重新愛上。
21.吉書失憶后努力尋找失憶前的愛人,最終發現就是陪自己尋找的女孩永荷。
22.柳月失憶后愛上別人,數十年后又愛上失憶前的戀人自勝。
23.昭順失憶前有老婆心蘭,失憶后愛上別人,恢復后選擇心蘭。
24.結婚50年的菲娜得了失憶癥,一個月內忘記丈夫并愛上了別人。
用I代表失憶前的失憶者,O代表失憶之中的失憶者,O→H代表在失憶時間段失憶者O慢慢具備新“自我”意識而成為H,A代表I的所愛,B代表H所愛,IH代表恢復記憶同時又保留新“自我”的失憶者。總結24個敘事中,第4個被男友拋棄而失憶I-A,失憶中愛著I+A,失憶后不再愛男友I-A。第7個失憶前愛妻子I+A=IA,失憶后娶別人B(O→H)+B=HB,恢復后誰也沒有選IH。第9個失憶前愛上依蓮I+A=IA,失憶中完全停滯O,失憶后依蓮選擇失憶者I+A=IA。第24個失憶前有丈夫I+A=IA,失憶后愛上別人(O→H)+B=HB,沒有恢復。剩下20個全部是失憶前I+A=IA,失憶中(O→H)+B=HB,恢復失憶后(IH-H)+A=IA。
失憶前、中、后依次為I+A=IA,(O→H)+B=HB,(IH-H)+A=IA。這是失憶癥的典型言情敘事程式。
失憶癥是自戀主義式愛情的試金石,失憶癥除了測試失憶者愛情的“忠貞”與否外,還可以探測失憶者是否存在自戀人格。言情劇中絕大多數失憶癥患者在恢復記憶后,在同時記得自己兩段戀愛生活的情況下,選擇失憶前愛的A。在這個結構中,記憶的回復使H被壓抑了,也就是失憶者向H方向發展的新的自我被壓抑了。在I變成O又發展成H的時候,原本的A,已經和I關系分離成為獨立的A。新的自我H選擇的是B,當原自我I回歸的時候為何會壓抑掉H而選A?這并非是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自戀主義者的自戀之愛的結構決定了這種行為。拉康認為,柏拉圖《會飲》對話中美少年阿爾基比亞德對蘇格拉底的愛就是一種自戀之愛。阿爾基比亞德認為蘇格拉底身上有一種無人擁有的珍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就像林神肚子內的Agalma神像。拉康認為Agalma代表就是不存在之物,是一種缺乏。對于蘇格拉底來說,它也是不存在的,而無法給出。阿爾基比亞德愛的是不存在之物,那么他愛上蘇格拉底就是把蘇格拉底當成一種不存在之物,阿爾基比亞德自戀認同蘇格拉底,也就是認同作為缺乏的Agalma,從而Agalma就取代了阿爾基比亞德,鑒于力比多的流動,Agalma就取代了阿爾基比亞德的自我,于是阿爾基比亞德就成了Agalma,也就是阿爾基比亞德愛上了自我。就像阿爾基比亞德對蘇格拉底的愛一樣,自戀主義者的愛本質是一種出于匱乏的欲望,被愛的人是填補欲望的對象,自戀之愛是以占有欲望對象從而滿足自己的匱乏為目的。這意味著自戀主義者把愛的對象視為自我匱乏的填補之物也就是自體的一部分來體驗、來愛的。原自我I回歸的時候,作為自我I一部分的A也必然一同回歸。A本身的意愿并未被I考慮,自戀主義者I認為A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是同體而不可分割的。自戀主義者是病態固著于自我I的,沒有自我就等于空無,因此對自我沒有抵抗力,也包括對作為自我一部分的A沒有抵抗力。恢復了記憶的自我I依賴于A的存在,沒有A,I就成了半路起家沒有歷史身份的H。
三、 失憶癥隱喻與“自我”機制
尋找“自我”敘事程式和愛情試金石敘事程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種隱喻都是關于“自我”機制的偽裝。正如德里達所說:“解構不是,也不應該僅僅是對話語、哲學陳述或概念以及語義學的分析;它必須向制度、向社會和政治的結構、向最頑固的傳統挑戰。”[6]“自我”機制作為現代人賴以生存的基石擁有最為狡猾的偽裝異化性、虛構性、分離性的手段。然而,“除了我們,誰會對‘我的客觀地位提出質疑呢?我們文化的歷史演化又趨向于將它與主體混同”[7]。要想把將“自我”與主體分開,首先要把“自我”所排斥、拒絕、矯飾的種種傾向重新縫合進來,把“自我”的暗面形狀暴露出來。
第一,尋找“自我”敘事程式中當事人南轅北轍的結局是對“自我”異化、虛構性質的巧妙矯飾。失憶者在鏡中照見的是想象鏡像A,認同的也是A,在對A完善認同的追尋過程反而帶來完全不同的“自我”B。事實上,B與A是同一的,A存在著的異化和虛構部分就是B。但是,敘事程式中把異化的“自我”部分分離出去命名為完全與A無關系的B,這是一種矯飾和偽裝。“自我”機制通過排除一切“不像自我”的部分,獲得一個完美自足的想像性存在。
第二,尋找“自我”后終獲死亡是“自我”機制對探尋“自我”這種恐懼行為的防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存在著想象鏡像A的鏡子之前的主體可能是B、可能是C,唯獨不是A,A對于鏡前主體來說是一個永恒的他人。以A為原型形成的“自我”的異化和虛構被“自我”想象的統一性所掩飾。作為B的人在鏡中照見完善的A,從此把完善的A當成自我,進行自戀式認同,盡管A與B實質上是始終分離的,但是在人眼中只看到A,B是被壓抑掉的,只是作為潛意識中對自我的抵抗存在。但是在失憶癥患者眼里,因為借助失憶而體會到A是不完整的,在追尋完善的過程中,B得以借A的不完整在場,令失憶者終于看到自身存在的B,從而體驗到自我進行認同的是虛幻之物,自戀的對象是絕對的空無。之所以說是空無而不是有罪錯的B讓主體崩潰、瘋狂,是因為即使是面容丑陋的骷髏在鏡中看見自己的臉不會恐懼,只有當骷髏在鏡中什么也看不見,才會恐慌于不在場的空無。絕對的空無意味著絕對主人,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中,絕對主人就是死亡。在《記憶碎片》這部美國電影中,主人公體會到了徹底的空無,不僅幻想的“自我”不可靠,記憶本身,追尋記憶本身也是不可靠的,主人公腳下沒有一絲真實,面對鏡子看到的是一片虛無,從而體會了被隨意拋擲的荒誕和瘋狂。敘事程式中,許多失憶者在尋獲B后主體自殺的結局是“自我”機制為主體設置的禁忌,對“自我”的探尋和質疑意味著危險的死亡和恐懼,因而成為禁忌。這個禁忌以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結局出現,迫使人們與“自我”保持安全舉例,奉“自我”為不可侵犯的神圣之物。
第三,愛情試金石敘事程式中對新生“自我”的否認是“自我”機制的專制剝奪。在這個敘事程式中,“自我”機制給自己加冕了忠貞美德的王冠,占據了更有優勢的地位。然而,失憶者在漫長的失憶時間和全新的社會環境中新生“自我”H本質來說和原初的“自我”是一樣的,沒有優劣、合法與否之分,但是“自我”與之俱來的剝奪性使兩個“自我”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在心理領域的“自我”范圍,拉康提出的象征界調停作用是難以發揮的。欲望完美統一的“自我”的專制對主體的占據不會留下“意識”到的任何一分空隙。“意識”是專制“自我”的最大幫兇,無意識為“自我”提供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拉康對“自我”專制性背后的能量之大有著深刻論述:“就像超我的無度壓抑是道德意識的有目的指令的根源一樣,人類特有的那種要在現實中打上自己形象的印記的狂熱是意志的理性干預的隱秘基礎。”[8]
第四,愛情試金石敘事程式中對 H狀態的畏懼是主體對“自我”的依賴性的結果,也是“自我”機制作為主人的強大力量體現。失憶者甫一失憶,仿佛成人的肉體中居住著一個剛誕生嬰兒的靈魂,這個時候“自我”不存在,但是“自我”所使用的各種工具手段都在。H狀態就是失憶者的新生“自我”,這個“自我”沒有歷史,背景是一片空白。空白不是可以建構理想“自我”嗎?為什么失憶者在恢復記憶的時候,盡管并沒有忘記這個新生“自我”,卻迅速撲入原初“自我”的懷抱呢?往往那個“自我”還帶著巨大的心理創傷和罪責。這一點很難批判說是“自我”強權,而是主體的先天破碎和不足導致,不和諧是先于和諧的,因此“自我形成的原型(Urbid)雖然是以其外在的功能而使人異化的,與它相應的是一種因安定了原始肌體混亂而來的滿足”[9]。主體對滿足感的渴求使主體處于“自我”主人屬下的奴隸位。但是,拉康又聲稱“自我”是自以為是主人的奴隸除了意味著“自我”以虛構鏡像為基礎的原因外,還意味著“自我”作為機制必須要通過主體才能發揮作用,這也為主體的反抗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2][3]劉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初版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64,165,198.
[4][5](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戀主義文化[M].陳紅雯,呂明,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39,4.
[6](法)德里達.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M].何佩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
[7][8][9](法)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115,11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