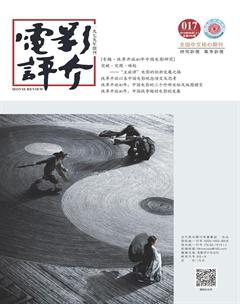流動的空間
張良
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 ethakul,下稱“阿彼察邦”)是泰國著名導演,1970年出生于泰國曼谷,并于2010年憑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電影自誕生伊始,就與各種交通工具有著“不解之緣”,電影史上最早的幾部電影中就出現了火車,比如盧米埃爾兄弟拍攝的著名的《火車進站》(1895)和喬治·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1902)。而之后電影史上許多著名影片也都出現了交通工具,比如埃德溫·S·鮑特的《火車大劫案》(1903),謝爾蓋·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1925)等。在現代電影中,火車、汽車、飛機、輪船等各種交通工具更是大量出現,飛車追逐的驚險場面在商業電影中也屢見不鮮,可以說,電影從發明之日到現在,一直是與各種交通工具聯系在一起的。
在阿彼察邦電影中也有很多關于交通工具的鏡頭,無論是拍攝運動中的交通工具,還是在運動中的交通工具上拍攝,它們都具有自己的視聽特點。本文將研究阿彼察邦電影中幾個含有交通工具的重點段落,并對這些段落中交通工具的選擇和表現方式做深入的美學分析。
一、“雙景框”的美學分析
在阿彼查邦電影中表現交通工具中的人物時,多次采用從交通工具外部拍攝的方法。我們下面將以《祝福》中的一段為例來做詳細分析:在影片上半部分的末尾,Roong和Min開車去森林,鏡頭從汽車正面拍攝了兩人在車內的情景。
從正面向封閉的、正在運動的車內拍攝,會產生一種“雙景框”的效果。一個是所有電影都存在的、電影畫面本身相對于銀幕之外的世界的景框;另一個是存在于電影影像中的“第二個景框”:觀眾視點在攝像機的位置,而攝影機跟隨車以同樣的速度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車相對于觀眾就是靜止的,而車外的景物看起來似乎是在向后方運動,這就形成大量從畫面中心到邊緣的放射線,使得整個畫面的構圖焦點聚焦在車的擋風玻璃上,擋風玻璃的輪廓也就形成了“第二個景框”。這種“雙景框”的美學效果,我認為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給人物關系或者情節加上了一層環境氛圍
在“雙景框”的影像中,外部環境是快速運動的,快速運動造成的影像模糊加上不處于構圖中心使得外部環境不能成為吸引目光的焦點,所以起到的往往是間接的、烘托氛圍的作用。比如上述《祝福》中的這個例子,車外“流動”的樹木和光影在情節之外給這一段疊加了一層輕松愉快的環境氛圍,配合了兩人離開城市去叢林郊游的心情。
這種由外向內拍攝運動中的交通工具的“雙景框”鏡頭,與從交通工具內部向外拍攝的“雙景框”鏡頭也有所不同。在后者中車窗外的景物是構圖中心,影像的重點就是景色和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窗外的風景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第二部電影”,所以環境起到的不僅是烘托氛圍的作用,更是觀眾的視覺中心,是被觀察、被期待和被實在觀看的對象。
(二)運動與靜止的碰撞
運動與靜止是一對矛盾,在這個鏡頭中,外部空間是運動的,內部空間是靜止的,這樣兩個空間同處于一個鏡頭之中,是交通工具為電影帶來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具有一種奇妙的、特別的效果,比只有一種狀態的空間更具有審美的復雜度和豐富度。
另外,在這種“雙景框”鏡頭中,交通工具本身是在運動的,但在影像中卻是相對靜止的,而外部景物實際上是靜止的,但在影像中卻看起來像是在運動的,可以說這種“雙景框”下的交通工具和景物的實際情況與它們被表現出來的影像在運動狀態上是相反的,影像使得人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發生了某種“偏移”,這同樣帶給觀眾一種奇妙的、神秘的電影感。
(三)客觀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碰撞
在現代電影中,交通工具的作用不再是運輸載體這么簡單,而是因為其獨特的空間性,成為了一種符號化的空間。交通工具隔開了兩個空間,一個是外部空間,一般可以表示客觀世界,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沒有情感因素;另一個是內部空間,往往可以表示內心世界,它是感性的、自我的、情感豐富的。交通工具可以表示隔閡,也就是表示人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之間存在的分裂。同時,交通工具還可以隔開外部的干擾,在它的里面,人可以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甚至可以理解為從“自我”回歸“本我”[1]。
在上述《祝福》的這個例子中,車把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隔開了,在車內是Min和Roong的二人世界,他們在車內是愉快的、充滿戀人間的幸福感的。而在車外,則是Min和Roong所不得不面對的、壓抑他們的、他們無法掌控的世界。在上車之前,Min幾乎一句話都沒說過,而Roong也被各種事情所困擾,表現得很煩躁,而到了這個段落,他們之前被壓抑的樂觀天性終于顯露出來了,Min高興地與Roong說話,并且用手指著給她介紹窗外的景象,還給負責開車的她喂食物,兩個人顯得都很開心。
(四)“縫合”[2]
“縫合”是拉康提出的一個概念,后來讓·皮埃爾·歐達爾把它運用在電影分析中,認為“縫合”功能使得觀眾不再懷疑電影的真實性,從而使“敘事的安全”得以保證。
“雙景框”的狀態下,觀眾可以看到外部景物的運動,這種運動是符合觀眾的日常認知的,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縫合”的作用。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上述《祝福》的例子在構圖中沒有外部景物,而是用擋風玻璃占據整個景框,這種情況下觀眾雖然知道劇中人物在運動中的車上,但是影像中卻完全看不到任何運動的跡象,這就偏離了日常生活的經驗,那么就容易使觀眾從劇情中“跳出”。有不少老電影在拍攝類似場景時,可能因為受限于當時的拍攝技術,很多都是采用讓擋風玻璃占據整個景框的構圖方法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模擬車的行駛效果,它們往往還會加入一些顛簸晃動、雨刷的來回擺動、以及在前擋風玻璃和后車窗上加以模糊的倒影和光線的變化等等。但盡管如此,在今天的觀眾看來,這些老電影的這類場景還是顯得比較“假”,原因就在于沒有背景運動的情況下,這種鏡頭會給觀眾帶來的“不合理”的直觀感受。
二、 開放空間的交通工具
與封閉空間的交通工具不同,電影中開放空間的交通工具(比如摩托車、卡車后部、敞篷車等)的影像又有其獨特的美學效果。因為開放空間的交通工具與外界的連通性,使得外部大環境可以對交通工具上的小環境起到很大的影響,風雨塵土可以發揮影響,日光暴曬、光影也可以發揮影響,甚至氣味以及外部人的觀察、侵犯等都可以發揮影響。而反過來,車上人物的情緒也可以影響到車的行駛節奏,從而使整個影像的氣氛為之一變……
阿彼察邦電影中也有一些表現開放空間交通工具的段落,其中最典型的是《熱帶疾病》上半部分的結尾,這一段之中既有摩托車的鏡頭,也有皮卡車后部的鏡頭,還有軍用卡車后部的鏡頭,匯集三種開放空間的交通工具于一段,值得我們加以詳細研究:
(一)摩托車
摩托車在電影中是具有符號化意義的,它具有機械性的、鋼鐵的外殼,馬力強大,而且不同于汽車的安全和舒適,摩托車帶有一種原始的、野性的、勇敢的符號。一提到摩托車,我們就會想到排氣管發出的巨大轟鳴聲,風馳電掣的飆車族等等,使得騎摩托車常常被用來代表“男人氣概”,以及用來表現愛情、勇氣、青春、荷爾蒙、野性等主題。
在《熱帶疾病》上半部分結尾,前六個鏡頭都是表現Keng騎摩托車的情景。因為這六個鏡頭中除了Keng、公路、路燈之外幾乎沒有別的景物,視覺元素很純凈,所以給人一種自由自在、天地間馳騁翱翔的感覺,這種視聽設計匹配了Keng當時喜悅的心情。具體來說這六個鏡頭還有如下兩個特點:
1. 鏡頭設計富于變化
這六個鏡頭的景別、角度、視角、運動方向各有不同:第一個鏡頭是俯拍的、表現Keng的主觀視角的鏡頭;第二和第三個鏡頭分別是Keng騎摩托車橫向和縱向運動的客觀視角鏡頭;第四和第五個鏡頭都是仰拍的、主觀視角的鏡頭,而且這兩個鏡頭之間還保留了景別上的變化,第四個鏡頭相當于中景,而第五個鏡頭相當于全景;第六個鏡頭也同樣是主觀鏡頭,但在鏡頭角度上又做了改變,變成了正常的平視角度。由此可見,導演對這六個鏡頭是精心設計的,使得這六個鏡頭之間既有一定規律、又不重復枯燥。
2. 節奏感
首先是視覺節奏。Keng騎著摩托車,路燈的光灑在公路上,也灑在他身上,呈現出一種明暗相間的、由光影構成的節奏。第一個鏡頭中,路燈的光照在公路上形成“光圈”,而這些“光圈”一個接著一個連起來就形成了節奏;第二和第三個鏡頭中,路燈的光照在騎摩托車的Keng身上,忽明忽暗連起來形成了節奏;而第四和第五個鏡頭,仰拍路燈在空中一個個劃過,也形成了節奏。
其次是聽覺節奏。在這六個鏡頭中沒有對話和聲音,從第一個鏡頭開始,就配以很有節奏感的流行歌曲,由光影形成的視覺節奏與流行音樂的節奏匹配起來,非常和諧。
最后是心理節奏。這一段表現的是Keng對Tong的愛情終于得到了積極的回應之后,他獨自一人騎著摩托車、心情無比喜悅的狀態。我們在文學作品中經常見到把幸福的心情形容為“一陣”“一股”“暖流”等等,而積極心理學也把內心的幸福感覺稱為“福流(Flow)”[3],實際上,它們都描述了處于幸福狀態的人感受到的那種綿延不斷的、流暢的心理感覺。這種一陣陣的幸福感與摩托車行駛的流動感配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種節奏。
總之,“福流”式的心理節奏、移動鏡頭的流動感、純凈感,以及視覺上的光影節奏和聽覺節奏,還有鏡頭角度和運動方向、景別的有規律地變化,以上幾方面共同作用,既帶來了視聽上的豐富性,也帶來了節奏上的秩序性,這就是這一段落讓觀眾覺得舒服、覺得美的原因。
沒有對話,也沒有戲劇化的動作,只用了一個場景——公路,只用了一個道具——摩托車,導演就把Keng內心的喜悅之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而且,用騎摩托車這個動作來表現無法言表的愉悅狀態,這個設計可以說是非常敏銳和準確的。
(二)皮卡車
在上述六個鏡頭之后,緊接著的三個鏡頭,在場景上首先就與前面有比較強的對比:前六個鏡頭都是在空曠的公路上拍攝的,路邊沒有人,路上也很少甚至沒有其他車輛,而緊接著的三個鏡頭的場景就顯得熱鬧多了,表現了皮卡車穿行在夜晚城市之中的情景。
第一個鏡頭是路邊很燈火通明的夜市全景,第二個鏡頭中是一輛行駛的皮卡車后面默默坐著的一群人,第三個鏡頭中路邊有人打架,而且這些人看到皮卡車經過,追上來向它扔酒瓶子。
我認為,前六個鏡頭與這三個鏡頭不僅僅是清凈與熱鬧的對比,而是夢幻與現實的對比,個人狀態與群體狀態的對比,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對比,單純、愉悅、美好與復雜、沮喪、不友好的對比……另外,在視聽語言上,導演也將這三個鏡頭與前六個鏡頭做了區別:首先是色調方面不同,前六個鏡頭是暖色調的,路燈的光線是黃色的,在路燈照耀下的街道和人物都顯得溫暖、親切,而這三個鏡頭是冷色調的,道路兩邊雖然很熱鬧,但到處都是日光燈管發出的白光,讓人感覺這是一個冷漠的、無法親近的世界;其次是鏡頭的視角不同,前六個鏡頭中有幾個表現Keng騎摩托車的客觀鏡頭,在客觀視角下,Keng像一個沐浴在幸福中的精靈,而這三個鏡頭全部是主觀鏡頭,攝像機像一個潛行在危險環境中的幽靈,它看到的都是冷漠和暴力……
導演之所以做這些區分和對比,我理解是想表達他對Keng和Tong的同性戀情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下的悲觀。雖然他們相愛,也有很美好的時光,但導演并不想給大家一個錯覺,似乎同性戀情在當今泰國社會中的處境都是美好的。他們終究不能永遠活在兩個人的世界里,當他們出來面對這個真實的世界時,就會發現這個世界雖然很精彩、熱鬧,但卻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人們很冷漠,他們只能在社會邊緣走動,而即便這樣,對他們的攻擊也會隨時突然出現,毫無征兆。
(三)軍用卡車
在上述三個鏡頭之后,接下來是一組表現一隊士兵(其中包括Keng)坐在軍用卡車后部前往叢林的鏡頭。這組鏡頭一共六個:前兩個鏡頭是移動鏡頭,拍攝卡車上的人物特寫;第三、第四和第五個鏡頭是固定鏡頭,拍攝卡車上的人物近景;第六個鏡頭是固定鏡頭,拍攝卡車后面的公路全景。
這六個鏡頭與之前的鏡頭的有三點不同:
首先時間是白天,這與之前九個鏡頭都是夜晚不同。夜晚是業余時間,白天是工作時間;夜晚是個人情感時間,白天是社會角色時間。所以導演用夜晚來表現Keng得到愛情的喜悅,而用白天來表現他回歸“森林小隊”跟大家一起去巡邏的情景。
其次是場景不同。這六個鏡頭的場景是在叢林公路上而不是在城市里,表示Keng最終還是決定回到叢林去。另外也從側面暗示了叢林是一個自由、包容之地,Keng和Tong在城市里不被接納的愛情關系卻可以在叢林中得到安放。
第三,這一組鏡頭的卡車與前六個鏡頭的摩托車,它們的美學效果截然不同:
1.乘坐者與控制者。摩托車上的人既是乘坐者也是控制者,人是主動的,人的情緒可以帶動摩托車的行駛節奏,可以產生情感上的共振,有一種所謂“人車合一”的感覺。另外因為摩托車具有空間開放性,人、車和環境是處于同一個空間的,人的情緒和感覺可以“發散”到空氣中去,使整個影像的氣氛都被帶動起來。
而坐在卡車后部的人只能是乘坐者而不是控制者,雖然人與環境也是處在一個一體的開放空間中,但人的情緒和車的運動并不能形成節奏上的匹配。人是被動的,人的情緒是被車的行駛狀態和周圍環境所影響的,而不是影響環境的。
2.個人化與社會化。雖然都是開放空間,但摩托車是個人化的交通工具,阿彼察邦鏡頭下的騎摩托車的Keng是充滿感情的,輕松、愜意、舒暢的。而卡車是社會化的交通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卡車上人的表現大多是生硬、呆滯、昏昏欲睡的,沒有個人情感的注入。
3.符號。如上文提到的,摩托車還有很多符號化的含義,比如代表青春、愛情、勇氣、野性、荷爾蒙、男人氣概等等,但卡車一般不具備這些符號化的意義,只是交通工具而已。
最后,這一組的第六個鏡頭是一個近半分鐘的長鏡頭,是在行駛的卡車上拍攝車后面的景象,在視聽語言上可以解釋為離開。從簡單的劇情角度理解,當然是表示Keng重新加入“森林小隊”離開城市回到叢林,而更深層次可以理解為Keng逃離城市所帶來的煩惱。而車后面被帶起來的塵土飛揚的景象,給人一種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感覺,其深層含義可以解釋為對城市的、世俗規則的破壞,在叢林里人們終于可以放飛自我、不受任何約束,這也是本片的主題之一。
結語
對于在自己電影中表現出的對交通工具的偏愛,阿彼察邦是這樣解釋的:“我喜歡夢幻的、流動的,不局限的形式。這樣的畫面有一種重量,而不是遵循于敘事的限制。電影院對于我來說就像汽車,把觀眾運送到未知的地方。所以有時候重要的不是想而是看,就像欣賞異國情調一樣,你可以讓理智模糊起來,這樣就有雙重的敘事了:風景的和故事的,這非常吸引我。”[4]
電影是運動的影像,而交通工具也天然具有運動的本性,在這一點上,交通工具與電影是非常匹配的。在交通工具的運用上,阿彼察邦電影中的汽車、摩托車等并不是僅僅作為道具為劇情服務,而是超越了簡單的敘事功能,引導我們進入了一個感性的世界。這體現了阿彼察邦的電影美學思維,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阿彼查邦的電影中,交通工具回歸了它的本性,電影也回歸了它的本性。
參考文獻:
[1](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122-128.
[2](英)蘇珊·海沃德.電影研究關鍵詞[M].鄒贊,孫柏,李玥陽,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479.
[3]Mihaly Csikszentmihaly.Finding Flow:The Psychology of Engagement with Everyday Life[M].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122-126.
[4]Holger Romers.Creating His Own Cinematic Language:An Interview with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M].? CINEASTE,2005,F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