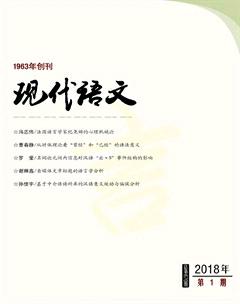略論楊倞《荀子注》的詞匯研究價值
霍生玉
摘 要:唐代楊倞《荀子注》是迄今可見《荀子》最早注本, 楊注對荀學研究的重要地位無可取代。楊注價值遠不止在整理《荀子》這一方面,還體現在訓詁學、詞匯學及校勘學等多個領域。本文僅就其在詞匯研究方面的價值擷取若干語詞加以論述,以引起學界對楊注研究的更多關注和重視。
關鍵詞:《荀子》 楊倞 注釋語料
唐代楊倞《荀子注》(以下簡稱“楊注”)是迄今可見《荀子》最早注本,楊注對荀學研究的重要地位無可取代。然而,如果我們將對楊注的研究僅僅放在其校注《荀子》方面,是遠遠不夠的。其實,作為中古一種重要的注釋語料,楊注的價值遠不止在整理《荀子》,還體現在訓詁學、詞匯學及校勘學等多個領域。近年來,關于中古注釋語料在漢語詞匯研究方面的價值已逐漸為學人所認識。董志翹(2005)、徐望駕(2015)、張能甫(2000)等都有論述,如徐望駕說:“中古注釋語料在漢語詞匯研究方面具有獨特的文體價值,只要推陳出新,完全有可能成為今后詞匯研究中可資利用的熱點語料。”然而,綜觀現有關于中古注釋語料的研究成果,楊注卻是被相對忽視的一種。本文就其在詞匯研究方面的價值擷取若干語詞加以論述,以引起學人對楊注研究的更多關注和重視。
一、楊倞《荀子注》重視引時人流行語詞作注,所引語詞多始見于楊注
張能甫說,“漢語史上所謂的史料價值,主要指語料接近當時實際用語的狀況如何。就這一意義上說,價值最高的是佛典,其次是注釋語言。”楊倞為幫助時人讀懂先秦時期的《荀子》,其注語表現出了對唐代新興口語詞的高度重視。比如,楊倞有時會特意引用一些當時的流行語詞來作注,其中有的語詞乃始見于楊注,這些新興的口語詞,正是因楊注的闡發,才得以傳于后世。楊注為后世提供了珍貴的唐代口語詞研究材料。例如:
不到①——
《性惡》: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
楊注: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于知,猶言不到也。
按:楊注中“猶言”,是用時人流行語詞來對《荀子》中語詞進一步解釋的一個訓詁術語。吳金華(1995:71)指出:“一些洋溢著時代氣息的俗語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這里的“不到”,即為唐代新興俗語詞,它是指“對某事的認知、體會尚不夠”,相當于“不懂”的意思,與今日習用的“不到”詞義不同。今日習用的“不到”,是指“沒有到達;不至”,這個用法在上古漢語里就很常見了,其后一般接處所名詞,或后面隱含有處所名詞。例如:
《詩·大雅·韓奕》:“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漢·毛亨《毛詩》,8-18/21a②)
《史記·晉世家》:“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史記》,卷39/1656)
《史記·李將軍列傳》:“且引且戰,連斗八日,還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史記》,卷190/2877)
然而,楊注中的“不到”,其后并不接處所名詞,也未隱含有處所名詞,它并非“不到達,不至”的意思,而是指向對某事的認知、體會,猶言“不懂”。此義項暫不見于楊注之前文獻,在楊注以后五代至宋的一些口語色彩很強的作品中才多見起來。例如:
《祖堂集·歸宗和尚》:“既有辝親棄俗,被褐講經。經有明文,疏無不盡。自是智辯不到,謬判三身;體解不圓,濫轉八識。將智辯智,狂用功夫;將文執文,豈非大錯?”(《祖堂集》,卷15/687)
《玉海·辭學指南·誦書》:“朱文公曰:‘讀書須成誦方精熟。”附注曰:“熟讀《漢書》、韓柳文不到,不能作文章。歐公、東坡皆于經術本領上用功。”(宋·王應麟《玉海》,948-卷210/280)
《九家集注杜詩·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天路牽騏驥,云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郭注:“首篇止引劉孝標《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為補舊注之遺,此豈獨出于劉孝標邪?陸機‘鞠歌行云。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嘆。孰謂前人不相依傍歟?此亦注《文選》所不到矣。”(宋·郭知達集注《九家集注杜詩》,1068-卷18/329)
《補注杜詩·杜鵑》:“杜鵑暮春至哀,哀呌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黃希注:“趙曰:‘鮑昭《行路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用蓋出于此也。至若此篇,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君之意前人所不到。”(宋·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1069-卷11/211)
上述“不到”用例多出現在五代至宋的一些口語色彩很強的作品中,都是“不及知;不懂”的意思。可見,此“不到”經楊注闡發之后,后世文獻中才較多使用。楊倞為讓時人讀懂戰國時期的《荀子》,以“不到”解釋《荀子》中的“不及知”,體現了他對當時流行口語詞的格外重視。這里也順便提及,《漢語大詞典》【不到】詞條,僅列“不到達”“不料”“不至于;不見得”“不周到”4個義項,建議《大詞典》暫引楊倞注為始見例,增列“不了解;不懂”義項。
除對時人口語詞的重視外,楊注對方言詞也頗為措意。楊注除直引揚雄《方言》為證之外,還時常以自己熟悉的方言——“今秦俗方言”證之,因而其注也留存了一些鮮活的唐代方言材料。
衢——
《勸學》: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楊注:《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
王念孫案:《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岐旁。”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涂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讀書雜志·荀子》,632頁)endprint
按:“衢道”與“兩君”對舉,“衢”的古義是“四”還是“兩”?竊以為,楊倞或說可取。他首先引《荀子》下篇“楊朱哭衢涂”(楊注:“衢涂,歧路也。”)為內證;繼而,又以共時的方言材料( “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為外證,內證、外證共舉,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衢”可訓“兩”。楊倞乃虢州弘農人,秦方言是楊倞熟知的方言,也是他注《荀子》時的共時語料,楊倞引唐代秦方言為實證來訓釋疑難字詞,發前人所未發,堪稱精彩。尤為難得的是,先秦時“衢”有“兩”義,并不見于今本揚雄《方言》,楊注為后人研究古代方言提供了可貴材料。清人王念孫在楊注的基礎上,進一步用外證(《爾雅》《大戴禮記》等與《荀子》共時的語料)與內證(《勸學篇》《王霸篇》及《大略篇》等《荀子》自身的語料),對楊注進行了申述,把問題解決得更為透徹。
律——
《禮論》: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楊注:律,理發也。今秦俗猶以枇發為栗。
按:楊倞用唐代秦方言“以枇發為栗”證先秦《荀子》中“律”有梳理頭發義。“律”有梳發義,亦不見于今本揚雄《方言》,卻在楊注之后的文獻中屢見。例如:
《廣韻·質韻》:“搮,用手理物。”(《宋本廣韻》,450頁)
《正字通·彳部》中亦云:“律,理發曰律。”(明 張自烈撰《正字通》,1-423b)
王先謙《荀子集解》引郝懿行曰:“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蟣虱為類,言一類而盡除之也”。(王先謙《荀子集解》,367頁)
由此可知,梳理頭發,可說“栗”,也可說“律”、說“類”。栗、律、類同屬來母,上古“栗”屬質部,“律”“類”屬物部,三字音近。以手理物、梳理頭發稱“搮”,現代方言中仍存遺跡。《漢語方言大詞典》(卷5/6469)有錄:“搮,梳理;以手理物。①膠遼官話,山東牟平;②吳語,浙江蒼南金鄉。搮頭。//頭發搮搮好。浙江象山,1926《象山縣志》:搮,《廣韻》力質切,以手理物。”可以說,“律”有“理發”義,正是因了楊注的闡發,才得以傳于后世,楊注對古方言俗語詞的流傳和研究作出了貢獻。
二、楊倞《荀子注》在訓釋古疑難字詞方面多有創獲
楊倞對《荀子》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校釋,其注不僅很好地繼承了前人的訓詁成果,嫻熟地運用了前代訓詁方法,并且在前人基礎上還時有創獲。楊倞有些注釋,發前人所未發,頗給后人以啟迪;有些注釋,學人雖或多或少偶有批駁之言,但經仔細核定之后,卻終覺楊注可取,他人所論,倒未必切合荀書之旨。茲舉兩例予以說明:
后王——
《非相篇》:“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楊注:“后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圣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于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后可,斯惑也!
按:楊注是把“后王”解釋成“近世之王”的,其意乃與上古圣王相對而言。但楊倞之后的諸多《荀子》注家,如:物雙松、劉臺拱、汪中、王念孫等,卻都認為“后王”系指“文、武”而言。孰是孰非?
楊倞對“后王”有注凡五見,除《非相篇》外,其余四處亦列舉如下:
《不茍篇》: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楊注: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
《儒效篇》: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楊注:后王,后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于時,制度亂矣。
《王制篇》: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
楊注:法不貳后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
《成相篇》: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后王。
楊注:后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后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于古法。
在這四例中,楊倞也是將“后王”釋為近時、當今、當世或后世之王的。除此之外,其余在闡發《荀子》文意中,楊注也多次作出了類似的訓釋。例如:
《儒效篇》: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后王謂之不雅。
楊注: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也。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
《不茍篇》: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楊注:言君子審后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后世澆醨,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
這些注語雖表述不完全一致,但考其本義,所指均相同,皆指近時或當今之圣明君主。楊倞關于“后王”的解釋和其后清代的各《荀子》注家,如:物雙松、劉臺拱、汪中、王念孫等,都不同。竊以為,楊倞關于“后王”之注洽符荀意,倒是諸家之說缺乏實證,并不足以否定楊注。理由有二:
其一,諸家以“后王”為周文王、武王,與《荀子》本意不合。孟軻、子思言“法先王”,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荀卿則常言“法后王”“治當世”。“法后王”是荀子提出的重要觀點。“后王”,在《荀子》一書中凡九見:《非相篇》一見,《不茍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荀子在這些篇章中多處闡明了其“法后王”的思想,如《不茍篇》:“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句中“后王”與“今日”相對,顯然非指距荀子時代不下七百年的文、武,而是指近世之王。再如《非相》:“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句中“后王”猶如“己之君”,也可見荀子言“后王”之本意并非指上古之文、武,而是指近世之明君。并且,當時不獨荀子有此論,《呂氏春秋》亦有類似觀點,《呂氏春秋·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呂氏春秋》,422-卷15/20a;21b)《呂氏春秋》與《荀子》大約同時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因此,諸家以“后王”為“文、武”,實未得《荀子》本義。endprint
其二,楊倞注“后王”為“近世之王”,并非沒有根據,其注乃植根于西漢司馬遷說。《史記·六國年表》序云:“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唐代張守節《正義》:“后王,近代之王。法與己連接,世俗之變及相類也,故議卑淺而易識行耳。”(《史記》,卷15/686)在這里,司馬遷言“傳曰:‘法后王”,雖然他沒有直言《荀子》,但先秦文獻中,“法后王”之語僅見于《荀子》。竊以為,司馬遷距荀子所處時代不遠,他把《荀子》中的“法后王”解釋為“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顯然比一千多年以后清代學者們的一己臆測更為可信。
在此也順便提及,《漢語大詞典》“后王”詞目下立兩個義項:“①繼承前輩王位的君主;②泛指繼前朝而起的國家元首。”由上所述,我們建議《大詞典》增列義項“與上古圣王相對而言,指近時或當今之圣明君主”。
端拜——
《不茍》: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楊注: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后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后世澆醨,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
王念孫案:古無拜議之禮。且“端拜”二字,意義不相屬。“拜”當為“”。“”,今“拱”字也,形與“拜”相似,因訛為“拜”。“端拱而議”,即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為“”之訛耳。(《讀書雜志·荀子》:642頁)
按:楊注指出“端拜”猶言“端拱”,這給了千年之后的王念孫以啟迪。王念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端拜”和“端拱”實際上是同一個詞,只是由于字形的演變,才造成了傳寫的訛誤。王念孫之說無疑受到了楊注的啟發。可見,楊注在訓釋古代疑難字詞方面頗有創見,為后人提供了較高的研究平臺。
由此可見,學界對楊倞《荀子注》的研究不應該僅僅關注其在整理《荀子》之功這一個方面,還應該重視楊注在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價值,著力開掘其作為中古注釋文體的語料價值。然而,目前學界對楊注語言的重視程度顯然還很不夠。茲撰此文,希望我們的膚淺論述能喚起學人對楊注研究的關注,則愿足矣!
引用書目(依成書時代為序):
《毛詩》(四部初編本);《史記》(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祖堂集》(中華書局,2007);《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九家集注杜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注杜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正字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釋:
①此條系受先師吳金華先生2011年12月16日在復旦大學授課時的啟
發所得,特此注明,以表懷念!
②本文引用古文獻例句,標注頁碼的體例是:對分冊、分卷編排
者,冊次與卷次、頁碼之間用“-”連接,又卷次與頁碼之間以“/”相隔,頁碼后的字母a/b表示引文在上/右或下/左欄次。
參考文獻:
[1][宋]陳彭年等主編《宋本廣韻》[M].北京:中國書店,1982.
[2]董志翹.故訓資料的利用與古漢語詞匯研究[J].中國語文,2005,(5).
[3]盧文弨,謝墉校.《荀子》(第1冊第8頁)叢書集成初編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Z].北京:中華書局,1999.
[5]徐望駕.中古注釋語料詞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合肥學院學報,2015,(2).
[6]王念孫.《讀書雜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7]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8]吳金華.《古文獻研究叢稿》[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9]張能甫.鄭玄注釋語言詞匯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0.
Abstract:It is Yang Jiang who is the first to annotate Xunzi in Tang Dynasty and his annotation important role cannot be replaced in the study of Xunzi.However,the values of Yangs annotation not only lies in compilation of Xunzi,but also reflects in Exegetics,Lexicology or Textual Criticism and so on. In order to arouse the scholars attention,this article has selected some words in Yangs annotation to discuss their values in the lexicological study.
Key Words:Xunzi;Yang Liang;linguistic data of annota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