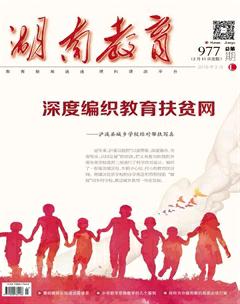小學數學思維教學的幾個案例(上)
數學思維教學的重要性現已獲得了小學數學教師的普遍認同,但就這方面的具體工作而言,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我們深入地進行研究。特別是,如何將數學思維與具體知識內容的教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學生不僅能夠很好地掌握相關的數學知識與技能,也能逐步學會數學地思維。筆者就近期接觸到的幾個課例對此做出具體分析,希望能夠引發廣大教師的思考,并能結合教學實踐積極地開展研究,從而將教學工作做得更好,切實促進自身的專業成長。
一、“年、月、日的認識”的教學
這是蘇教版數學教材三年級下冊的一項內容。常見的教法是:引導學生對某一年份的年歷做具體考察,從而發現大月、小月的區別,包括它們各有多少天,2月有什么特殊之處,全年共有多少天,以及平年和閏年的區分,等等。顯然,這樣的教學設計主要集中于知識的掌握。
上述的目標應該不難達到,但就我們的論題而言,筆者希望讀者能進一步思考:就這一內容的教學而言,我們如何很好地體現數學思維的教學這樣一個目標?當然,這也是這一教學活動的一個相關事實,即我們的教學如果完全局限于相關事實,就很難被看成一堂真正的數學課。因為,這些知識都只是生活知識,很難被看成與數學具有真正的聯系。
或許也就是基于后一種思考,有教師提出了這樣的教學方案,即由單獨考察某一年份的年歷轉而同時引入多個不同年份的年歷,希望學生通過對比,憑借自身的努力獲得相關的發現,甚至認為這也屬于“找規律”的活動。
相對于簡單的傳授而言,讓學生自己獲得相關的發現當然更加可取。但是,這樣的活動是否就因此具有了一定的數學味?筆者對此仍有一定的懷疑,包括這樣一個思考:所說的知識能否被看成真正的規律?因為,這正是人們關于日常認識與數學認識主要區別的一個共識:后者不應停留于事實的發現,還必須對此做出進一步的說明與理解,包括必要的證明。再者,在筆者看來,與其將大月有31天、小月有30天、一年有12個月等看成所謂的規律,還不如說它們都只是一些歷史事實,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進而,也正是從同一角度分析,筆者以為,與單純強調找規律相比,這可以被看成關于這一內容教學更恰當的一個定位,即我們應當由現成知識的簡單傳授或發現轉而更加重視其形成的過程———當然,后者主要是指歷史與文化的考察,而非純粹的理性分析。
但是,我們如何將這一內容的教學與數學思維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呢?或者說,使其具有較強的數學味呢?在筆者看來,這就直接涉及分析的視角:從數學教學的角度看,我們應當將年、月、日的認識放到度量,特別是時間的度量這一更大的范圍中去進行分析思考。
還應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數學的視角,不應被看成是與前面所提到的歷史與文化的考察直接相抵觸的。這就為我們更好地從事這一內容的教學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們如何將兩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具體地說,在此不妨首先將學生引入這樣一個情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概念與計時工具和方法,早期的人類與現代人相比,顯然更加容易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們不知不覺就老了!時間都去哪兒啦?
當然,這也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計時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當時并沒有合適的計時工具及概念系統,人們就必然會借助日常生活中所觀察到的一些自然現象,特別是天體的變化作為基本的計時工具。這直接導致了日、月、年的引入:它們分別與晝夜的輪替、月亮的圓缺變化,以及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環直接相對應。
再者,如果教學中我們能從社會文化,特別是聯系人們生活生產的需要去進行分析,顯然就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引入年、月、日這些計時單位的必要性。另外,與現實的需要相對照,以下的思考則可說表現出了較強的數學味:由于同時存在多個不同的計時單位,我們顯然也就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如1年究竟有多少天?1個月有多少天?1年又有多少個月?等等。這也就是指,后者事實上即可被看成一般性的度量問題在這方面的具體體現。
當然,上述各個問題的提出還可被看成很好地體現了精確定量這樣一個數學思想。然而,就這方面的各個具體結論而言,又應說是文化的因素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如,我們為什么會進行大月和小月的區分,為什么會對2月的天數做出特別的規定等。再則,以下的事實顯然可被看成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它們的文化性質,即歷史上存在多種不同的計時系統,如所謂的陽歷與陰歷等。當然,最終又是科學的進步為時間度量的統一提供了客觀標準。比如,我們應當如何決定一年的長度,又應如何依據相關的事實做出平年與閏年的區分,等等。
最后,筆者以為,借助以下事實我們或許可幫助學生初步地領會兩種文化的區別:如果說現行的計時系統主要體現了人文文化的影響,那么,這就是科學文化(數學文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成分)十分重要的一個特征,即更加注重結論的合理性。就我們當前的論題而言,這也就是指,我們應當如何安排年、月、日才最為合理。例如,以下就是一些科學家曾提出的一個建議:我們應當完全取消大月與小月的區分以及2月的特殊地位,而是統一規定“一年中12個月都是30天”,并將剩下的5天(或6天)放在一年開始之時作為公共假日。
由此可見,上述內容事實上也為我們在教學中很好地滲透數學文化提供了契機。
關于計時問題的另一實例可參見《24小時記時法的教學》([1]:第一章,[例14]),其中特別提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除了12小時記時法與24小時記時法的明顯區別以外,還涉及兩種不同的計時系統,即所謂的周期記時法,以及如同“2016年9月18日下午6時30分”這樣的精確記時。在此要強調的是:月份的引入事實上可被看成周期計時的又一實例,而這又正是采取周期記時法的一個主要優點:“數學使一切科學變得簡單。”(陳省身語)
二、“誰的面積大”的教學endprint
這是各類教學觀摩中經常可以看到的一項內容,任課教師普遍采取了聯系生活實際的引入方式,如,用28根1米長的木棍圍一塊長方形的菜地,如何圍面積最大?(這方面的一個課例可參見[1]:第一章,[例8])這里所說的引入方式當然有一定的優點,但筆者在此從另一角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如何才能使數學課上所提出的問題對學生而言是真正十分自然的?如果說所謂的問題引領和問題驅動可被看成數學教學既能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又能很好地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并能幫助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更一般地說,就是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特別是,能逐步學會更清晰、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地進行思考,并由理性思維逐步走向理性精神)的關鍵,那么,這就是這方面工作應當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即我們應當高度重視相關問題的自然性:“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教師必須讓學生感到問題的提出是自然的,而不是神秘的,是有跡可循的,而不是無章可依的。”(詳見[2])
當然,筆者在此所關注的,不只是所說的“圍地問題”對學生而言是否可以被看成十分自然的,而主要是這樣一個思考,即我們應當如何提出“誰的面積大”這樣一個問題,才能更加有利于學生思維的發展。這顯然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學生現實情況的深入分析。
具體地說,正如人們普遍了解的,這是學生在學習平面圖形的面積與周長時經常會出現的一個錯誤,即對面積與周長這兩個概念產生混淆。為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有不少教師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如我們可以利用直觀動作(即所謂的畫一畫與摸一摸等)幫助學生較好地把握周長與面積的區別(這方面的一些實例可參見[1]:第三章,[例19],第九章,[例17])。這些做法當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應強調的是,這又正是人們思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人們已建立的觀念,包括各種錯誤的認識,并不能通過簡單糾正就會立即得到改變,而往往會潛伏在主體頭腦的某個部位,并在某個時候不知不覺地表現出來。容易想到的是:這事實上也就是將周長與面積混淆的一個具體表現,即有不少學生會認為“如果兩個平面圖形的周長相等,它們的面積也一定相等”。特別是,如果兩者都屬于同一種圖形(如長方形)的話。
至此,相信讀者也就容易理解筆者關于如何引入“誰的面積大”的以下建議了,即不同于現實情境的設置,我們可讓學生自由地提出自己關于以下問題的猜想:“兩個長方形如果周長相等,它們的面積是否也一定相等?”應當強調的是,除了有益于更好地糾正學生對周長與面積這兩個概念理解上所存在的錯誤以外,后一做法還具有這樣一個優點,即能使學生們切實體驗什么是真實的數學研究活動。特別是,這往往包含這樣的過程:問題———猜想———檢驗———修正或改進———再檢驗———理解與說明(作為真正的數學研究活動,最終當然還應對所得出的結論做出嚴格證明)。這也就是指,我們在此同樣可以按照上述的路徑開展相關內容的教學。
在此還應清楚地指明這樣一點(這也是數學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所面臨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在此是指否定性結論的得出,即我們通過實例的計算———例如,假設長方形的兩條邊長分別是12與2,10與4———就可證明“周長相等時,長方形的面積也一定相等”這一猜想是錯的)并不意味著研究的結束,而是應當以此為基礎積極地開展新的研究,包括提出新的問題與猜想。(詳可見[1]:4.3節)
具體地說,在得出了“周長相等的長方形,面積未必相等”這樣一個結論以后,我們還應引導學生遵循以下思路積極地開展新的思考:盡管周長與面積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相等關系,恰恰相反,隨著圖形形狀(或者說邊長)的改變,面積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但是,對于所說的變化,我們是否可以找出某種確定的關系或規律?更一般地說,這也就是指,我們應努力尋找變化中的不變成分或因素。(這方面的另外一些實例可參見潘小明,“用核心問題引領探究學習,培育小學生的數學核心素養,《小學數學教師》,2016年增刊;鄭毓信,《小學數學概念與思維教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14,第七章,[例22])
另外,還應強調的是,盡管單純從知識層面分析,上述的兩種教學方法似乎沒有什么重要的差異,即無論我們是從實際情境出發組織教學,還是按照“問題與猜想”的途徑進行教學,學生最終似乎都能很好地建立起這樣一個認識:“在周長相等的情況下,長方形兩鄰邊的長度越接近,它的面積就越大。”但從促進學生思維發展的角度看,后一做法應當說更為可取,包括有益于學生徹底地糾正將周長與面積混淆的錯誤認識。當然,為了實現后一目標,教師在得出上述結論之后就應有意識地強調這樣一個推論:我們決不能將周長與面積簡單地等同起來!
最后,從幫助學生逐步學會數學地思維,特別是解決問題這樣一個研究傳統的角度進行分析,就上述內容的教學而言,我們還可提出這樣一個建議:在解決了最初的問題以后,我們還應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如果所涉及的圖形并非長方形,而是其他的圖形,如三角形等,所得出的結論是否仍然成立?再者,如果我們不對圖形的類別做出具體規定,這時又可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另外,建議讀者在教學中不妨也嘗試著讓學生說出自己對已得出結論的理解,包括相關的道理。因為,這也是我們在教學中始終不應忘記的一個基本事實,即應當充分肯定小學生的創造能力,而且,他們在這方面的一些具體表現往往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驚喜(這方面的一個實例可參見[1]:第三章,[例17])。
(待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