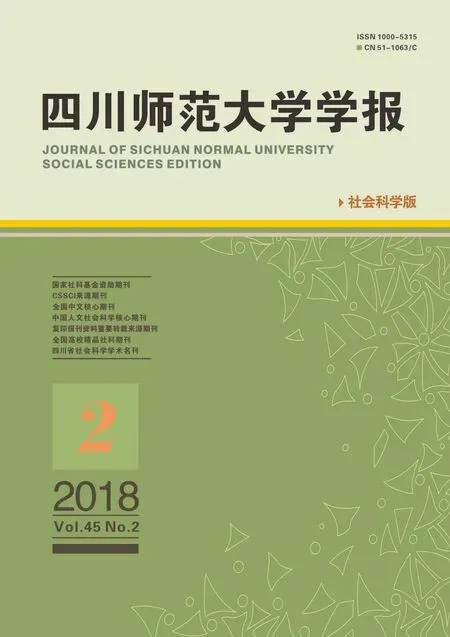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互聯網專車”勞動用工問題的法律規范
——以P2P模式為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2)
自2013年初互聯網專車進入出租車市場,便依托“共享經濟”靈活、高效的優勢,迅速地風靡全國。作為分享經濟在我國的創新實踐,互聯網專車有利于促進出行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統一,但同時互聯網專車市場也呈現出市場風險、道德風險與法律風險相交融的現狀[1]。為了興利除弊,多數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對互聯網專車市場的法律監管制度上,研究如何構建符合“互聯網+出行”新業態的監管方式。直到最近兩年,互聯網專車運營中各方利益主體不斷發生糾紛沖突,使學者們開始關注互聯網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問題,認為專車司機的身份認定問題關系到專車運營中各方主體的利益分配,也關系到互聯網專車模式能否健康、持續的發展。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在如何界定互聯網專車模式下用工關系的問題上分歧很大、不同觀點很多:有觀點認為應當認定為勞動關系[2],有觀點認為是承攬合同關系[3-4],也有觀點認為可以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并存[5-6],還有觀點認為應該是一種介于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之間的中間類型的用工關系[7]。前三種觀點在適用上有其不可逾越的障礙,第四種觀點具有可行性,但目前學界對中間類型主體的討論還僅限于對域外概念的簡單“套用”,缺乏理論基礎的支撐,也未能結合我國法律制度與現實狀況給出具體的路徑設計方案。本文嘗試對互聯網專車的用工關系進行分析、界定,借鑒域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規范我國“互聯網專車”用工關系的路徑選擇與設計方案。
一 問題的提出:從國內外“專車”用工關系糾紛案件說起
(一)國內外“專車”用工關系糾紛案件
1.國內首起“專車”用工關系糾紛案
2013年,司機孫先生與某北京汽車技術開發公司簽署了任該公司“代駕司機”一職的《勞動合同》,一年后,因公司解除與孫先生的合同關系而發生糾紛,孫先生向勞動仲裁部門提起勞動仲裁,而仲裁部門認為孫先生與該公司之間的關系不是勞動關系[8]。此案件為國內首例網約車平臺公司與其司機之間的勞動關系確認案件。其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是,專車平臺公司與司機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從根本上決定著雙方的權益分配及其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如果雙方之間被認定存在勞動關系,則司機應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享受勞動者應有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待遇;運輸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等運營風險的,應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關系為基礎來劃分責任關系;司機獲得的報酬應以工資而非勞務費來納稅等等。

圖1.P2P專車商業模式④
2.美國Uber專車司機身份糾紛案
2014年9月,美國洛杉磯的Uber專車司機Barbara Ann Berwich向加州勞動委員會起訴Uber公司(Berwich v. Uber)。原告Berwich向勞動委員會主張確認其與Uber公司之間的雇員關系(相當于我國的勞動關系),并要求Uber公司補償其被拖欠的勞務費、加班費等費用;加州勞動委員會最終裁決Berwich是Uber的雇員,兩者存在事實上的雇傭關系,并支持了Berwich的勞務費等費用的補償請求①。受該案裁決結果的鼓舞,大量的Uber司機們更加積極地爭取正式雇員待遇。2015年9月,以Douglas O’Connor為首的一些Uber司機向加州舊金山地區法院起訴Uber公司(O’Connor et al v. Uber),要求確認其為Uber公司正式員工而非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②)。該案被舊金山地區法院法官Edward Chen判定為集體訴訟(Class Certification),意味著加州16萬之多的Uber司機都可以加入該訴訟案,并在Uber敗訴后,向其主張員工待遇。該案在Uber公司上訴期間,原、被告雙方達成了和解協議,約定由Uber公司向Uber司機支付1億美元的和解費,和解后雙方承認Uber司機是Uber公司的獨立合同人③。
Berwich v. Uber案中,勞動委員會將其裁定為雇員關系(勞動關系)的結果,在美國爭議巨大;而O’Connor et al v. Uber一案,以雙方和解結案。可以預見,如果此案也被判定為雇員關系,巨大的員工福利負擔很可能直接摧毀Uber公司。事實上,不只是Uber公司,這些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創新公司都無法在傳統勞動關系所附帶的巨大員工福利“枷鎖”下負重前行。
(二)P2P互聯網專車之用工模式
目前市場上存在的“專車”運營模式可以大致概括為B2C與P2P兩類。B2C模式下,運營方式相對傳統,軟件平臺公司購置或租賃車輛,司機經聘任并嚴格培訓后上崗,人員穩定性高。此種模式下,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簽訂勞動合同,運營收入與風險由平臺公司掌握和承擔。此種模式下軟件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法律關系較為清晰。因此,本文主要討論用工關系較為復雜和混亂的P2P模式下的互聯網專車勞動用工關系(見圖1)。
P2P模式也即私家車加盟模式。該種模式主要是通過調動私家車主和私家車參與運營來滿足市場需求,平臺公司與私家車車主對運營利潤進行分成。P2P模式的特點是靈活、松散,是典型的“共享經濟”。其優勢是運營成本低,擴展速度快,受到消費者與投資者的青睞;劣勢是司機隊伍人員流動性高,服務質量難以統一,運營風險較高。如滴滴專車就是該種模式的典型。私家車主注冊成為滴滴專車司機的程序十分簡單,只要軟件平臺審核通過私家車主上傳的駕駛證和行使證,該車主就可注冊為滴滴的專車司機。靈活松散的特點背后是專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明確,理論與實踐上都存在很大的爭議。故本文著重來分析P2P模式下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法律關系及其帶來的相關問題。
二 “專車”用工關系不清晰所產生的現實問題
我國2015年《〈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曾試圖要求網約車平臺公司與司機簽訂勞動合同,但該條規定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支持的聲音多來自傳統出租車行業從業人員,認為簽訂勞動合同才能保護專車司機的權益[9];反對的聲音多來自法學學者與專車軟件平臺運營商們,其理由是傳統勞動法的用工模式與互聯網時代用工模式的靈活性、多樣性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不符合共享經濟發展趨勢[10]。例如,以Uber、滴滴為代表的專車平臺運營商們始終主張,他們的身份是“信息的撮合者,而非專車司機的雇主”[9]。
鑒于爭議較大,2016年最終頒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文簡稱《暫行辦法》)采取了折中的辦法,規定專車平臺與專車司機之間可選擇性地簽訂勞動合同。此種規定表面上兼顧了共享經濟的靈活性,但依然沒有回應專車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法律關系問題,專車運營市場上的用工混亂現狀也沒有出現實質性好轉。而且這種可選擇多種合同形式的“開放式”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鼓勵”了平臺運營商通過簽訂承攬合同、合作協議等來規避簽訂勞動合同所帶來的系列問題。
(一)“專車”司機權益缺乏保障的問題
根據《暫行辦法》規定,平臺公司具有與專車司機簽訂勞動合同的義務,但該條規定同時又指出,勞動合同不是雙方之間簽訂的唯一協議形式,平臺公司也可以選擇與司機簽訂其他形式的協議。如此開放式的規定,難以起到約束平臺公司履行與專車司機簽訂勞動合同義務的作用。實踐中,鮮見軟件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多數情況下,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簽訂的是“合作協議”或“承包合同”;或者是將勞務派遣公司加入進來,將勞動合同上的用人單位換成是勞務派遣公司,將平臺公司的直接用工變成了勞務派遣;還有一些情況存在,如勞務派遣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合同不是勞動合同,而是“勞務中介合同”,將用工方式從勞務派遣改為中介服務。據媒體報道,有些司機因為拒簽此種協議,而被凍結了賬戶資金[11]。
不管是合作關系、承包關系、勞務派遣關系,還是中介服務關系,平臺公司的目的都是為了逃避用人單位責任。在現有的制度規范下,專車司機都要對運輸過程中的風險承擔全部責任,其權益被置于極大的風險之中。
(二)交通事故責任承擔問題
《暫行辦法》出臺之前,對于互聯網專車出現交通事故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理論和實務上都存在很大爭議,主要圍繞軟件平臺公司應否承擔責任的問題討論激烈。由于專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沒有清晰的界定,在發生交通事故的情況下,很難從法律上要求平臺公司承擔責任。《暫行辦法》頒布后,明確了專車平臺公司承運人的法律地位⑤。根據《合同法》對運輸合同的規定,承運人應承擔運輸過程中的安全責任。然而,現實中,軟件平臺公司往往主張跟專車司機訂立的是承攬合同,根據《合同法》對承攬合同的責任承擔規定,承攬人需要承擔質量保證責任,這意味著承運人責任被轉嫁給了專車司機,即運輸中的事故責任完全由專車司機承擔。
如此的責任承擔方式,一是不符合“誰受益、誰負責”的風險承擔原則,平臺公司作為運營商,不應只分享經營收益,不承擔經營風險;二是不符合對乘客的風險擔保利益要求,一旦出現交通事故,專車司機作為自然人主體,其風險承擔能力有限,而且在發生安全事故的場合下,司機本人往往也會遭受人身或財產的損害,由司機個人承擔此種風險,既不現實也不合理。盡管2016年8月交通運輸部在《網絡預約出租車運營服務規范(征求意見稿)》中對這一現實問題做出了回應,明確了平臺公司在安全責任事故中的先行賠付責任。該規定雖然能夠保證乘客的利益不因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扯皮”而受損,但是,該規定僅針對的是乘客的傷亡賠償責任,對專車司機本人的傷亡或車輛的毀損沒有包括在內,這是對專車司機利益的忽視。
(三)行政處罰風險承擔問題
根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公司或其他企業法人應當對其員工的經營活動,承擔“自己責任”,即在勞動關系明確的經營活動中,員工在從事用人單位業務活動中所產生的法律后果由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員工本人不承擔責任。對于互聯網專車來說,其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的法律關系并沒有明確為勞動關系,因此,在專車司機通過軟件平臺接單而進行的運輸業務中產生的行政處罰責任,應該由專車司機個人承擔,還是應由平臺公司承擔用人單位的“自己責任”,爭議很大。
2015年的“全國專車第一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爭議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專車司機在進行專車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行政處罰責任應由誰承擔的問題。專車司機陳超在通過滴滴軟件平臺接單后,在送乘客到目的地的過程中,被交通執法部門工作人員以非法運營為由,罰款2萬元;陳超不服該處罰決定,將做出該處罰決定的交管部門告上法庭;陳超認為,自己不能代表專車,交管部門要罰也應該罰滴滴[12]。P2P模式下的專車運營中,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關系相對松散、靈活,平臺公司往往強調其與專車司機之間是承攬合同關系或合作關系,而目前理論和實務上都缺乏對兩者之間關系的清晰界定,故在不能明確勞動關系的前提下,專車司機缺乏要求平臺公司承擔責任的法律依據,這種結果無疑對專車司機是不公平的。
三 “互聯網專車”勞動用工的法律關系分析
(一)是否為勞動關系的分析
在認定勞動關系的問題上,我國大體沿用的是勞動關系從屬性這一標準。原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于2005年發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給出了對“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第一,主體適格性標準,即要求用人單位和當事人都必須是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適格主體;第二,從屬性標準,即勞動者須接受用人單位勞動規章制度的約束,接受用人單位的管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存在從屬關系;第三,業務相關性標準,即勞動者提供的勞動與用人單位的業務緊密相關,前者是后者的組成部分。盡管這一標準相對于當前的經濟模式有一定的滯后性和局限性,但仍然是確認勞動關系的重要參考。
根據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并結合我國《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這里來分析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是否是勞動關系。
首先,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不符合主體適格性標準。根據我國法律規定,企業不得開展工商登記經營范圍之外的經營活動,而專車軟件平臺公司的工商登記經營范圍一般為技術開發類,如滴滴公司的工商登記經營范圍就是技術開發類。嚴格來說,平臺公司不是專車運營的合法用人單位。
其次,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不符合從屬性標準。一方面,專車司機所賴以運營的生產資料即專車并非由平臺公司所提供;另一方面,盡管司機在運輸業務中需要遵守平臺公司制定的運營規則,但專車司機具有極大的運營自由度和業務自主性,如司機接單與否、何時接單完全根據自己的時間、行車路線來決定,而無需接受平臺公司的命令或指示,這與傳統勞動關系中勞動者須嚴格執行用人單位的工作時間、工作任務的模式明顯不同,兩者之間的“從屬性”已經弱化。
第三,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不符合業務相關性標準。以滴滴公司⑥中的北京滴滴無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為例,其工商登記中的經營范圍為:計算機軟件及網絡技術的研發;技術服務;技術咨詢;技術轉讓;銷售自行研發的軟件產品;經濟信息咨詢⑦。專車司機從事的是運輸業務,而平臺公司的經營范圍是計算機及網絡技術類,兩者相去甚遠,顯然沒有業務相關性。
第四,專車模式下的用工關系不符合我國勞動法的規定。從我國勞動法律的立法精神來看,我國并不提倡雙重勞動關系[13]115。1994年的《勞動法》明確否定雙重勞動關系,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雖然沒有明確禁止雙重勞動關系,但將可以建立雙重勞動關系的主體明確限定為非全日制用工的勞動者。從目前專車運營情況來看,大多數專車司機是有正式工作單位的全日制員工,他們以業余時間兼職的形式參與專車運營,有的專車司機甚至同時是幾個軟件平臺的專車司機。這種用工方式顯然不是符合勞動法上“一人一職”的用工原則。
(二)是否為居間關系的分析
專車的運作模式與居間合同關系有很多相似之處,看似是軟件平臺公司向專車司機提供訂立運輸服務合同的機會,但實質上,專車模式下的關系并非居間關系。
首先,軟件平臺并非像居間人那樣完全中立,并不干預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軟件平臺對專車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合同具有介入性。如對于那些信用等級高的乘客,在沒有司機接單的情況下,軟件平臺會強制向司機分配訂單,被分配的司機不能拒絕;再如,平臺還會對違約司機進行處罰;也會根據乘客對司機的評價對司機進行信用評級,并根據司機的信用等級制定司機“搶單”時的競爭規則。軟件平臺的這些“介入”行為,都不符合居間人的身份要求。
其次,軟件平臺并不是像居間人那樣以委托人的要求和意愿為服務目標,平臺不僅為司機的“進入”設置條件,并為司機的運營活動設置一定的規則,還要在一定范圍內對司機進行獎勵或處罰的管控,顯然不同于居間人完全中立的地位。
再次,平臺公司與居間人獲取報酬的方式有本質的區別。居間人因提供訂立合同的機會來獲得報酬,不分取合同項下標的業務所產生的收益;而平臺公司從專車司機完成訂單所獲的收益中分取提成。
(三)是否為承攬關系的分析
目前學術界有學者支持專車司機與軟件平臺公司之間是承攬關系,其理由有兩點。首先,私家車主注冊為軟件平臺的專車司機后,意味著雙方就專車司機按照平臺發送的乘客和路線信息完成運輸任務的合意,專車司機將乘客送到指定地點后即為完成工作,平臺提取分成后的收益為司機的報酬,符合承攬合同的形式要件;其次,專車司機是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或勞動工具(即車輛)、使用自身的技能,獨立自主地完成運輸工作,平臺只對司機的工作質量作了要求(即乘客的滿意度),只關注司機的運輸結果,并不干預司機的運輸過程,在司機完成工作后,以乘客的滿意度作為工作合格與否的判斷標準,若司機的運輸工作沒達到標準,平臺會對司機行使降低報酬直至終止合同的權利,符合承攬合同的實質要件。
然而,將互聯網專車模式下的司機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界定為承攬關系,是機械地套用現行合同法中關于承攬合同的規定,不符合“共享經濟”調動社會閑置資源共創財富、共享收益的理念,抹殺了共享經濟靈活、松散的運行模式所帶來的綜合效益優勢。傳統承攬合同法律關系對應的是傳統經濟模式下的傳統勞務關系,已經不能“生搬硬套”地用在以互聯網為媒介的“共享經濟”模式之上,否則就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癥狀。
第一,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在承攬合同關系中,承攬人須對合同項下的工作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意味著一旦發生運輸風險,將由承運人即專車司機承擔全部責任,而軟件平臺將不負任何責任。這種風險承擔方式,對專車司機與乘客的保護都非常不利,必將損害專車司機參與專車運營的積極性,也會降低消費者對專車運營安全保障的信心。
第二,辯證法認識論告訴我們,認識事物時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對于互聯網專車來說,軟件平臺是其降低運營成本的技術手段,是互聯網技術時代下運輸行業發展的一種新型的運營“現象”,其本質仍然是運輸。從專車軟件平臺公司的經營行為本質來看,其核心業務就是運輸,而不是軟件平臺服務,軟件平臺只是其進行運輸業務的工具而已;并且,軟件平臺服務并不是其收益來源,因為各方使用軟件平臺的服務都是免費的,平臺公司真正的業務收益來源是運輸,只有專車司機完成了運送乘客的業務,才能產生收益。因此,平臺公司的真正業務仍然是運輸。作為以運輸為核心業務的平臺公司,對運輸風險完全不負責任的承攬合同關系顯然不符合權利義務對等的民事行為基本原則。
四 域外專車用工關系界定模式的嘗試——中間類型的就業主體
如果將互聯網專車模式下的勞動用工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范圍,會沖擊分享經濟松散、靈活的模式優勢,束縛分享經濟的發展,也會顛覆傳統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而完全否認互聯網專車下用工關系的勞動關系屬性,又會將專車司機的權益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域外一些國家嘗試了構建“中間類型主體”的路徑,具有借鑒意義。
德國學者創建了類似雇員(arbeitnehmerahnliche person)的概念,用來描述那些處于純勞務工作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那一類從業主體,他們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松散、靈活,卻在經濟上對企業具有依賴性[14]。在德國,類似雇員享有職業安全權、健康權、年休假權等權利,受《照護時間法》保護,受勞動法庭的司法管轄,能夠通過簽訂集體合同來保護相關權益,不受非法歧視,但是,類似雇員不能加入職工委員會,也不受解雇立法的保護[15]。
英國立法上除了勞動者(worker)和雇員(employee)這兩個概念外,還有一類“非雇員的勞動者主體”⑧,即介于雇員與純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就業主體。非雇員勞動者享有最低工資保障、法定病假工資、帶薪休假、夜班限制、不受用工歧視、不受非法扣減報酬等權利,但是,不享受不公正解雇保護、遣散費、產假、陪護假等權利和福利[16]50。
加拿大立法和判例中也承認在雇員與獨立承攬人之間存在一類中間類型的就業主體,即依賴型承攬人(dependent contractor)⑨。依賴型承攬人,是相對于獨立承攬人而言的,是指那些在經濟上依賴于相對方的勞務提供者,其在提供勞務的過程中所承擔的義務更接近于雇員。法官判斷依賴型承攬人的標準包括雙方關系的持續性、合同關系的依賴性、工作的唯一性等;依賴型承攬人受集體談判立法的保護,享有合同終止獲提前通知的權利,并享受集體談判立法中規定的權利內容⑩。
五 界定與規范“互聯網專車”用工關系的路徑探索
如前所述,平臺公司與專車司機之間的關系具有明顯的共享經濟特征,無法被簡單地界定為傳統的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筆者建議,借鑒域外創建“中間類型主體”的做法,在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之間創建一類“類勞動關系”,在勞動者與勞務者之間創建一類“類勞動者”。使用“類勞動者”的概念來指代那些對經營者的依賴性要顯著低于傳統雇員,而在經濟收入上對經營者的依賴性又高于一般的純勞務提供者。創建“類勞動者”與“類勞動關系”的概念,首先要從理論上解決“類勞動關系”對傳統勞動關系在組成與結構上的改變。
(一)“類勞動關系”的理論基礎
勞動契約制度建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工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依據的是成年男性勞工的工作生活特性,他們在雇主的工廠中以不定期契約的形式,服從雇主的指示,提供特定的勞務[17]9。勞動契約關系以提供勞動的場所單一、時間集中、所需技能單純為主要特色。無庸置疑的是,自信息技術推動的資訊時代伊始,勞資關系的組成與結構就開始逐步地被“改革”,從工會的組織動員方式、勞資關系的維系規制、雇主與勞工的個別關系上都從根本上發生著改變。在互聯網技術推動的共享經濟大潮下,這種勞資關系的組成與結構的改變更加深刻、更加顯著。具體而言,這些改變主要體現為:第一,雇主與勞工關系,從傳統的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逐步演變為組織的從屬性與技術的從屬性;第二,工作時間,由傳統的八小時正規工時制向彈性工時轉變;第三,工作場所,由集中型工作場所向分散型工作場所轉變;第四,勞務供需關系,由原有的雙務關系演變為多邊關系。
世界各國面對上述變化,已經采取諸多應對辦法,包括擴大解釋勞動關系從屬性理論;通過接觸管制來減低勞動保護法的規范水準,提高勞動市場當事人的自治能力;增加勞動契約制度的彈性來應對現實的多樣性等等。其中,建立松散而自由的勞動雇傭關系,已是經過各國實踐、行之有效的新型勞資關系形態。
回顧勞資關系發展歷史,從奴隸制時代龐大的奴隸階層提供勞動供少數上流社會成員悠然自在地創造政治、文化、藝術文明,到農奴取代奴隸以自由換取生存為貴族提供統治基礎,再到產業革命解放農奴后,取而代之的廣大債奴在工廠勞作,依然是以自由換取生存。這種形態所伴隨的意識形態的斗爭被信息社會的到來終止,因為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建立將以“自由換取生存”的勞動方式徹底排除在人類文明之外。松散、自由的勞雇關系,不僅是使人性尊嚴獲得應有的尊重的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更是現代經濟發展大潮下勞資關系不斷向前演進的必然形態。
(二)我國規范“互聯網專車”用工關系的路徑選擇
1.立法中增加“類勞動關系”與“類勞動者”的概念
筆者建議,將來在修訂《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或出臺某領域共享經濟運營模式的單行法規時,可明確“類勞動關系”和“類勞動者”的概念。“類勞動者”的身份確定應符合以下特征。
第一,主體為親自提供勞務的個人。“類勞動者”不包括那些由第三方用人單位指派從事勞務的個人,亦不包括有權選擇他人代為提供勞務的個人。如,對于互聯網專車,《暫行辦法》中明確了平臺運營商有義務確保線上和線下司機的一致性,即專車司機必須親自提供運輸服務。現實中,滴滴打車軟件平臺也會提醒乘客,“當遇車輛信息不符時,建議您拒絕乘坐并進行投訴”。
第二,“類勞動者”對經營者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人身從屬性。在互聯網專車運營模式下,司機在工作過程中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與靈活性,不存在傳統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對員工嚴格的控制與管理關系。從屬性的弱化,也是共享經濟下用工關系的典型特點,是“類勞動關系”的本質特征。
第三,“類勞動者”在報酬獲取上對經營者具有依賴性。“類勞動者”的報酬獲取主要來源于某個經營者,其收入穩定性取決于該經營者,工作任務的接受與運營規則上受經營者的調控。對依賴性的認定,一般有兩個方面的標準。一是提供勞務的專屬性程度,即“類勞動者”的經濟收入中的絕大部分來源于某一個經營者。如,德國的標準是50%以上的收入來源于某一經營者;加拿大則將這一標準提高至80%。筆者認為,我國采用50%的標準為宜,過低的標準勢必將會給平臺運營商帶來過重的負擔;而過高的標準也會將多數的專車司機排除在“類勞動者”的范圍之外。二是提供勞務的持續性程度,如果勞務的提供僅是一次性或偶然性的短期行為,那么就不具備報酬獲取上的依賴性。持續性要求,雙方之間的勞務提供行為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具有一定的時間長度要求。
2.賦予“類勞動者”一定范圍內的權利
“類勞動者”畢竟與勞動法中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有所不同,對其的保護應比照對勞動者的保護,并在保護程度和范圍上有所限制,即法律對“類勞動者”的保護要弱于對“勞動者”的保護。參考域外國家保護中間類型勞動者的做法,大多將這種保護定位于對其經濟收入、休息等基本勞動權利的保障,而對于解雇保護及其他福利性待遇則排除在此類保護范圍之外。此種保護力度符合共享經濟下用工關系的特征,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具體而言,我國在構建對“類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時,也應著眼于以下權利內容。
第一,報酬保障權。報酬保障主要是指對“類勞動者”的基本勞動報酬應及時、足額地發放;平臺運營商在制定提成、補貼規則時,應避免利用壟斷地位優勢,制定有損“類勞動者”利益的提成、補貼規則。
第二,職業安全與健康權。互聯網平臺運營商具有保障“類勞動者”職業安全的義務,建立相應的安全保障制度措施來避免工作過程中的風險和傷害。對于互聯網專車來說,安全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安全駕駛方面的監督制度。
第三,解除合同獲事前通知的權利。鑒于“類勞動關系”中雙方松散的關系,各方都有權隨時終止已經達成的勞務提供協議。又鑒于“類勞動者”在經濟收入上對經營者具有依賴性,為避免勞務提供者突然喪失收入來源的風險,應要求經營者一方履行終止合同前的通知義務。若經營者違反此通知義務,則應該給予“類勞動者”合理的經濟補償。
第四,不受就業歧視的權利。域外各國在構建對“中間主體”的權利保護時,幾乎都將“免受歧視”作為必要權利內容之一。我國也應不例外地將“不受歧視”納入到對“類勞動者”的權利保護范圍之內。具體而言,我國《就業促進法》第三條規定的勞動者的不受歧視權,也應適用于對“類勞動者”的保護。
第五,社會保障的權利。依照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類勞動者”可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自行繳納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但在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上還缺乏可行的途徑。如前所述,諸如專車司機之類的“類勞動者”對經營者存在經濟上的依賴性,同樣面臨著合同終止所帶來的突然失去收入來源的風險;而且,互聯網專車這種運輸行業,本身的職業風險相對較高,一旦發生交通事故,由專車司機獨自承擔責任后果,必將給此類個體帶來沉重的負擔。因此,筆者建議,我國在構建自由職業人員參加失業保險與工傷保險的路徑探索中,可以考慮將這些“類勞動者”的主體涵蓋其中,以適應分享經濟大潮下新型勞動用工模式日益常態化的必然趨勢。
六 結語
“互聯網專車”是共享經濟改革大潮下的新生事物,給我國的社會經濟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分享經濟剛剛嶄露頭角,今后勢必將更廣泛地影響各行各業的運營模式,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將參與到分享經濟模式下的運營中。如果按照傳統勞動法的規范模式,分享經濟運營模式下的勞動提供者將面臨的是充滿風險的就業環境,重新界定與分享經濟相容的勞動用工法律關系及構建相應的保障體系已是不能回避的問題。我國面對分享經濟大潮的影響,也應該引入中間類型的用工主體概念,即將共享經濟用工模式下的這類就業主體賦予“類勞動者”的身份,將此類中間類型的用工關系可界定為是“類勞動關系”。參照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征來分配雙方主體的權利義務,這種權利義務的分配界限應以既不束縛分享經濟優勢的發揮,又不會將勞動提供者置于高風險的用工環境下為宜。
注釋:
①參見:Uber Technologies Inc.v. Barbara Berwich,Case No. CGC-15-546378,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June 16, 2015.
②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被譯為“獨立締約人”或“獨立合同工”,是美國法律中的一個概念,指與企業簽訂合同,約定在自己的工作場所,利用自己的設備或雇員,完成特定的工作,由企業支付報酬的工作者,類似我國的承攬合同關系。
③參見:Douglas O’Connor,et al.,v.Uber Technologies,Inc.,et al. Case No. 15-cv-00262- EM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August 18,2016.
④資料來源于王晨曦《中國互聯網出行市場年度綜合報告2016》(2016-06-20), https://www.analysys.cn/analysis/trade/detail/1000099/。
⑤《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應當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
⑥這里的“滴滴公司”指滴滴系,包括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滴滴無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滴滴(中國)科技有限公司。
⑦參見: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http://qyxy.baic.gov.cn/。
⑧參見: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of United Kingdom, Article 230(3).
⑨參見:British Columbia Labor Relations Code, R.S.B.C. 1996, Chapter 244, Section1(1).
⑩參見:Drew Oliphant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v. Harrison, Case No. 2011, ABQB 216.
[1]劉俊海,張宇翔.共享單車需騎行在法治軌道上[J].群言,2017,(5).
[2]辛穎.專車司機身份之爭[J].法人,2015,(11).
[3]張素鳳.“專車”運營中的非典型用工問題及其規范[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6).
[4]盧鑫.專車司機與打車軟件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探究[J].法制博覽,2016,(4).
[5]顧偉.論網絡專車平臺與專車司機之間的法律關系定位[J].法制與社會,2016,(14).
[6]何雪穎.專車司機身份之爭——從美國加州Uber司機訴Uber公司案談起[J].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6,(5).
[7]班小輝.論“分享經濟”下我國勞動法保護對象的擴張——以互聯網專車為視角[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
[8]彭斐.全國專車第一案:私家車司機被罰狀告客管中心[N/OL].(2015-03-30).http://tech.sina.com.cn/i/2015-03-30/doc-iavxeafs3389180.shtml.
[9]王建平,崔杰.“專車”司機與網約車平臺簽訂勞動合同:該不該?[N/OL].(2015-11-16).http://zhuanche.juhangye.com/201511/weixin_1797459.html.
[10]黃瑤.法學專家:專車不該強制平臺與司機簽勞動合同[N/OL].(2015-11-05).http://it.sohu.com/20151105/n425410086.shtml.
[11]吳燕雨.滴滴專車司機拒簽合同,賬號被凍結[N/OL].(2015-06-22).http://fun.youth.cn/2015/0622/1327363.shtml.
[12]馮雪.中國“專車第一案”被罰兩萬司機:我不代表專車,要罰就罰滴滴[N/OL].(2015-04-16).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5_04_16_316159.shtml.
[13]鄭尚元.勞動合同法的制度與理念[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14]〔德〕曼弗雷德·魏斯,馬琳·施米特.德國勞動法與勞資關系[M].倪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15]PENNINGS Frans, BOSSE Claire.TheProtectionofWorkingRelationship:AComparativeStudy[M].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1.
[16]European Parliament. Social Protection Rights of Economically Dependent Self-employed Workers[R]. European Union: IZA,2013.
[17]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