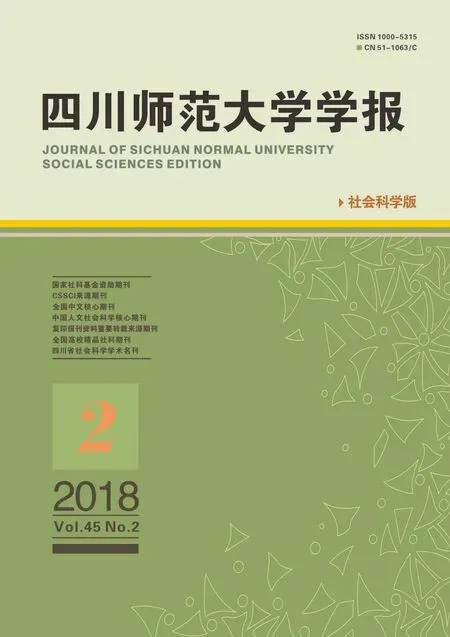民國婦女婚姻變革中的家庭財產觀
——基于民國婚姻訟案的考察
吳 燕,張 汝2,許 良
(1. 電子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成都 611731;2.樂山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張汝(1964—),女,四川樂山人,樂山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許良(1993—),男,陜西咸陽人,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研究生。
民國以來,中國婦女的婚姻觀逐漸變化。時論對民國婦女婚姻權利覺醒常予以肯定。如1929年《大公報》稱:“離婚案件逐年加增,原告出自女子者為多,說明女界思想之日漸進步,不愿受男子之壓迫”[1];1935年《東方雜志》也載文將離婚率增加的原因歸結為“思想的發展”、“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漲”[2]315,316。同時,時論對民國法律保障婦女權益的作用亦予以贊賞。如胡漢民稱贊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民法親屬編》中的親屬繼承兩編,是把“過去一切大家族制度的專制,倚賴男女不平等種種弊病,也都可以一掃而清了”[3]884。今天的學者除了首肯民國婦女婚姻權利制度建設外,還從司法方面探索了婦女婚姻權利意識覺醒,如劉昕杰、徐靜莉等人的相關論文,以及近年山西大學若干博碩士論文對根據地社會改造中的婦女婚姻問題的研究①。但是,在檢閱大量婚姻訟案之后,我們感覺到過去在關注婦女權利觀確立的同時,對婦女的義務觀尤其是對婦女在家庭財產觀念方面的認知還注意不夠,對婦女的某些婚姻行為和婚姻心理欠缺研究。比如,論者多謂婦女權利意識覺醒,卻少有論及相應義務觀是否建立;婦女勇于爭取婚姻自由權,但她們在婚姻自由名號下為自己爭取自由和爭取財產的權重有多少;思想解放為寡婦再婚開道,法律為寡婦再婚提供保護,可是寡婦再婚受哪些因素影響與制約等等問題,均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成果發表。黃宗智的《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4]和《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5],潘大禮的博士論文《民國三四十年代湖北婚姻沖突案例研究》[6]等論著雖曾論及這些問題,但是限于主題,討論并不充分,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況且,當初不顯眼的問題,今天似有擴展之勢。女性在婚戀中過分看重財產已成共識,有些女性把婚姻視為快速致富的手段,“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即為形象的總結。這一情況在精英和草根階層中都可見到,這是婦女解放的逆流,研究它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兩點需要先說明:第一,本文并不否認婚姻自由大潮中婦女婚姻觀的進步,而是旨在從婦女的家庭財產觀說明過去忽略了婦女婚姻義務觀的一種傾向;第二,本文案例大多采自婚姻訟案,反映的多是不識字的底層婦女對家庭財產權的認知,同時也用一些初通文墨的普通婦女的觀念和言論加以對照分析,以求研究更加全面。以前,筆者以為這兩類婦女的觀念有很大差別,仔細解讀案例,才發現并不盡然。
一 相互扶養還是被扶養:婚姻案中婦女權利義務觀不對等
按現代觀念,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義務是平衡、對等的,享受了權利,理當承擔相應的義務,這是現代法制的基本準則。在婚姻關系上,晚清到民國的幾部民法都不分性別地給予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在婚姻中的各項權利,當然也不分性別地規定了權利人相應的義務。雖說規定的是男女平等,實際上對婦女的意義大于對男子的意義。因為婦女們可以享有傳統的婚姻家庭關系中所沒有的權利,而丈夫則要讓渡過去獨享的這些權利。很自然,妻子與丈夫分享婚姻家庭中的權利后,按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對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也應相應分擔。但是,從晚清到民國,包含男子和婦女在內的很多人尚未及建立權利義務衡平對等概念,法律實施亦然。就扶養而言,男女都缺少扶養權利和扶養義務對等的行為和觀念。
對家庭中夫妻的扶養關系,未頒布的《大清民律草案》、1925年《民國民律草案》和1930年《民法親屬編》的規定有所不同:前兩部法律都規定“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7]173,353;后一部法律之第1026條規定了夫妻雙向的扶養義務,“家庭生活費用夫無支付能力時,由妻就其財產之全部負擔之”,第1047條規定了“夫妻因家庭生活費用所負之債務,如夫無支付能力時,由妻負擔”,第1048規定了“夫得請求妻對于家庭生活費用為相當之負擔”[8]90,92。從這些條款可知,一般情況下,法律規定由丈夫負責供養家庭、清償家庭債務,但丈夫無能力時,妻子就應承擔責任。一個享有了法律賦予的權利、具有獨立人格的妻子,理當做到這些。但是,一些婚姻訟案中的婦女,秉持的卻是單向被丈夫扶養的觀念,她們一邊鬧離婚,一邊卻無獨立理念。在婚姻中,常常是當丈夫靠不住時,婦女就逃避家庭中本應承擔的同居扶養義務,“背夫”離家,或另攀高枝,引發重婚或妨害婚姻的糾紛,或離婚時漫天要價,更弱勢的婦女則自尋短見。
比如1938年天津徐楊氏訴武張氏重婚案中,被訴人武張氏與徐楊氏之子結婚、生一女后,嫌夫家貧窮而回娘家,后又在其母張馬氏的幫助下,以夫亡在娘家寡居多年為由,經媒人說合而嫁與武永生,并在徐楊氏訴至警局后辯稱:“我先嫁姓徐的,以后嫁姓武的,因為徐家不養我,我們夫婦不和。”武張氏認為丈夫理當供養她,因夫貧不能供養,她便理當“背夫”而去,卻不知不能因貧窮而推卸應承擔的相應的同居和“雙向扶養”義務。最后,法院判決:武張氏重婚,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張馬氏幫助其女重婚,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理由是:“查該武張氏嫌貧愛富改嫁重婚,就其品行而論,固數罪無可恕,惟究系村婦無知,量刑姑予從輕。至該張馬氏極力贊助其女重婚,意在得財資以為利,故雖系從犯亦無減輕余地。”②
又比如1943年天津地方法院審理判決的、由檢察官起訴的趙韓氏、張趙氏妨害婚姻一案,被訴人仍持應單方即丈夫供養的觀念。該案中,張趙氏的丈夫張吉泰外出做工,無錢寄回家,張趙氏遂以生活無著為由回到娘家;其母趙韓氏對人稱其婿亡,托人把張趙氏嫁與任姓男子為妻,并按照習俗舉行了結婚儀式,拜過天地、請過客,結婚儀式完全符合民國《民法》第982條規定,張趙氏犯重婚罪。當法官問:“有男人為何又嫁人?”張答:“沒有飯吃。”斬釘截鐵的回答,說明張趙氏認為丈夫窮而另尋高枝理所當然。這里需注意的一個細節是:張趙氏嫁給任姓男子時,后者給了260元錢,分給了張趙氏的母親、婆母、媒人。這筆錢既可認定為彩禮,也可認定為買賣。若認定為彩禮,張趙氏就是重婚,應當受法律處罰;若認定為買賣,張趙氏就是被買賣的受害人,不應受到法律處罰。該案當事人并未糾纏到底是什么罪名,即接受重婚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緩刑二年結案③。由此可見,張趙氏連自己是否犯罪這種必須弄清楚的事實都不辨明,要她明白法律規定夫妻互相扶養是雙方權利義務更無從談起。
因循過去大家庭居住的習慣,那時的判例規定:“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依法應互負扶養之義務,是夫之父母對于同居之子媳自應負扶養之責。”[9]271929年,天津某婦女的丈夫失蹤,她向法院控告公公“虐待,不事養贍”,公公在法庭上辯稱其媳不守婦道,過去曾給該媳每月20元養贍費,現在她如回家,“也不辭贍養之責”;推事告知該婦女:“如欲索款,盡可遞呈要求,可以拍賣汝夫房產,欲歸家度日亦可,兩者孰是,任汝自擇。”[10]問題是公公承擔了贍養媳婦責任后,媳婦的義務何在呢?推事并未明示。1940年,天津朱書印告其妻與他人重婚案,該案中妻子也有該由夫家人扶養的觀念。朱訴稱,他與周趙氏原為夫妻,他出外做事,給妻子留有大洋120元、洋面1袋半,他走后,周趙氏卻聽信了周思義說朱已死亡的讒言而嫁給了周思義,朱要求民事賠償、返還彩禮和其它物件;周趙氏卻辯稱:“改嫁原因是生活困難,并聞朱書印已在關外身故,要求夫兄朱書深扶養不準許。”派出所所長證實了這一說法④。那么,周趙氏依據什么要求其夫兄“扶養”呢?1930年《民法》第1114條規定:互負扶養義務的親屬,包含:“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姐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8]96如果說前一案中要求公公撫養媳婦還符合第二條,那么后一案中周趙氏要求夫兄扶養則沒有法律規定。但是,人們思想中有夫兄扶養周趙氏是理所當然的觀念,更能揭示這一觀念普遍性的證據則是天津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周趙氏有配偶而重為婚姻,處有期徒刑二月、緩刑二年,理由是被告沒有證據證明原夫已亡,“其為有配偶而重為婚姻,實已口無疑義。……惟查被告犯罪原因,究系因感受生活壓迫,而其夫兄又不予扶養,乃始出此下策,其情不無可原”⑤。如果說周趙氏和派出所所長口中的“扶養”只是一般民眾的認知,法院稱夫兄應“扶養”則具有法律效力。顯然,這不合法律規定。20世紀40年代,四川德陽縣司法處也作出過類似判決。德陽縣婦女鐘翠華以遭受丈夫吳紹陵虐待為由而回娘家居住,并到德陽縣司法處訴求和吳離婚,吳不同意,司法處判決吳的父親吳湘濤給鐘扶養谷⑥。法官在夫妻扶養問題上都深受夫家應單方扶養妻(媳)的傳統觀念左右,現代法律知識闕如的家庭婦女安能擺脫其影響。
很多底層婦女在法庭上毫不掩飾重婚行為的動機,坦承因丈夫窮就要和別人結婚,說明她們根本不知道“相互扶養”概念。婦女因無知而犯罪,對此,法庭也多無奈。1929年,代理司法院長魏道明指出:“惟女子既有財產權利,法庭應尋求離婚責任之屬于何方面,男女責任之地位應平等。通常離婚案件每多女子向男子要求賠償,此后如曲在女子方面,男子亦可同樣要求賠償。”[11]19這證明要求丈夫單方扶養的習慣性心理普遍存在,否則,司法院長不會作出此類指示。
報刊所載消息和相對嚴肅的司法統計都顯示,離婚案大多為婦女尤其是底層婦女提出離異訴求。1929年9月,天津婦女協會統計一年有97件由女性提出的離婚案,其中42件是因丈夫無職業,離婚原因多是虐待或遺棄,占總比例的43.2%[12]。1930年代中期的《司法統計》也稱離婚者的職業以“男性失業與無業者多”⑦。因男子經濟條件差,婦女產生離異的現象同樣發生在共產黨領導的已有一定社會改造的抗日根據地。山西大學杜清娥博士的調查結果顯示,華北抗日根據地離婚案中,很多是因感情不和,“從榆社、武系統計可知,由女方提出離婚者則貧農妻子最多,即婦女嫌貧愛富是造成婚姻失敗的主因”⑧[13]137。這揭示出“相互扶養”的觀念不是短期內能夠建立的,哪怕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對社會進行了力度較大的改造后,仍有婦女沒有這種觀念。
把丈夫失業、家庭經濟窘迫和虐待遺棄聯合考慮,會出現兩個相反的情況:第一,丈夫因失業或經濟窘迫而遺棄妻子;第二,丈夫失業后,妻子棄夫而去。在這兩種情況下,被棄的對象不同。雖然不能指責因貧窮而離異就是缺少相互扶養的責任感,但是最后被準予離異的數量和比例則能說明究竟是否缺少相互扶養責任觀。從1926—1928年間天津離婚原因和審判結果的統計(見表1)中,可以透露提出離婚的婦女有無夫妻相互扶養的觀念。其中,提出離婚的多為婦女,男子提出者約占1/5;三年共92件離婚案中,由男子提起的19件,法院準予離異的為5件,占男子提起離異比例的26.3%;由女子提起的73件,法院準予離異的有36件,占女子提起離異比例的49.3%,婦女提出離婚成功的比例高于男子。而這由婦女提出的73件離婚案中,有53件原因是逼良為娼、被遺棄和虐待,占女子提起離婚案的72.6%;在這53件離婚案中又有25件被準予離異,約為該三類案件的47.1%,有超過一半的案件被法院駁回。逼良為娼、被遺棄和虐待當然是離婚的正當理由,但超過一半的比例被駁回也證明了有些婦女企圖以這些理由規避“相互扶養”責任。

表1.1926—1928年三年天津離婚原因和判決結果統計表[14]
怎樣認定遺棄,需要界定丈夫是否扶養和有無扶養能力兩種情況。1929年,因江西廬咸英與曾焱春離婚案,最高法院就如何扶養作出判決:“夫妻均需要扶養,又均缺乏扶養能力,即不能以一方不給扶養,他方遂持為遺棄之論據。”該案中,妻子廬咸英向江西高院起訴丈夫曾焱春遺棄,要求離婚;江西高院認為無理由,判決不離;廬不服,上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駁回上告。廬辯稱:丈夫在外當兵十余年,音信全無,回到江西也不見面,是為遺棄;丈夫在外有情人,故而不思家;被告現在本城,仍無半文給養,此種遺棄,甚于法律上的虐待;原判不應以禮教為詞,判不準離。最后,最高法院駁回上告、維持原判,理由有兩點:第一,音信全無,沒有寄錢回家不能歸責于被上告人,丈夫在外有情人而不回家,上告人沒有證據;第二,“夫妻之間扶養,系一種相互關系,故妻需要扶養,夫有扶養能力時,夫固負扶養義務,若夫需要扶養,而妻有扶養能力時,則妻亦負扶養義務,倘夫妻均需要扶養,又均缺乏扶養,即不能以一方不給扶養,他方遂持為遺棄之論據。此乃法律上至當之條例,也適合男女平等之精神。……惟被上告人從前缺乏扶養能力(即經濟困難),已成顯著事實,殊難以不給扶養指為遺棄。至為被上告人現在本城仍無半文給養,則在上告人未能證明被上告人已有扶養能力,……上告人既別無應行離婚之正當理由,乃徒借口婚姻自由,攻擊原判適用法律不當,實涉誤解”[14]。對比廬咸英和最高法院的理由,能更清楚地理解什么叫“遺棄”:廬所稱遺棄是丈夫不供養;最高法院則說明要分清是“不能供養”還是“不供養”,能供養而不供養才叫遺棄,無能力供養而不供養則不能謂為遺棄。
20世紀30年代,最高法院多次訓令何為“遺棄”,1934年還發布上字第2015號文明確規定:“夫妻財產制如未以契約訂定,夫對于家庭生活費用固應負支付之責,惟夫如無支付能力,妻即應就其全部財產而為負擔,尚不能因夫之無支付能力,即指為惡意遺棄。”[15]361936年,最高法院一則判例要旨謂:一定要“惡意遺棄”才能提出離婚,“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請求離婚,……所謂惡意遺棄他方者,固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之義務或扶養之義務而言,但違背義務之一方如未達于惡意遺棄之程度,他方不得據以請求離婚”[16]32。最高法院多次就“遺棄”做內容相同的訓令,說明現實中因遺棄而引起的婚姻糾紛不少,尤其是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究其根源,在于很多當事人因生活困難而不愿承擔“相互扶養”的義務,這一現象在婦女中較男子為多。
二 孰輕孰重:婚姻訟案中婦女爭自由和爭財產的權重
傳統社會中,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敲定。民國伊始,婚姻自由思想逐漸傳播,法律的修訂和實施又在司法實踐上保障婚姻自由的落實。婚姻自由包含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結婚、離婚均依包含婦女在內的當事人自由意志而定。過去離婚,一般由丈夫“休妻”而非妻子言離,現在妻子也有表達離婚意志的權利。《法律評論》載文稱贊從男子專權離婚到自由離婚是“吾國婚姻史上之一大新紀元”[17]5-6,但深入到離婚訴訟案例背后,會發現還有遠比“進步”更豐富的內涵。在爭取婚姻自由的訴求下,婚姻訟案中既有對自由權和財產權只能擇其一的無奈,又有對二者抱有熊掌和魚都要兼得的心思,不同的女性對自由和財產的追求不盡相同,但又并非全然相異。
婚姻自由是指根據當事人的自由意志而決定婚姻。可“自由意志”又依據什么產生?按字面意思,婚姻自由應建立在了解和感情之上。但是,現實生活則不盡然。一般認為,都市知識女性追求的是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但從一些調查看,她們愿建立感情的基礎卻離不開財產。若干案例可以為證。下邊部分案例取自報刊,不排除報刊為賺取眼球而對事實添油加醋的情況,就個案而言,未必完全如實;但就趨勢而言,報刊的加工傾向,反映的正是時下婚姻觀的某些側面。
1928年3月1號和8號的《大公報》登載了11位青年男女婚姻觀念的調查結果,其中4位女青年中有3人要求男方“家勢中等”,1人要求“小康”,而且對男方的學問學識有要求,如“立或坐像大人物樣。學問各樣都好,才識天資”,至少要大學畢業,刻意用英語表達,“須有common sense and intelligent”,學問要“professional”[18]。能填寫該調查問卷的女青年,至少是初通文墨的人,她們對家勢的看重說明她們對男方有財產要求。應該說,把對方的經濟條件作為婚姻選擇要素無可指責,要注意的只是財產在涉婚諸因素中的比重。若女方對男方的財產要求,超過了男方的能力,或諸因素中,財產滿足了,可忽略其它因素而成婚,或其他因素滿足,財產不達其要求,則不成,才是“以財嫁人”傾向。自主婚姻中,不管是結婚還是離婚,以男方財產為婚姻成敗導向的事例并不少見。1933年,《新新新聞》就以《現代女兒談戀愛,條件離不了洋錢》為題報道了一則消息。該消息稱,川大某家庭殷富的男生,不允家長說的親事,自行與一女士談戀愛,而該女士提出滿足四項條件后才愿與他結婚:第一,脫離舊家庭,另立新居,第二,退去已定的未婚妻,第三,購置500元金飾品及木器,第四,房租必有十年為期的預約;該男士因不能滿足三、四條而自殺,該女士對該男生的死不僅不悲切,還要求退還訂婚戒指[19]。故而,報紙以嘲諷來報道此事件。當時,各類報刊常刊載此類事例,不乏嘖嘖指責之聲,直言有些在校讀書的女子未必自尊,未必真心想自食其力,大多數讀到初中的女生,想的基本是快婿、洋房、汽車、游戲場、時髦裝飾品,“考中國社會上,無論是貧富階級的家庭,并沒有一個作家長者的來教導他的女兒,告訴她自謀生計的道路。她自幼處在這樣一種‘女依男’的惡風氣的社會里,更遇到一般最闊綽的小姐少奶奶似的女同學,從知識萌芽的那一天,就沒有接受著良好的影響”[20]。顯然,有些都市知識女性標榜婚姻自由,一邊奮力掙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羈絆,另一邊又自覺不自覺地掉進以金錢衡量婚姻的窠臼。
底層女性在婚姻自由權和財產權上的取舍表達很直接,很多案例表明她們把婚姻自由權放在財產權之后,即便沒有感情,又遭夫或夫家虐待,仍不愿意離婚。1928年10月,《大公報》載一花邊新聞,反映了在生計艱難情況下底層夫妻處置其關系的首要考慮。該新聞講:賣菜男劉某與女高某結婚,婚后高又與男姚某有染,二人的奸情被劉當場發現,劉把二人送到警署,再轉送檢廳,法院判決高和姚各有期徒刑四個月。劉向民庭提出離婚,稱花了大洋160余元才娶得高,所以請“判給小人點錢”;高則稱自己8歲就說給了劉,19歲過門,現年26歲,奸情的事是誣陷,是夫家“七八輩皆靠人吃飯,常受虐待,逼我做此等行為”,又稱自己在夫家如何辛苦等等;推事問高,是否愿意離婚,高卻“愿意與他回家過日子”[21]。奇怪的是,高一面稱自己在夫家如何受虐待、辛勞,被逼出賣身體,一面卻不愿離異。究其原因,無非二種:或是離婚后生活無所依附,或是同意離婚則既承認奸情又壞了名聲。1940年,重慶黃清繩要求與妻子劉承英離婚,黃訴劉:“不安于室,罔知婦道”,“訴請判離婚”;劉一邊辯訴如何受到丈夫虐待打罵,一邊堅稱寧可出家也不離婚,稱丈夫是因她嫁妝不豐,所以不喜歡,她又發現了黃與佃戶朱二嫂關系曖昧,于是常遭黃的毒打,黃還想毒死她,“此刻我若回家,性命危險,離婚我也不愿,情愿出家上廟,日后原告回心轉意,再可同居云云”⑨。雙方陳述反映出感情似已決絕,妻子更稱丈夫曾給她下毒、回家性命不保,她原本應當積極回應丈夫離異請求,但她卻不愿離婚而只求別居。筆者分析其矛盾來源有二:一是她為了博得法庭同情,無中生有,危言聳聽,說丈夫曾對她下毒,原本沒有下毒,當然無需離婚;二是她若離婚就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而別居卻有生活保障。不管出于哪種考慮,生活有保障是其最終目的。1941年,雅安的鄭況普請求與妻子鄭朱氏離婚,鄭朱氏同上案劉承英的表達類似。鄭稱:鄭朱氏性情乖張,偷家里的東西,隨時回娘家,因此訴請離婚;鄭朱氏聲明,鄭況普“隨時打我”,每次回娘家,均系原告請人送回去的,并未偷竊家中東西,“不愿離婚,請駁回原告之訴”⑩。鄭況普不否認對妻子大打出手,鄭朱氏寧愿常受皮肉之苦也不愿離異,證明她有更重要、更基本的利益需要保護。卷中未提及孩子,排除她為保護孩子而寧愿自己受苦的心理,只有基本生存條件在婚姻狀態中的維持才能迫使她做出不離婚的選擇。1949年,重慶葉辜氏告葉樹山、葉品山、王陳氏侵占重婚案中,葉辜氏一再表示受到虐待,但又要求“返還產業,救濟生活,同居為甚”。從各案分析,她們選擇不離婚,主要是生存壓力,受虐待打罵固然痛苦,但若選擇離婚,獲得了另嫁自由,生存則可能面臨危機,兩害相權,為了生存,她們寧可犧牲離婚重獲自由的權利。
顧及生存,婦女們的另一種離婚訴求就是多要求財產。1929年,天津朱女士請求婦女協會幫助離婚時,提出的理由是丈夫寵愛前妻所生之女,虐待與自己所生之女,要求丈夫給離婚贍養費2000元;其夫稱朱女士因沒有滿足她想像的生活條件而離婚,只能給予200元,因為自己月收入才100元;婦協商量朱女士退讓,提出:“如男方能力充足,則深盼能盡量予以經濟上的援助”,朱女士則不允[22]。婦協本是維護婦女權益的機構,一般站在婦女立場維權,連肩負維護婦女權利的婦協都要求朱女士退讓,可見朱女士的要求的確超出丈夫承受能力。天津男鄭某與女蔣某結婚一年后,蔣稱丈夫無性功能,不能生育,將來老年無望,“且彼家亦非富戶,而自己亦難以忍受”,向法院請求離婚[23]。言外之意是,如果是富戶,或可另當別論,也許就不訴求離婚。這暴露出該女子離婚動機之一還是因為丈夫家財產少。
這種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從最高法院的判例要旨可得出肯定的答案。1930年,《民法》第1057條對離婚的贍養費已有規定:“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于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予相當之贍養費。”[8]931934年2、8月,最高法院兩例民事判例要旨進一步解釋了贍養費的給付條件及標準。其中,2月判例要旨曰:“民法親屬編第1057條規定,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于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予相當之贍養費等語,是因判決離婚陷于生活困難者,必其自己于離婚無過失,始可對于他方請求給予贍養費。”[24]17實施中,此要旨多是救濟在離婚中經濟相對弱勢的婦女。因為一般而言,多數婚姻是丈夫負責供養家庭,妻子離婚后更可能生活困窘,“他方”多指丈夫。8月判例要旨曰:“關于贍養費之給付標準,先應審究贍養權利人生活上之需要狀況,然后就其需要之數額審究贍養義務人之有無此能力以為裁斷。”[25]13意在平衡贍養權利人和義務人的權利義務,即丈夫縱然應給贍養費,也應以贍養權利人的生活需要和贍養義務人的能力兩項條件為限;而贍養權利人申訴權利時不能獅子大開口,漫無邊際,超越權限。最高法院做出的扶養上訴判決中也明確提到:“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倘負扶養義務者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時,應免除其義務。”[26]23最高法院諸多判例要旨和判決,說明此時離婚案中權利人提出超越義務人能力的訴求不少,最高法院不得不統一訓示,以糾正這一偏向。
不過,糾偏也不容易,雖最高法院屢發訓令,時至20世紀40年代這一現象仍然存在。有些訴求離婚的妻子,不僅要求行將離婚的丈夫扶養一時,還要求他扶養終身。1942年,四川省高院民事第二審判決的樊文貞訴周宗廉一案即是一例。1934年,什邡縣樊文貞訴稱丈夫周宗廉虐待她,多次對她實施暴力,要求離異,并要求周宗廉給她終身撫養費1400元;什邡縣政府判決離異,判決周給樊生活費300元;原、被告均不服,上訴至四川省高院,四川省高院駁回上訴稱:“本院查夫婦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依照同法第1056條,只能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并無請求終身撫養之權。……以被上訴人之身份而論,已足以填補其所受損害,何能借此請求終身撫養費用。”[27]專載,48-49無獨有偶,40年代末,四川新繁縣一離婚案中女方也提出扶養終身要求。呂龍氏以呂文祥侮辱人格、斷絕生活、暴行虐待為由提出離婚請求:“由被告給付我撫養生活費,白米三十石為終身生活費,被告實有田產及水田幾畝、房屋幾間,力能負擔承受。”此兩案有一共性頗費思量。首先,女方憑什么要求終身扶養費,此要求貌似強硬;其次,1400元或三十石米就夠終身扶養嗎?這又顯得很無知。她們起訴離婚最終想得到什么?筆者推測,貌似強硬的訴求無非是盡量多得些財產而已。
底層婦女對婚姻財產權的追求大于對自由權的追求,是求生存的本性使然。當時已有人注意及此。一篇《何時能解放》的文章寫到:“在現在過渡時期中,女子經濟不能獨立,離婚后茍于生活已發生問題,其所感苦痛或較不離婚為更甚。”[29]所以,即便離婚,也一定要在財產上留有后路,主觀上不全是追求婚姻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觀念多是被附加的,多是位居高位的政、學、女界用底層婦女爭取生存的事實來詮釋自己想象中的自由、平等、解放等含義。很多時候,兩者風馬牛不相及。
最初,筆者以為,都市中的知識女性在婚姻自由大潮中唯一的追求就是自由。仔細解讀個案,才發現并非“唯一”。前述《大公報》的統計和批評可為一證,她們的離婚訴求也可為證。1927年3月21日,《申報》載有一則消息:一對男女同居幾月后定立婚約,婚約顯得相當平等,男女均享有權利、負有義務;次年,男子未及時回家,該女子即把男子告上法庭,要求男子賠償5萬兩白銀;最終,該案以“違背善良風俗”而被駁回[30]。該女提出的5萬兩白銀絕非小數,比較北洋時期司法官官俸即可看出5萬兩白銀的份量。北洋時期司法官最低薪俸為月薪100元,高的可達到600元[31]200-202。雖案中女子索賠銀的單位是“兩”,司法官月俸單位是“元”,兩者不等同,但以后者做參考仍可說明女子對離婚財產要求太多。1928—1929年間,天津王世芳與張懷廣離婚案審理中,案中女主角對財產的強勢要求也非常明顯。王世芳于1925年與張懷廣結婚,1928年王世芳以虐待和夫妻間沒有愛情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王之理由非常正當——追求愛情,法院認為:“夫婦間既無愛情,自不能維持家庭平和,根據國民政府第二次婦女大會議決案,離婚以自由為原則,再據大理院判例,離婚無須條件。”該案審理時,民法尚未出臺,法官們適用政策、法令、司法解釋而判決離婚,王世芳爭取婚姻自由權的意愿得以滿足。但是,離婚過程卻窒礙叢生,窒礙來自王自己的財產訴求。王提出的贍養費是20萬,后來又要求張家每月給生活費500元,最終法庭判決每月只給200元,距王的訴求甚遠[32-36]。王世芳的言行表明,她知道依法保護人身權利而提起訴訟,但對贍養費的多少則沒有依法律規定。她離婚時,1930年《民法》尚未頒布,1925年完成的《民國民律草案》已由司法部通令各級法院作為條例適用,在實踐中指導民事司法審判。這部草案關于贍養費的基本精神被1930年的《民法》繼承,總的意思是,無責任者有請求責任人給付撫養費的權利,給付的多少是“相當”。法條未解釋“相當”的含義,從前后文理解應是相當于生計、生活需要,并以義務人的能力為限。該案中,王雖聲稱:“一造應給另一造以生計程度相當之賠償和撫慰之義務”,但提出的費用中則包含出洋費、雇傭仆人費、中英文家庭教師費等,明顯超過了生計、生活所需,超越了法律規定她應得的部分。王按自己的需求片面援用法律,反映出其想在離婚中多得財產的用意。此案在當時較為著名,案件延續一年有余,原、被告均為富家子女,被告張懷廣系原山東督軍張懷芝之弟,王世芳也出身富家[35]。宣判時,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婦女協會出席旁聽,媒體自始至終追蹤報道,眾人討論不休,可見其有一定影響力。
這里筆者需說明的是,大多數都市知識女性看重的是婚姻自由權,但不排除部分人同時看重財產權,她們既要熊掌又要魚,各種媒體從正反面都有報道。二者兼有,本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只不過這種層次女性的財產訴求被爭自由的說辭遮蔽,打著婚姻自由的招牌另有所圖。當然,這僅是婚姻自由大潮中的支流、潛流,不影響滾滾向前的主流。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這股被忽略的支流和潛流在合適的環境中可能匯聚成潮,如果不加以引導,將影響婦女良善婚姻觀念的建立。
三 再醮還是留夫家:寡婦的再婚權益與法律保護局限
民國以來,婦女界、學界、法律界對貞節烈婦觀念是口誅筆伐,胡適斥之為“全無心肝”,認為“貞操問題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37]50420世紀30年代初,《民法》讓寡婦再婚有了法律保護。該法第二章規定了婚姻自由若干條款,從婚約、結婚到離婚均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只規定未滿法定年限的未成年人的訂婚、結婚、離婚得由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所謂的“當事人”,包含具備結婚條件的寡婦在內。似乎思想和法律上都為寡婦再婚鋪平了道路。但是,在這條看似敞開的道路上,諸多寡婦卻不愿邁出再婚的步伐。原因為何?
現實中,輿論和法律對寡婦再婚看法并不一致。胡長清在《婚姻習慣之研究》中稱:“孀婦再嫁,原為法所不禁,但在各省習慣,對于孀婦再嫁,則極鄙視。”[38]6法律本來就不禁止寡婦再婚,寡婦不愿再婚顧及的主要是輿論和其它更實際的因素。民國以降,輿論放開,但輿論影響的群體、地域、時間和程度有限,不是所有寡婦都能領會。再則,法律保護的寡婦再婚權是在婚姻自由原則下給予寡婦的權利,寡婦再婚與否取決于她本人的意志,而有些人卻利用普遍認知中的寡婦可以再婚來催促、逼使不愿再婚的寡婦再嫁。究其實,還是違反了婚姻自由原則,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
1929年1月18日,《大公報》載天津某婦女到婦女協會尋求幫助的消息稱:婆母逼她改嫁以便得到錢財,她除了表示改嫁有失貞操、要守節外,沒有別的理由對付婆母的強求,但婦協不支持她的貞操觀,輿論也認為她受了舊禮教熏染,結果她內心的財產要求難以言說,財產權得不到保護[39]。1946年,四川名山縣一樁案子也顯示出寡婦面對夫家覬覦其財產的無奈。名山縣高煥卿有田產上百畝,但行為不軌;為了保住家庭財產,高煥卿的妻子高雄氏趁他在外,在族長主持下,把田產平均分給了3個兒子、2個女兒,每人得30石田產;高煥卿回家后,否定了田產分配;當高闕氏的丈夫,即高煥卿的大兒子死后,高煥卿以年輕女人帶著孩子不宜單獨生活為由,要求高闕氏回家共居,交回30石田產;高闕氏不同意,表示終身不嫁,用心撫養兒子;高煥卿不允,高闕氏無奈提起訴訟,司法處做出和解結論,高煥卿每月給高闕氏母子三人食米3斗、零用錢10000元,另覓房屋給原告居住,高闕氏原分得的田產交還高煥卿保管收益,高煥卿保管時不得把田產抵押或當賣。這一和解最終違背了高闕氏初衷,她每月雖有米、錢,卻沒有自己掌控田產那樣自主,喪失對田產的自主支配權,增加了其所有權的不確定性。從1946年江北縣李段氏要求李國禎給付生活費提起訴訟一案,也可看出不再婚而留夫家的寡婦在保障財產權上的艱難。李段氏是李家的媳婦,其丈夫李美成死后沒有改嫁,她要求分得一部分家產,而李家其他人不僅稱“我弟兄四人,姊妹三人,母親尚在,□遺產100石為我弟兄姊妹及母親8人所共有”,以田業難以分配為由,拖延應給李段氏的遺產和生活費,李段氏不得不要求法院強制執行生活費。上述案件反映出并非所有寡婦都想再婚,寡婦不再婚而留在夫家,其財產占有情況受諸多因素影響。
寡婦們能否繼承遺產,如何繼承遺產,將來憑借什么生活,左右著她們再婚的意愿,而不僅僅是貞操觀念使然。但是,民國以來,婚姻自由思潮的奔流,加之標榜堅持婚姻自由的民法的施行,寡婦的婚姻自由權常被偏狹地理解為再婚自由,其不愿結婚的意思并沒有受到關注,對她們不愿再婚的原因也少有深究,學界、女界即大力批判鞭撻貞節烈婦觀念,鼓勵支持寡婦再婚。此類占壓倒優勢的言說,把寡婦不愿再婚的原因一味歸結為節婦烈女遵守封建婦道,忽視了現實的經濟財產因素,甚至代寡婦們立言,似乎所有寡婦都希望再婚,再婚是她們的最愛,這未免簡單化地對待寡婦愿否再婚的問題。的確,寡婦再婚必須沖破傳統觀念,但是,她們不愿再婚,也不全是恪守舊道德,還有現實的生存考量,除觸及靈魂外,還要觸及其生存利益,這更令很多寡婦難以決斷。再婚后,亡夫的財產能否繼承、如何繼承、繼承多少,是她們更為關注的問題。當她們得到滿意的答案,再婚才會被提上考慮日程。在批判貞節烈女的聲浪中,寡婦的家庭財產權常在其夫家的占有私欲中以支持再婚的高調而被侵害。
民國法律給予寡婦再婚權上有兩個矛盾:一是道德和法律精神的背離,二是大法精神和司法解釋的沖突。傳統的婚姻倫理觀褒獎婦女從一而終,好女不嫁二夫。清代對節婦的旌表制度更是登峰造極,不僅有倫理道德的軟約束,還有貞節烈婦可變通繼承亡夫遺產的剛性法律約束,以保障她們的守志生活。傳統法律對寡婦繼承的規定是:“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40]601911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第1467條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得承其夫應繼之分,為繼承人。”[7]188道德和法律精神是一致的,都保護了留在夫家寡婦的繼承權利。只要寡婦留在夫家,其財產若被夫家、族人侵吞,侵占者不僅不合道也不合法,寡婦可理直氣壯地訴請法律保護。民初則是道德和法律精神的背離,學界、女界一味批判貞節烈婦,鼓勵寡婦再婚,而法律仍承襲保護守志婦女的精神。如1925年《民國民律草案》第1338條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在立繼前,得代應繼承人,承其夫分,管理財產。”[7]382這些法條經最高司法當局通令各級法院作為條例適用。幾部法律都明定婦女在守志狀態下有遺產繼承權或遺產管理權,易言之,不守志就沒有這兩項權利。寡婦們是依從宣傳還是依從判例呢?恐怕底層婦女更傾向于服從后者。不允寡婦再婚,從某個角度說,當然是摧殘、不人道,是“極難、極苦”,使婦女“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41]129,130,但從財產而言,卻給予守志寡婦以生活保障。
論者或稱,民國法律在給予寡婦婚姻自由權的同時,還給了寡婦繼承亡夫遺產的權利,寡婦不會因確保繼承亡夫遺產而失去再婚權。的確,1930年《民法》第1138條把配偶作為當然繼承人,規定:“法定繼承人除配偶外”,還有直系血親輩親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42]203。這說明寡婦無論守節與否,對丈夫遺產均有法定繼承權,法律沒有設定任何條件。理論上,因婚姻法實行婚姻自由原則和繼承法給予寡婦遺產繼承權利,寡婦可以在享有遺產繼承權利的同時享有再婚權,再婚不影響繼承亡夫遺產;但實踐中卻出現始料未及的情況。若干案例證明,夫家人、族人逼迫寡婦改嫁以便分享寡婦應得財產之事例,屢有發生;寡婦利用守節來維護自己的財產權利,不僅被斥為“封建婦道”,更沒有從前那樣具有國家保護的力量。黃宗智就指出:“民國寡婦雖然有一定新權利,當她留在夫家時,她的地位其實比清代更弱”,寡婦的財產權更難以得到保障[4]180。
在司法實踐中,另一困惑是基于理想制定的大法法條和指導現實的司法解釋有沖突。1931年,最高法院一則民事裁判要旨稱:“守志之婦所酌提之贍養財產只可供守志之婦贍養之用,而其所有權仍應屬諸其子,嗣守志之婦亡故,當然無財產繼承之可言。”[43]同年,司法部訓令稱:“孀婦招夫入贅,即非守志之婦,雖因扶子招夫,仍不得于子亡后承受前夫之分或為前夫及前夫之子擇繼。”[44]341933年,最高法院在一例“確認監護權即繼承遺產上訴案”判決中仍稱:“依民法繼承編施行前之法例,婦人夫亡無子者合行夫分,系指守志之婦而言。”該案的上訴人是張李氏,被上訴人是張發,張李氏是張發的弟媳,其夫張喜已去世,兩人為張李氏是否應繼承張喜的遺產發生訴訟,云南高院二審判決張李氏不能繼承,張李氏不服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理由是:“依照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應依當時之法例為裁判。按當時法例,婦人夫亡無子者合承夫分,系指守志之婦而言,本件上訴人于其夫張喜死亡后,業已招夫并未守志,則關于其夫張喜之遺產上訴人自無過問之權。”[45]釋讀兩則訓令和判決中的“守志”寡婦提取的贍養財產不能被繼承,孀婦“扶子招夫”后不得承受前夫之分等意思,可以判斷,司法解釋和訓令保護守志寡婦的財產權,與《民法》的婚姻自由、夫妻財產權平等、遺產繼承權的規定不一致。盡管幾則判例要旨都指出案中繼承發生在《民法》施行以前,但判例的做出則是在《民法》施行以后,對寡婦決定再婚的影響不可小覷。寡婦因慮及事關生存的丈夫遺產繼承受阻,自然不能把再婚權放在首位。就這點而言,民國時期的思想宣傳、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并不在同一個方向對寡婦再婚施加影響。
誠然,民國不提倡婦女守節,不給守節婦女以特殊照顧的立法,是保護寡婦再婚權利。但審判實踐卻表明,孤立地強調這點,沒有配套其它規定,輕視了再婚婦女的經濟、子女等條件,忽略了社會文化傳統,立法意圖的實現必定受阻。偏狹地把寡婦的婚姻自由理解為她們的再婚自由,在她們不愿再婚情況下,反而是對民法意思自由、自治等基本原則的違背,是另一形式的婚姻不自由,甚至危及寡婦的生存權利。民國婚姻法保護寡婦婚姻的窘境,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在1935年全國司法會議上已有評價:“依舊律,守志之婦雖不得繼承其夫家財產,但得合承夫分而歸其將來嗣子所有,依現行民法,若夫無子而先于父母身故時,其妻既不能為夫收養嗣子,而子婦又無繼承翁姑遺產之明文,除得受撫養外殆無所獲,殊不公平。”[46]154-159某些寡婦的生路反較以前狹窄。這當然非立法和司法者的主觀意愿,而是在新舊糾纏的觀念轉變中多方博弈的結果。
四 影響民國婦女婚姻變革中家庭財產觀念構建的若干因素
上述從婦女婚姻權利義務觀是否平衡、婚姻訟案中爭自由和爭財產的權重、寡婦愿否再婚幾方面討論了婦女的家庭財產認知及引發的問題。為什么幾種情況下婦女們都特別在意爭取財產?我認為下述幾種因素似有影響。
第一,婦女家庭財產權缺失帶來的生存憂慮感,使她們必須重財產權。
存在決定意識,婦女的生存狀態及其在家庭中不能支配財產的現實,決定了她們在婚姻訟案中必然把財產放在首位考慮,即“女子經濟不能獨立”是婦女們在婚姻訟案中不得不特別看重財產的重要原因[20]。所謂“經濟不獨立”,一是指婦女在家庭中雖勞作辛苦,卻沒有財產所有權,二是指婦女不能獨立謀生。
傳統社會中,很多婦女辛勤勞作,對家庭財產貢獻頗多。沈雁冰曾分析道:“凡鄉村間的婦女是能夠自食其力的,伊們的謀生不亞于男子”,“大凡鄉村婦女在職業上,或謀生方法上,是和男子處同等機會的”,不過,“雖然能自食其力,但是不能有自己的錢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自由處分用伊自己勞動換來的錢”[47]2-3。據社會學界、婦女界很多調查證明:城鎮婦女勞動艱辛,其勞動是包括丈夫在內的家人的生活來源,但是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下,在“三從四德”的家庭倫理道德中,婦女們辛勤勞作后,在家庭中仍沒有財產所有權,一旦婚姻出現危機,到了離婚地步,她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生活來源斷絕。此外,還有些婦女,沒有獨自謀生的能力,專賴丈夫為生,一旦離婚,頓失所依。無論哪種,都迫使她們不得不優先考慮財產。
某些有能力、有職業的婦女離婚時在贍養費上的爽快,反面印證了這一問題。不過,因婦女就業少,例子也較少。1928年12月16日,《大公報》載天津彭女士要求離婚,彭29歲,國民黨員,因丈夫納妾而要求天津市婦女協會幫助她與丈夫離異,并幫忙謀份工作;丈夫李某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商科,任洋行經紀,李稱后悔納妾,同意按月給彭女士生活費30元,但不離婚;彭堅持離異,她最初要求丈夫給1000元贍養費,先付一半,其夫同意離婚后,卻只承認先給100元,彭未糾纏,達成離婚協議[48-49]。1929年1月17日,《大公報》登載天津結婚10年的張某與妻王某離婚,本是張到法院訴求離婚,離婚時,張語不成聲,但王卻“神情昂然自得”[50]。20世紀30年代,北平地方法院處理的一樁北大教授梁宗岱離婚案中,其妻何瑞瓊也是有理有節地提出生活費要求。梁、何結婚十余年,梁歸國后到北大任教,卻未把老家的何氏接到京城,何便起訴離婚,她提出梁月薪400元,故要求月給她生活費150元,最后法院判決月給100元,何欣然同意[51]39-41。上述三位女士之所以沒有漫天要價,原因在于她們都能自食其力,不靠丈夫也能獨立生活。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土地改革后,婦女地位得到實質提升,她們也產生了“有一份田后,咱有說話權了”的認知。當時就有人指出:“女子欲謀徹底的解放,非自己經濟獨立不可。”[52]
第二,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異化制約。
基本生存條件制約了婦女在婚姻中的財產觀念,但不足以解釋那些有生存能力、有一定財產的婦女在離婚中對財產的過分要求。對此現象,我認為還要從中國傳統婚姻家庭觀念和婦女的教育中尋找原因。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男主外,女主內”,是廣為流傳的深入民間的俗語,反映了妻子依賴丈夫的習慣性心理。既曰“習慣”,就不可能在短期內驟然革除,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支配人的行為。那些依賴丈夫財產的婦女,正是因襲嫁漢穿衣吃飯的傳統思維,認為夫養妻是天經地義。探究其內心,或許因她們的無助和柔弱是一種潛在的自我禁抑而非自我解放。不過,她們這時是禁抑于丈夫的財產而不是禁抑于丈夫的人身。1930年,胡漢民便對這一現象尖銳批評道:“現在所謂解放的婦女,常常是脫了此一端的束縛,放縱起來,又鉆到彼一端的束縛里去。”[53]
第三,教育的缺失所致。
教育的缺失也使得婦女多以財產為婚姻合離的準據。正如時人論男女平等時指出:有時“家庭中的不平等,不能盡歸罪于男子方面,一般女子她們不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盡她們自己的責任,……但這也不能怪她們本身,推本求源,皆因沒有受教育”[54]。特別要說明的是,此語中的“教育”,并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化知識教育,還包含法律概念上的權利義務觀衡平教育。民初伊始,在教育、鼓動伸張婦女權利時,基本沒有提及婦女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應履行相應的義務。
第四,激越革命引起權利與義務觀念的建構失衡。
婚姻自由在我國由口號到法律文本、再到司法實踐,一路都伴隨著激越的革命,婚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婚姻革命的對象主要是舊式婚姻,是壓迫婦女的婚姻家庭倫理道德觀念。在封建婚姻關系中,婦女們承載了太多義務而少有權利,婚姻革命當然要以翻身求解放的激情打倒舊式婚姻。革命中,爭取的是權利而非義務,渴求的是翻身而非平等。檢視二三十年代與婦女運動相關的文獻,幾乎全是伸張女子權利的吶喊。如1921年,《長沙女界聯合會成立宣言》宣示要恢復女子人權,與家庭相關的權利包含“財產均分權”和“婚姻自決權”[47];同年,《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與家庭相關的權利要求是“在男女權利平等的理由上,我們要求在私有財產制度未廢以前,女子有受父或夫之遺產權”[47];次年,在《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及章程》中,法律方面是“在民法上,怎樣改革親族法,使女子有和男子同樣的繼承權;怎樣改革婚姻法,廢除納妾制度,規定妻的完全權利和行為能力,并承認女子有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47]。其它個人、團體的文章、講話也一再提及類似意思。這些主張是對千百年來女子受壓迫的革命,也是對現實社會中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反抗。革命的激情,翻身的鼓動,對婦女婚姻權利觀的建構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對義務觀的確立則作用不大。在提及爭取婦女權利時幾乎沒有涉及義務,特別沒有提及家庭義務。就婦女受壓迫的歷史和現實而言,這完全可以理解;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當革命激情平復,回歸日常生活,用法律規范婚姻行為時,權利當然要與義務相對應。法律理性中的義務本該是建構的內容,革命中卻無人顧及,致使權利義務平衡觀念的培育空缺。這或許是離婚案中的婦女動輒就以被遺棄而提出離婚,或提出超過法律限制的財產訴求的一個原因。
激越的革命對于婦女權利義務觀的平衡建構作用不大,也不能如秋風掃落葉般一夜間清除舊觀念,不僅守舊人士、普通百姓抱殘,就是趨新人士骨子里也可能鑲嵌著舊觀念的碎片,舊觀念又循環激發出婦女更強烈的爭權意識。1918年,胡適在《貞操問題》中論及寡婦再嫁,不自覺地流露出矛盾認知。他批駁寡婦守節,主張寡婦再嫁,說在幾種情況下寡婦可以不嫁,夫妻情深,兒女牽掛,年紀已大,“家道殷實,不愁衣食”,如果“家又貧苦,不能度日”,為何不再嫁呢[37]507?稍作解讀,便見其矛盾。胡適潛認知中,再嫁到底是打破舊的貞操觀,還是迫于生計而依賴男方呢?若是后者,豈不就是婦女應依靠男子嗎?即便兩者兼有,胡適也有婦女為穿衣吃飯而嫁漢的意思。在大革命狂飆之后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兩種觀念仍舊對壘。1934年初,青島市府因前總統黎元洪之妾再醮而把她驅除,但把66歲的熊希齡娶33歲的毛彥文贊為佳話,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驅黎之妾是政府所為[55]4-50。時至1934年,政府還用雙重標準衡量男女再婚,可見社會對婦女爭取平等權利的阻礙。
1934年修改《刑法》第239條關于通奸規定時,會場內外的互動也反映出新舊觀念的博弈。起因是現行刑法第256條單科“有夫之婦”與人通奸罪,對有婦之夫的通奸行為則不予處罰,女界認為違背了男女平等原則,要求修改此條。于是,立法會議起草時便將此條文修改為:“有配偶與人通奸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意謂夫妻與人通奸均受刑法處罰。二讀討論,該條竟未獲通過,多數表決刪除此條,定為:“有配偶之男女違背貞操之行為,僅負民事責任,而不受刑法制裁。”再開會時,卻全文翻版現行刑法第256條的規定:“有夫之婦與人通奸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奸者亦同。”僅在刑期上有所減少。這激起了南京婦女的極大不滿而開會抗議:“此種科女子片面義務之法條,實屬壓抑女子,放縱男性,根本背叛總理遺教,違反對內政策第12條,且與訓政時期約法第6條明文抵觸。”[56]31-34要求立法院按照男女平等原則復議。經過多番辯論,該條定為:“有配偶與人通奸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最終定格維護了婦女的權利。為此,婦女們歡呼這是“婦女界力爭刑法第239條勝利”[57]1-2。《法律評論》稱:“三改而后定,慎重其事矣,立法委員之法律思想進步,致有此現象矣。”[58]1女界眼中理所當然之事,立法委員們要“進步”后才能首肯,可見男女平等在還算開明的立法委員和女界認知中的差異。連本當深明男女平等涵義的立法委員都存有男女權利不等的痼疾,可見雖然自民初以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聲浪從未斷絕,但時至30年代,要落實到可具體操作的法律條文仍然阻礙重重。阻力越大,婦女們爭取權利意識便越強烈,越要為爭取權利而抗爭。此時此景,又有誰來提起婦女的權利義務觀應平衡建構呢?
注釋:
①參見:劉昕杰《民國民法中離婚權利的司法實踐》,《北方法學》2010年第3期;徐靜莉《民初司法判解中女性權利變化的總體趨勢——以大理院親屬繼承判解為中心》,《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徐靜莉《“立法”與“司法”的變奏——民初女性權利演變的特性》,《學術論壇》2010年第5期;徐靜莉《男女平等原則在近代中國民法中的確立》,《婦女研究論叢》2012年第4期;杜清娥《女性·婚姻與革命:華北革命根據地女性婚姻與兩性關系》,山西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等。
②天津市檔案館:檔號401206800-J0044-2-000413。
③天津市檔案館:檔號401206800-J0044-2-018812。
④⑤天津市檔案館:檔號401206800-J0044-2-049375。
⑥《被告鐘翠華申請同居上訴事件案》,四川德陽市檔案館:全宗號5,目錄號2,案卷號716。
⑦司法行政部編《司法統計(1935—1936年)》,四川省檔案館:歷史資料5/19/1。
⑧《晉冀豫區婦總會一年來婦女工作總結報告(1941年8月)》,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1-7-4-6。
⑨《黃清繩與劉承英離婚案》,重慶市渝北區檔案館:全宗號民5,卷號7924。
⑩《鄭況普與鄭朱氏離婚案》,四川雅安市檔案館:全宗號3,目錄號1,案卷號353。
[1]天津最近三年離婚案件之統計[N].大公報,1929-02-10~12(9).
[2]沈登杰.中國離婚問題之研究[J].東方雜志,1935,32(13).
[3]民法上親屬繼承兩編中家族制度規定之意義[M]//胡漢民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4]黃宗智.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5]黃宗智.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潘大禮.民國三四十年代湖北婚姻沖突案例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1.
[7]大清民律草案 民國民律草案[G].楊立新點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六法全書[G]//民國叢書:第三編(28).上海:上海書店,1948.
[9]最高法院民事判例[J].法律評論,1934,12(8).
[10]丈夫跑了沒人管 她為穿衣吃飯欠債千元[N].大公報,1929-02-26(9).
[11]司法界極力進行改革[J].法律評論,1929,6(38).
[12]天津婦協救濟科一年的工作[N].大公報,1929-09-12(13).
[13]杜清娥.女性·婚姻與革命:華北革命根據地女性婚姻與兩性關系[D].太原:山西大學,2016.
[14]新法律與婚姻問題[N].大公報,1929-08-01(13).
[15]最高法院判例要旨[J].法律評論,1934,11(33).
[16]最高法院判例要旨[J].法律評論,1936,13(51).
[17]彭時.論離婚制度與我國立法應采之方針[J].法律評論,1929,6(50).
[18]婚姻調查的答案[N].大公報,1928-03-01&08(10).
[19]現代女兒談戀愛 條件離不了洋錢[N].新新新聞,1933-09-25(9).
[20]經濟不能自立是女子的奇恥大辱[N].大公報,1929-06-20(13).
[21]丈夫深夜歸來 觀破家庭秘密[N].大公報,1928-10-04(6).
[22]感情不恰 要求離婚 丈夫同意 為免痛苦[N].大公報,1929-07-08(9).
[23]不良婚姻的結果 她何苦要枉負虛名[N].大公報,1928-10-05(6).
[24]最高法院民事判例要旨[J].法律評論,1935,12(20).
[25]最高法院民事判例要旨[J].法律評論,1935,12(19).
[26]最高法院訓令[J].四川高等法院公報,1935,(1).
[27]民事判決[J].四川高等法院公報,1935,(1).
[28]里贊.“大波”中的“微瀾”——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離婚立法在四川省新繁縣的實踐[J].民間法輯刊,2010-09-30.
[29]何時能解放[N].大公報,1929-01-31(9).
[30]婦人指控違背婚約案之判決書[N].申報,1927-03-21(11).
[31]司法官官等條例[J].東方雜志,1918,15(8).
[32]王世芳離婚案判決[N].大公報,1929-05-28(9).
[33]王世芳離婚案判決[N].大公報,1929-04-05&06(12).
[34]離婚以自由為原則[N].大公報,1929-05-25(9).
[35]生活費20萬元[N].大公報,1929-01-20(9).
[36]王世芳要求生活費案[N].大公報,1929-04-14(9).
[37]胡適.貞操問題[C]//歐陽哲生.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8]胡長清.婚姻習慣之研究[J].法律評論,1930,7(17,18).
[39]她受了舊禮教的熏染[N].大公報,1929-01-18(10).
[40]史尚寬.繼承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41]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2]郭衛.六法判解理由總集[G].上海:法學書局,1935.
[43]守志之婦的財產繼承[J].四川高等法院公報,1935,(3,4).
[44]司法部訓令[J].法律評論,1931,8(18).
[45]裁判要旨[J].司法公報,1934,(6).
[46]全國司法會議提案摘要[J].法學雜志,1935,8(5).
[47]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8]不愿再處傀儡家庭[N].大公報,1928-12-20(6).
[49]脫離了無邊苦海[N].大公報,1928-12-22(6).
[50]家庭之裂痕十年夫婦一旦離婚抹殺了以前的恩情[N].大公報,1929-01-17(9).
[51]民事判決[J].法律評論,1934,11(12).
[52]從婦女解放說到經濟獨立再說到貞操問題[N].大公報,1927-07-19(10).
[53]怎樣使全國婦女能行使女權[N].大公報,1930-07-08(3).
[54]什么是男女真正的平等[N].大公報,1928-05-24(9).
[55]時論集珍、節婦、再婚婦[J].婦女共鳴,1935,4(2).
[56]京婦女界反對刑草通奸罪條文[J].法律評論,1934,12(2).
[57]婦女界力爭刑法第239條的勝利[J].婦女共鳴,1934,3(12).
[58]論說[J].法律評論,193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