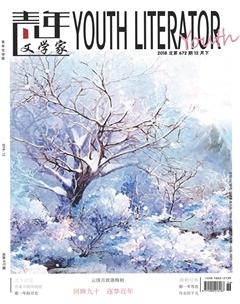何為君子(外一篇)
李浦楠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強、自信的民族,它歷經五千年的世事變幻,云波詭譎,千古江山,人才輩出。即便往日滄海已然變為了桑田,無數杰出人才流逝于時間的長河中,君子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使中華民族始終散發著古老卻蓬勃、清淡而耀眼的光芒。
“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做,敢當。”魯迅曾指出社會是一座高塔,所有人都沉睡于此,但當第一縷陽光從高窗照耀進來的時候,君子應是塔中率先蘇醒過來的人,他們敢于直面刺眼的陽光,明晰內心中的光明,敢于思考如何逃脫高塔,敢于叫醒沉睡的人,敢于帶領人們走出陰暗的高塔。在當今網絡發達,信息鋪天蓋地的時代,各式各樣的新聞在網絡上爆炸開來,引得人們轉發評論、圍觀稱奇。龐大的信息量免不了混入謠言與虛假傳聞,此時的君子,應是敢于指出不實的信息,舉報傳播惡意與黑暗的人,揪出這些躲藏在網絡背后的犯罪分子,然后敢想敢說,將正確、真實的信息公之于眾,成為社會光明的傳遞者。
“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君子懂得認清自己,懂得保持真我,君子們從不刻意點染、夸耀自己,如同那些追名逐利、愛慕虛榮之人一樣費盡心思展現自己以求取目光博得人們關注。陋室之中的劉禹錫就認為“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樣的環境簡陋并不會使自己自卑,反而因為身為君子的劉禹錫認清了自己的品德高尚而感到樂觀自信。
“受光于庭戶見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只有在個人奮發努力的基礎上,將眼光放長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理想才可能實現。中國秉承大國風范,盡心盡力地援助亞非拉地區,幫助他們建設基礎設施,完善產業結構,正是因為君子們不僅是為了向貧窮人口伸出援手,更是為了使世界發展更穩定、更平衡,是眼光長遠的一種表現。
君子就是這樣一群隱藏于普通人之中,卻做著、考慮著不平凡的事。他們默默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不被世俗所污染,匯集在一起,共同使社會褪去黑暗,迎接黎明的到來。
“老腔”何以令人震撼
在猴年春晚的舞臺上,我聽到了一聲從未聽到過的曲子——那黃土地黑皮膚鑼鼓喧天,吼聲震撼了八百里山川河岳的老腔!我愿意把它令人震撼的力量歸結為一個詞——接地氣。
“老腔”不是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它并不適合淺斟吟唱。因為,在大西北粗礪的風沙之中,陽春白雪扎不下根來,淺斟吟唱傳不到遠處,它吼出的是底層草根兒們的心中吶喊,它體現的是農民原生態的艱難歲月。
這來自關中大地深處的一聲嘹亮的老腔,不僅僅沖擊了人們的視覺聽覺,還讓人找回了千年之前對于大地那原始的眷戀。因為“老腔”是誕生于民間,傳承于人們內心的藝術。
《詩經》的國風,是從周南、召南等十五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它之所以在千年之后仍能觸動著我們的心弦,是因為它是民歌藝術對于百姓真實生活切實體現,是貼合實際的,是可以使無數靈魂與之共鳴的。
“老腔”之所以有著令人震撼的力量,是因為它的真實、它的本色、它的溫情,更因為它深深扎根于這片熱土的執著。
陳道明曾在一次電視節目上發飆,幾十個來自山西稷山的農村孩子表演了一出高臺花鼓,滿堂喝彩,但卻被幾位自認為藝術修養極高的評委貶低的一無是處。陳道明怒斥:你們對傳統文化毫無理解,居然就直接否定了這個節目。你們可能讀過不少書,有很高的知識水平,但卻對中國最質樸的傳統文化和農耕文明知之甚少、理解不了。“震撼”并不在于文化程度有多高,無所謂見識有多少,而在于能否放棄那種矯揉造作的姿態,以一顆赤誠之心感受那種發自內心的沖動與虔誠。
老腔、秦腔、花鼓等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們,骨子里就是一種這樣動人的虔誠。只是有的人誤解了這樣的虔誠,甚至蔑視地稱它為“愚昧”。因此在老腔火了以后,雖然愛著老腔的人越來越多,但真正愿意學習老腔的人少之又少,肯踏實傳承這項技藝的更是寥寥無幾。
民間技藝的傳承不是口頭過場,每一位優秀的傳統藝人精湛表演的背后定離不開汗水與堅守,絕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高度,難道這民間藝術火爆如老腔,也還是難逃式微之勢?
在當今快速發展的時代,民間藝術等待著人們去挖掘其中的魅力,更需要被創新,使千百年后的人們同樣感到震撼與靈魂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