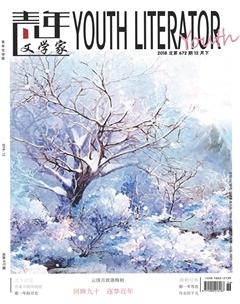文以載道的功夫在文外
佘飛鴻
每逢春末夏初,我系大二漢語言文學與英語專業學子,按照教學籌劃,皆走出校門,以修采風實踐課。《三人行》編輯組薈萃其精華,結成“三人行”專版文集,亦為活動之成果。
甚是慚愧,先前雖有接觸《三人行》,但多數未曾坐定靜心閱覽,而手中此集確有細讀:一為崗位調整職責之使然;二為曾帶隊赴桂林采風。
輕拂油墨香,一幀幀秀山麗水之畫卷穿梭眼簾,一幅幅風土人情之光影定格腦際:無論漓江象鼻山倒影入波鱗水光中之彎曲變形,還是六朝古都夫子廟前江南貢院奮筆疾書疲憊身影之遐想;抑或天際海風挾至鹽粒子將鼓浪嶼潮濕空氣料理為淺淡咸味,以至高山平湖三峽兩岸遁尋遠逝猿聲唯余草木繁茂之惆悵,甚至連遠郊近野攜山水植被均浸潤于厚重歷史文化底蘊之西安古城……皆可從這一行行文字里,或暗或明窺見作者慧眼捕獲之景象,俱能從那一篇篇思緒中,亦淺亦烈觸摸文者因景生情的感懷。
遣詞造句有講究,布局謀篇多推敲,文筆華而麗,情感細而摯。描山繪水狀聲色,感景抒情寫風光。雖也還難掩青澀,但那純潔的感、那質樸的情、那率真的思,使人陶醉,令人神往!
只是,倘若能在這明艷華麗的霓裳中,即在這般色彩、款式里,若還將布料再打織精美一些,以進一步提升其面料質地,就不僅只高貴典雅,且錦上有花,更花中藏果了。亦如膏湯不僅只味鮮美,更有富足營養,滋補裨益人之“精氣神”,是謂善莫大焉!
文當以載道,文之“道”,指其不僅有思想性和藝術性,更能予人真善美和向上力。故文章不唯推字敲句,布局謀篇,做好文字功夫之雕技,而更應著力內涵其“道”。雕技當以出神,即工技之元本應為文之“道”服務。
文如其人,言為心聲,無論是托物言志,還是借景抒情,皆文為道之體,道為文之神。夫天地大正之“道”,須臾離不開“真善美德”,離不開“良知、正義和愛的陽光”。作文者當有悲天憫人之情懷,當有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之格局,當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宏偉抱負!
“文道”為一種閱歷與修為,一種氣度與品格,更是一種境界與情懷。視野廣博胸襟闊,登高望遠格局大。心中有仁愛,眼中有美善,文中有道骨。在身體埋頭拉車趕路時,精神卻不能不仰望星空,胸懷高山大海。弘揚正能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時俱進,與百姓黎民同呼吸共命運,追夢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范仲淹之《岳陽樓記》,千百年來美岳陽樓勝景之宏文巨篇宛若星河,難憶其數。唯其范氏《岳陽樓記》,因其鑲有“憂樂”思想精神之璀璨明珠,不但未隨歲月淹沒于漫長歷史塵埃中,反而如一束強光投射在時光隧道里愈加熠熠千古生輝。其實,范氏的憂樂情懷亦孕育于更古先哲,如《孟子·梁惠王下》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歷代先賢圣哲,為文之道一脈相通。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走出小我到大我,當從大我到無我;跳離情緒到情感,升華情感言情懷。苦人間苦,樂民所樂,美世上美,又何愁文中無道?道不動人乎!
匆成草就,姑且為序。戊戌年丹桂飄零季於柳城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