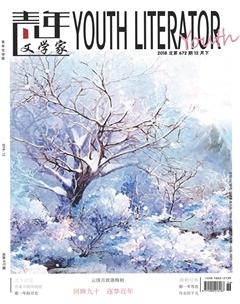論王安憶《長恨歌》中城市與女性的人物關系
摘? 要:上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上海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豐富多樣的人文內涵成為享有“東方巴黎”美稱的現代化大都市。王安憶的《長恨歌》中用獨特的女性視角挖掘女性與城市的關系,解讀王琦瑤傳奇女性的人生同樣就認識了上海。本文將以作品分析為重點,對這部作品中的女性和城市關系進行系統的分析,探尋女性與城市之間所隱含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長恨歌》;王琦瑤;城市景觀;互動關系
作者簡介:呂遜(1992-),女,滿族,貴州黃平人,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2017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02
引言:
王安憶以女性獨特的視角和審美創作了《長恨歌》,創作了滬上淑媛王琦瑤飽滿的人物形象,以細膩入微的觀察賦予上海這座城市鮮活的生命力。通過女主人公一生的愛恨糾葛向世人展現了一幅城市在時光中變遷的畫卷。王琦瑤是“上海弄堂的女兒”,她代表著市民階層,王琦瑤的命運與上海這座城市不可分割,兩者之間也交織著現代社會下女性與城市復雜的互動關系。
一、王琦瑤的“上海故事”
“她用女性做上海的代表,講述一個女人一輩子的故事用王琦瑤的一生來演繹一個城市的歷史,通過王琦瑤命運變換,表現上海這座城市的時代變遷,用王琦瑤的心靈、性格氣質,精神追求映射上海的精神特征。”(張燕,2007)
故事從1946年開始,王琦瑤作為一個平凡的上海市民階層的小女兒,正如同作品中所描寫的:“上海的弄堂里,每個門洞里,都有王琦瑤在讀書,在繡花,在同小姐妹慪氣掉淚……”(王安憶,2003)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從蔣麗莉的家“在背靜的馬路一條寬闊的弄堂”之中走出來,一夜之間成為三小姐的“滬上淑媛”,得到了國民黨要員李主任的青睞,她毫不猶豫的投進李主任的懷抱,甘于淪為物質和浮華的奴隸。直到上海政局變換,她還是牽掛上海,搬進了平安里,體驗人生的愛情。到了1976年,王琦瑤重溫舊夢,回光返照的與老克臘產生一段畸形戀,最后被長腳殺害,落了個“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結局。
王琦瑤的不平凡就在于時代的變遷政局的風云詭譎對她沒有絲毫的影響,她依舊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自得其樂,而這個世界正是與上海這座城市互為表里。 “長恨歌里我寫了一個悲劇 ,其實我要寫的是一個城市的故事,我是直接寫城市的故事,但這個女人是城市的影子。”(南帆,1998)《長恨歌》成就了城市與女人,王琦瑤從輝煌到平淡,落寞再到梅開二度的人生軌跡,與20世紀上海盛衰枯榮的歷史恰好同步。可以說,《長恨歌》中的王琦瑤就是一部城市生活的風情史,一個人的四十年風雨寫活了一座城市,將女性的人生命運與城市的風云變幻交替表達。
二、弄堂、閨閣:王琦瑤的“上海背景”
上海作為市民文化的集聚,王琦瑤的生命呈現即是在此被攤開的,其中,又主要是以弄堂和閨閣來細致展開王琦瑤的命運之維。
(一)弄堂:王琦瑤的“上海故事”之始
一個城市的市民文化的形成,其中居住環境以及生活方式有著重要的意義。弄堂是上海所有建筑中最主要象征性符號,而生活在弄堂之中的主角是最普通的上海人,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就成為了《長恨歌》的故事中心。
《長恨歌》的弄堂是溫情的,從日出時分精致的老虎窗,整齊排列的青瓦,窗臺上的月季,再到窗臺上晾曬的衣衫,還有銹紅色磚墻,甚至是青苔,水泥和石卵鋪蓋的底弄。弄堂之中還有油垢的后窗,浮著爛菜葉。正是這樣的場景,少女時代的王琦瑤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排斥弄堂,向往繁華的世界。弄堂又以包容寬和的姿態毫無保留的接納她。從弄堂中走出去再到歸來,是命運玄妙的輪回。“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王安憶,2003)弄堂不再僅僅是人生活的背景,而是與人心相通,并被作者賦予了生命。
作為上世紀的舊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弄堂生活實際上代表著上海市民文化精神,是上海精神的濃縮。王琦瑤就居住在此,洞悉市民階層世俗生活的各種人情世故。王琦瑤是《長恨歌》的靈魂,她的命運展示著上海日常生活的物質文化。
(二)閨閣,凡俗瑣碎的命運之維
王琦瑤對世界有著按捺不住的野心:“要說她們的心是夠野的,天下都要跑遍似的。”可是這樣的心態有隱含有一份卑微,“卑微是人的內心斗爭永不停止的根源,戰勝還是屈服,這是超越虛無的關鍵,可它是那樣的根深蒂固,和孤獨、焦慮等等緊緊地籠罩著人類,讓人生最終成為一幕無法超越卑微的悲劇。”(張公善,2009)這份卑微在閨閣之中就已形成,貫穿王琦瑤的整個人生。閨閣生活教會她察言觀色,冷靜的處世態度,審時度勢、以退為進的做人姿態。
閨閣生活是低俗和市儈的表現,王琦瑤從閨閣之中走過人生寒暑,閨閣中的王琦瑤到成為母親的王琦瑤,除了沒有實現的上海舊夢,她多了一份溫情,至真至純的細膩。閨閣也讓王琦瑤念念不忘:“閨閣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間,從嫩走到熟,卻是生生滅滅,永遠不息,一代換一代的。閨閣還是上海弄堂的幻覺,云開日出便灰飛煙散,卻也是一幕接一幕,永無止境。”(王安憶,2003)
《長恨歌》把王琦瑤與閨閣相互并置,呈現了閨閣的市民氣息,也讓王琦瑤這樣的“上海女性”有了性格的成長基礎。“弄堂、閨閣 、鴿子,這些尋常的生活物象,它們是王琦瑤的影子,王琦瑤是它們的影子,無論是事物本身還是人物的性格和生活處境都因作家這種含蓄蘊藉的追求而獲得了審美的深度。”(于哲霏,2011)
“王琦瑤和上海就像一個人的正面和背影,王琦瑤因上海而豐滿,上海因王琦瑤而靈秀。王安憶以自己對上海的理解和領悟,賦予了王琦瑤這個人物形象更深刻的內涵。”(肖敏俊,2011)王安憶細膩的女性視角將宏大的城市和不同時期的氛圍全部都融合在一個以弄堂為背景的舞臺中,展現一個平凡的女性在城市的歷史長河中成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細碎家常、調朱弄粉,以及上海的城市圖景
王琦瑤的上海生活,夾雜著“細碎家常”與“調朱弄粉”的雙重意味,一方面,呈現著都市市民文化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是都市時尚與潮流文化表征。
(一)細碎家常,王琦瑤們的市民文化
一個城市的文化精神女性是作為主角的,無論外界如何風起云涌,她依舊圍爐夜話,打著橋牌過日子,正是這些生活才是造就一座城市的骨血根基。
王琦瑤是上海弄堂的女兒,在漫長的時間里她與自己作伴,王琦瑤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做些家常便飯,不會虧待自己。有時候訂一份晚報,在黃昏時間就看報打發時間,這些日常生活化的表達呈現了王琦瑤在世俗生活的平庸中執著的追求。即使也有過艱難的時刻,她也是聰慧堅定的,哪怕是退而求其次。她的一生經歷了中國近代重大的變革“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這些變換與王琦瑤都沒有關系。她在平安里依舊閑話家常,屋子里燒著爐火,圍爐夜話。王安憶曾經說過:“有人說我回避了許多現實社會的重大歷史事件,我覺得我不是在回避。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的,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李泓,2005)
城市的市民生活以及市民文化與女性的某種特性不謀而合,上海文化紛繁多樣是源于“上海是座移民城市,也是座紛繁復雜的城市,移民城市給了她海納百川的胸懷,也給了她智慧和心力,讓她更富有創造力和奇特的敢想敢做的思想。這就是這座城市的魅力,她給予人的不僅僅是物質的東西,也有精神的力量。”(董愛霞,2008)
(二)調朱弄粉,時尚與潮流的都市文化呈現
“王琦瑤是追隨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結隊的摩登。她們追隨潮流是照本宣科,不發表個人見解,也不追究所以然,全盤信托的。上海的時裝潮,是靠了王琦瑤她們才得以體現的。”(王安憶,2003)上海是摩登的化身,在上海女性的身上會看到摩登的影響。少女時代的王琦瑤是上海潮流的代表者,中年時期的王琦瑤是上海的潮流歷史。
從時興的潮流服飾、報刊上的愛情故事、陰丹士林藍的旗袍、藏在胭脂盒里的蝴蝶標本、精致的點心,愛麗絲神秘又昏暗的時光、各式各樣的發髻,掩蓋本質的香水到最后時間在她身上留下的深深淺淺的皺紋。她了解摩登的潮流是輪回的,哪怕是生了薇薇之后她只要把壓箱底的衣服拿出來稍稍修改就又成了上海大街上的一道亮麗風景。
成為三小姐之后,有點眾星捧月的意思,使她內心本就不安分的欲望多了呼之欲出的意味。這夜晚“派對”中的王琦瑤在人們眼中更是集萬種風情于一身的艷麗,這細化了上海內斂的審美趣味,“然而這一切的繁華只在城市的深處,王琦瑤走進上海的深處看到的是上海弄堂的昏暗,感受到的是繁華中的黯淡和對繁華終會消逝的一種傷感。”(張淑云,2006)
王琦瑤的美為上海繁華增添了神秘和風情,就像上海這座城市,“小說不是通過寫人來反映城,而是城就是人,王琦瑤就是這個城市的驚魂”(馬超,2001)
女性是都市的代言人,王琦瑤雖然平凡,但是光靠著平凡是得不到上海小姐這樣的殊榮的,她是大家眼中最有代表性的上海女性。王琦瑤的命運濃縮了一座城市的發展史,“女人象征一座城,女人就是這座城,傳達著生命的氣息,也閃露著衰亡虛無的征兆,我們本身就是就是城市圖像中的一部分,是這個城市之中微妙的元素,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積累著我們思想精華和生活碎渣”(徐珊,2004)
結語:
“都市不僅僅是政治性,經濟性的,也不僅僅是咖啡館、電影院、攝像館與美容院,對于上海而言,像王琦瑤這樣的普通市民更多的是弄堂,流言,閨閣、鴿子,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和生活心境。”(王哲,2004)
王琦瑤的坎坷一生,與上海的璀璨和萎靡相互依存,是一個城市的縮影。作為都市女性,王琦瑤就是“上海故事”最好的代表,上海給了她們最絢麗的舞臺讓她們各顯神通,她們也賦予了上海這座城市別樣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王安憶.長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
[2]南帆.城市的肖像—讀王安憶的長恨歌[J].小說評論,1998,9(6).
[3]張公善.呼喚體悟性的智慧批評——對國內研究王安憶《長恨歌》的反思[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
[4]張淑云.凄婉纏綿長恨歌——對王安憶《長恨歌》的三種解讀[J].柳州師專學報,2005(4).
[5]馬超.都市里的民間形態——王安憶《長恨歌》漫議[J].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01(1).
[6]張燕.人與城的融合——析《長恨歌》[J].滄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7(1).
[7]徐珊.論王安憶《長恨歌》的城市景觀[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
[8]王哲.海上風華及無盡悲歌——王安憶的長恨歌解讀[J].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7).
[9]肖敏俊.從長恨歌看王安憶筆下的人與城[J].文學教育,2011(09).
[10]董愛霞.女性城市歷史—從文化角度解讀王安憶的長恨歌[J].安徽文學,2008(6).
[11]許峰.《長恨歌》中王琦瑤人物形象及價值分析[J].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10(1).
[12]于哲霏.詩性的語言表達與詩化的日常生活——試析王安憶《長恨歌》的女性詩學特征[J].廣西設計學院學報(文學版),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