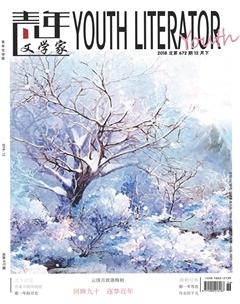另類的“青春之歌”
潘如成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01
《去趙國的邯鄲》關注的是實習隊長小丁及其手下實習生們構成的青年群體的生活狀態。作者信筆將幾個碎片化的生活場景串聯起來就成功勾畫出了這群青年的精神世界。將青年作為觀察對象,剖析青年精神狀態的寫作意圖使得這篇小說具備了“青春小說”的特質。
提起“青春小說”,大多數人想起的是謳歌革命青年林道靜成長歷程的《青春之歌》。將《去趙國的邯鄲》與《青春之歌》相對比,不難發現這兩首“青春之歌”的不同之處。小丁們擁有著與林道靜們截然不同的青春風景,這源于他們成長的時代之間巨大的反差。林道靜成長于以革命戰爭為主題的時代,而小丁們是在80、90年代進入自己的青春期的。這兩個相距甚遠的時代間的巨大差距弱化了小丁與林道靜這兩個青年間比較的意義。
小說對比了小丁與其父親對待“集體”的態度,小丁“討厭、痛恨集體”,而父親對集體卻有著“狂熱的愛”。這兩種集體觀念的對比包含了極大的價值,直觀地反映了小丁們與其父輩間不同的青春樣式。雖然小丁極力地想擺脫集體對自身的綁縛,但作為一名國營電廠的職工注定了他的生活與其父輩一樣要與集體緊緊地綁在一起。相比于《青春之歌》,十七年時期的兩部劇作《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能忘記》更適合與《去趙國的邯鄲》做文本互讀。兩者之間正好呈現了兩個時代兩種不同的青年典型、青春樣式。而這樣的不同正是由兩個時代的不同造就,顯現了時代的變遷路徑。
《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能忘記》里的青年的社會身份與小丁極其相似,他們是具備一定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且有公家身份的職工,因此他們都不得不面臨著如何處理好個人與集體關系的問題。前者出現的青年又正是小丁們的父輩一代,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可比性。小丁的父親瘋狂地熱愛著集體,這與《年輕的一代》里的肖繼業和《千萬不能忘記》里的季友良等青年是高度一致的。這些青年將生活的重心最大化地傾向了集體,幾乎閹除了個人生活的一切的欲求。他們有清晰明了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建設的光明圖景為他們指明了人生奮斗的方向。而小丁們與其父輩是背道而馳的,他們將個人放在首位,將集體視作實現自己充分發展的阻礙而加以排斥。所以小丁和實習生們喪失了對工作的熱情,不愿意遵守集體的規矩,用樁樁件件無聊的事兒打發在他們看來無聊的工廠生活。
然而小丁們在掙脫集體生活的牢籠之后卻沒有尋求到能夠實現自身充分發展的要素。所謂的自由賦予他們的是價值的虛空,與肖繼業們相比,他們的青春充滿了虛無、焦慮、迷惘等等諸多不確定因素。這在小丁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他知道自己不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卻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何方。尤其是在他意識到自己年近三十,“想干的事情還沒有一個眉目”這一冷酷現實之后,他對未來的恐懼意識進一步加深。他羨慕自己手下的實習生們對未來還有些許稀里糊涂的期許,嫉妒他們正處于二十出頭的青春年華,所以往往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使自己陷入到孤立的境地里。從這些實習生們身上,小丁能夠看到自己的過去,所以他能夠善意地對待他們,以“望天收”的方式放任他們。
小丁們的青春圖景中重要的一極是個人的欲望,這在小說里有多處直接的表現。小丁有讓人難以理解的運動欲望、有超乎常人的食欲、有想要壓抑住卻難以壓抑的性欲。這些人都會有的肉體欲望閃現著人性的光芒。與近乎于“滅人欲”的前輩文學書寫不同,朱文大膽地宣告著人欲的合理性,他在努力地為人欲正名。所以小丁和實習生們對于各種人欲的追尋都是在實踐著自己作為人的權力。人對合理性欲望的追求不再需要在崇高的價值信條下遮遮掩掩。對于人欲的正名化書寫所包含的人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意義不言而喻。當然人欲除了人的肉體存在的欲望之外還隱藏著人作為精神存在的欲求。小丁們近乎變態的欲望的發生更多是由精神層面驅動的。一方面他們欲望的宣泄來捍衛人之為人的權益,以此來反叛在他們看來禁錮他們的因襲的社會規制。另一方面正是因為無力徹底改變現狀造成的不安感以及對于未來無望的虛空感迫使他們只能通過變態的欲望去排泄無形中的壓力。
朱文通過這篇寫青年的小說塑造出了另類的“青春小說”,大大地顛覆了人們對于青春應該是洋溢著陽光的,青年應該是積極向上的一貫印象。但正是這種離經叛道才賦予了他筆下青年真實的生命,使得我們能夠窺見90年代知識青年的精神特質。
苦苦尋求未來方向而不得,只能陷入靈與肉掙扎漩渦的小丁們暴露出了同時代的一些問題。他們父輩曾經將烏托邦當成了堅定的精神倚靠,而在這一允諾逐漸失效之后,他們失去了能夠為他們指明奮斗方向的精神憑借。他們需要能夠明確告知自己做一件事情的目的性何在的價值信念,信念崩塌之后,他們也就徹底迷失了方向。對于那些不明世事的實習生而言,就連晨起跑步這樣簡單的小事情背后都應該存在明確的目的性。
小丁這樣的青年面對市場經濟洪流滾滾的90年代是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他們在同時代的邊緣化位置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是他們自己放棄的,還是時代拋棄了他們?市場經濟的盛行使得以集體利益為核心的舊意識形態分崩離析,在商業化時代,集體已經難堪維系舊式人際關系的重任。如果說舊的意識形態的失效使得青年失去了舊有的精神導師,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拒斥使得青年一時陷入了精神無所依的境地,那么市場經濟迅猛發展所帶來的新一輪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更迭對知識青年尋得精神存在的影響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