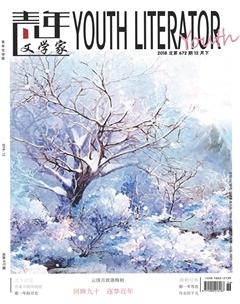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摩羅詩力說》的比較方法研究
唐萬濤
摘? 要:魯迅《摩羅詩力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研究其產生的環境和文學內在邏輯,對于由求別新聲于異邦到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進而構建當下文學理論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摩羅詩力說》;比較方法研究;文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01
魯迅《摩羅詩力說》的產生是必然的,中華民族經歷外國的船堅炮利被動打開國門,仁人志士不斷救國圖存。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魏源《海國圖志》、嚴復《天演論》等以期通過介紹西方進而有“制夷”之效;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運動以圖挽救將傾之國,然都已失敗告終。面對眾多仁人志士為挽救民族危亡不斷地貢獻著自身之力,魯迅也不例外,《摩羅詩力說》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形成。魯迅處于不斷向西方學習的時期,西方文論占據世界主流。許多與魯迅同時代的大家學者都在不斷地引入西方文學理論,不斷地分析與介紹,進而“求別新聲于異邦”[1]p28。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講述中國的文學內在邏輯。
魯迅勾勒“蓋文之留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1]p27與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有異曲同工之妙。曹丕認為氣在文章中的作用是顯著的“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與魯迅所講,其內在邏輯一致。文章講求內在的氣,進而各自有其特點,并不是千篇一律。同時提出“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1]p30詩并不是詩人所獨有,希冀其成為一個能“握撥一彈,心弦立應”,詩人成為那個能引起人共鳴的對象與載體。
魯迅對“詩無邪”持否定態度,“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后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弊。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古之做文多“悅媚豪右之作”,并且在“情感林泉”亦多“拘于無形之囹圄”。古今僅屈原“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可是其中“多芳菲凄惻之音”并沒有“反抗挑戰”。這其中蘊含著“攖”的前后變化。[1]p30-31
魯迅提出“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其術善也。”而后談到在之后的中國統治中出現的景象與其相反,是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于前說。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1]p30這里所提出的攖與老子所提出的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老子主張無為而治,其所主張的不攖人心,主體是統治者不攖人心,使其按照自身規律發展。而后者的攖,不允許詩人性解(Genius)影響干擾人心,存在著控制人的思想,讓人的思想按照統治者指定的方向發展,威脅到其統治地位的時候就會進行絞殺。
那么如何實現中國思想轉變轉而實現破書立說?魯迅進而轉向西方的摩羅詩派。拜倫、普希金、雪萊、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斯基、裴多菲等,“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維,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而實統于一宗:無不剛健,報誠守真;不取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魯迅通過對以上摩羅詩人的介紹,進而佐證自身的觀點。有日本學者提出《摩羅詩力說》是在魯迅的某種意圖支配下,根據當時找得到的材料寫成的①,屬于一種編譯。“天竺古有《韋陀》四種,瑰麗幽敻,稱世界大文;其《摩訶婆羅多》暨《摩羅衍那》二賦,亦至美妙……有但丁者統一,而無聲兆之俄人,終支離而已。”[1]p27說明一個國家或民族需要發為雄聲的人或文,“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1]p31“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1]p32與魯迅在文末所疾呼的那般發先覺之聲才能對民族和國家有著促進作用。但發覺先聲并不是國民就能在很快的時間內響應,相反地會進行抵制甚至反抗。
“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1]p38是為常態。魯迅批判國民的阿Q式精神,任何事物都在其內心得到勝利。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往往淪為先覺者落寞的墓志銘。悲憤交加,但是這并不能阻擋啟發民智的步伐。魯迅認為“平和為物,不見于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1]p29不能因為和平的景象失去批判的精神與視野。“臺陀開納(Theodor K?rner),慨然投筆,辭維也納國立劇場詩人之職,別其父母愛者,遂執兵行。”[1]p31到“敗拿破侖者……國民而已”[1]p32魯迅認為國民在其中伴隨著的重要作用。通過對西方摩羅詩派的介紹,魯迅期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啟迪民智,使民善美剛健,救民于荒寒。
魯迅所處的急劇變化的時代與當下所處的發展劇烈的時代有著共通之處。前者是在國家危難之跡,仁人志士尋求救國救民之策,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都奮力進取;后者是在國家富強時期,之前的人文哲學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亟待尋求新興之思想。當今如何進行中國文化的復興,是一個問題。前兩年是西方文化理論掌握著話語權,但是現在回溯其理論,中國文學理論式微,實際上,中國的文學理論歷史久于西方。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對“古事不道”,進而“別求新聲于異邦”[1]p28,當下則需要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詳細深度的分析,建立自己的理論自信。
注釋:
①北岡正子著 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4頁。
參考文獻:
[1]經典珍藏版 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
[2]熬忠.中國現代科學文藝論的一塊堅實基石——魯迅《摩羅詩力說》研究[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4(01).
[3]徐志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軔期[J].山西師大學報,1995(01).
[4]唐文娟.語言牢籠的革命——論《摩羅詩力說》的啟蒙話語[D].陜西師范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