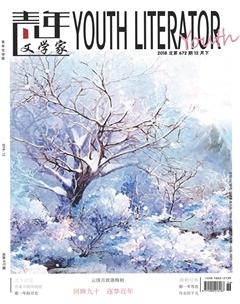井上靖筆下“異鄉人”的西域浪漫
基金項目:本論文受2017年北方民族大學校級一般科研項目資助,項目名稱為“近代以來的日本‘西域游記及其文化想象”。
摘? 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古代西域題材小說一直受到中國學界的持續關注,本文選取作家創作于1963年的《明妃曲》和《宦官中行說》兩部作品,并對兩部取材于歷史事實作品與史籍相異部分內容及其深層原因加以考察,從而明確井上靖如何借助兩名中原人士在面對異文化的探索中實現其西域浪漫的構想。
關鍵詞:井上靖;西域;異鄉人;明妃曲;宦官中行說
作者簡介:寇雅儒,北方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北京語言大學2016級亞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3
日本作家井上靖(Inoue Yasushi,1907-1991)以題材豐富的歷史小說享譽文壇,其中對古代西域題材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更被看做是他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井上靖自1950-1969年共計創作了包括《漆胡樽》(1950)、《樓蘭》(1958)、《明妃曲》(1963)《宦官中行說》(1963)等十五篇中國西域以及中亞題材的歷史小說。
為了更好地把握井上靖歷史小說的特色,文學評論家曾根博義按照發表順序并結合篇幅和創作風格將其歷史題材作品分成了以下四個階段。①
根據上述劃分不難看出井上靖的西域題材的創作可謂貫穿其歷史小說的前三個階段。在其諸多的西域小說中日本評論界普遍將其作為井上靖歷史小說中的一部分因而更集中于單個西域作品的研究但缺乏對西域作品整體的把握,而縱觀國內的研究會發現更多集中于探討其作品中對中國文化的受容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等內容。這些尤其在《天平之甍》以及《敦煌》兩部作品的相關研究中更為突出,鑒于井上靖西域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對中國文化友好性有過度闡釋嫌疑的現狀,本文試圖以《明妃曲》(1963)、《宦官中行說》(1963)兩部都取材于歷史事實作品為研究對象考察兩部作品中與史籍相異部分內容及其深層原因,從而明確井上靖如何借助兩名中原人士在面對異文化的探索中實現其西域浪漫的構想。雖然《明妃曲》、《宦官中行說》兩部作品創作時間有十年之差,但在主題上存在內在的關聯。即兩位主人公王昭君、中行說都作為真實的中原文化背景的歷史人物進入西域后面對的異文化沖擊與調適來表現“異鄉人”在西域②對自我命運把握和未知生活探索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靖在創作這些西域題材的作品時,并未實地到訪過故事背景地。“西域”雖然是漢代文獻中就已經有的地理詞匯,但是,作為一個有意識地連接各國歷史、語言和宗教來研究的歷史世界,卻是近代的事情[1]。尤其近代以來日本大谷探險隊步西方后塵進行的西域探險以及由此推動的日本的“西域”研究都成為了作家創作時潛在的知識背景。同時作家自己也坦言自學生時代起就閱讀了大量和西域相關的書籍。因此西域對于井上靖而言或許并非實際的風景,而是一種由歷史、語言和想象構成的先驗概念。“浪漫”一詞在漢日兩種語言中對應不同的解釋,辭海中的解釋為兩種即:①富有詩意,充滿幻想;②行為放蕩,不拘不節(常指男女關系而言)。日本大辭泉的解釋為:①傳奇故事或長篇小說;②對夢想和冒險具有強烈的憧憬。但本文所指的西域浪漫來自日語中的“西域ロマン”這一表達,在此采用大辭泉的第二種解釋即“對夢想和冒險具有強烈的憧憬”。
*真實的歷史背景與虛構的細節
回顧作品會發現《明妃曲》、《宦官中行說》中王昭君、中行說兩位主人公前往西域雖然都源自朝廷派遣、并承擔著中原權力中心交付的政治使命,但在個人動機上井上靖賦予了兩人明顯的差別。與渴求在西域建功立業擁有強烈內在動機的班超不同。《明妃曲》中的王昭君井上靖借助酷愛匈奴的圖書管理員田津岡的描述反寫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使得廣為流傳的元曲《漢宮秋》中為民族大義遠赴匈奴的王昭君悲情形象演變為“漢恩自淺胡自深”的多情女子。相較而言宦官中行說的西域之行可謂奉文帝之命迫不得已,而得知自己要作為漢室公主的侍從一同前往匈奴時 “倘若您真要打發我去匈奴的話,那肯定對朝廷是不會有什么好處的” 的回應既是對遠赴西域的一種反抗表現,同時也成為其之后忠心輔佐單于、對抗漢室的一個預言。
或許是帶著濃烈西域文化印記的班超回歸中原文化時遭遇的困境過大,井上靖安排下一次中原人的出走距離《異域之人》有十年之隔,這就是創作于1963年的《明妃曲》和《宦官中行說》,而且這一次主人公們的目的地更遠,是讓歷任漢朝皇帝頭疼的匈奴。
王昭君和宦官中行說遠赴匈奴的內在動機在上文已有論述,與渴求在西域建功立業擁有強烈內在動機的班超不同。《明妃曲》中的王昭君作為與主人公“我”并列的另外一個主人公是通過虛構人物—圖書管理員田津岡龍英的描述得以呈現。田津岡看來馬致遠《漢宮秋》中關于王昭君的行為方式的敘述過于離奇即“一方面她決心為國犧牲而自愿嫁到匈奴去,而另一方面她卻又受不了與漢土的離別之情,投河自盡”[2]。因此就有了田津岡宣稱意外發現于圖書館倉庫的元朝隨筆書名也叫《漢宮秋》。在這本田津岡版《漢宮秋》中王昭君遠嫁匈奴表面上是因為“小妾愿嫁蕃邦。倘若刀兵得以寧息,妾亦能留名青史”,實則是因為心里一直惦記著有過一面之緣的單于長子。但田津岡所描述的為了愛情前往匈奴的王昭君難以逃脫中原對其命運悲慘的想象,而面對作家設置的兩次返回漢土的機會,王昭君都拒絕了。其對西域的強烈認同體現得最為明顯的莫過于得知漢土上下流傳著她不肯嫁給單于投河而死的故事后的反應:無動于衷毫無感慨。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另一個主人公“我”認為田津岡版的昭君是他本人的創作,理由是田津岡講完這個故事就再沒提到過那份新資料了。而“我”對田津岡創作的昭君故事的態度則是“蠻有意思”。 可以說至此井上靖借助虛構人物田津岡在昭君出塞這一故事的歷史縫隙中摻入了自己所特有的解釋,從而完成了中原人士向西域浪漫的徹底歸化。如果說王昭君認同西域(匈奴)的過程完全是由個人情感主導充滿了感性的一面,沒有那么多心理掙扎的話,宦官中行說則完全不同,面對漢室強行選派的和親侍從這一安排,中行說說出了那句反抗預言“必我也,為漢患者。”但反抗無用。中原人中行說在匈奴的生活就是每天伺候單于,在日復一日的觀察與接觸中,中行說對匈奴日漸熟悉也形成了自己的判斷:“他們對某些事很精通,而對某些事卻極其無知。”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行說“以太監獨特的神經和感受性敏銳地感受到了”匈奴那種單純,殺氣騰騰的樣子,那種精悍勁兒,那種冷酷無情,那種重視實利的做法,那種無法按現代道德標準衡量的行動[3]。進而癡迷其中。而關于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中行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強力反駁漢使傲慢詰問匈奴輕蔑老人、子娶繼母、缺乏禮儀之時,至此中原人中行說的匈奴文化認同身份基本確立。而《史記卷百一十·匈奴列傳第五十》,以及《漢書卷二十八·外夷傳·匈奴傳》中所記載的中行說勸說單于堅持匈奴飲食文化的內容,也全都在井上靖筆下得到了完整的呈現。而作者做出這一呈現選擇自身就是作家創作意圖的一種外在反應。一個來自強勢文化的中原人士勸說單于擺脫對漢朝物產的依賴、放棄對漢風俗的仿效,進而肯定匈奴飲食文化應該說會增強匈奴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此一來中行說的中原視角的價值在匈奴才得以體現,反對漢化保持獨立才能實現異鄉人中行說的西域浪漫。但僅有這些建議還不夠,年邁的中行說內心還須接受中原文化的另一考驗:落葉歸根回到漢土。即便他的身份是一個宦官。通覽《史記卷百一十·匈奴列傳第五十》,以及《漢書卷二十八·外夷傳·匈奴傳》的內容會發現關于中行說的記載止于“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4] 。之后再無描述。中行說在全力輔佐匈奴單于對抗漢室的過程中,是否也曾有過對故國的一絲留戀,我們無法在《史記》與《漢書》的相關記載中尋得蛛絲馬跡,而這剛好也留給了作家足夠的想象空間。于是在中行說抵達匈奴十年后,老上單于去世、軍臣單于即位之際,作品中順理成章地出現了一位中行說面熟的漢朝使者履行文帝將其召還的命令。面對漢使拋出的“都城長安的熟人、以及京城的風是甜的,水是美的”這樣試圖喚起他中原文化記憶的表述,中行說雖然沒有否認其對故土中原的懷念,但依然選擇“倘若沒有單于的命令,我是不能回去的。”曾經“決心埋尸骨于異域”的班超未能實現的愿望在中行說這里最終得以實現。井上靖以“如今這大漠之地便是我的祖國,是我的葬身之地。”宣告了中行說徹底經受住了這場來自中原文化召喚的考驗。也坐實了其對匈奴文化的歸屬感。
這一過程也足以表明作家在書寫中國西域題材小說時對歷史人物的選擇顯然不是出于其個人喜好的隨意取舍,而是醞釀已久的安排。面對上述歷史人物的文化認同選擇我們不禁產生疑問的是,放棄中原扎根“西域”除了源于作者自學生時代就產生的對所謂“未知、夢想、謎題、冒險”西域的強烈喜好的一種外在表露以外,借助“西域”舞臺,作家最終想要表達何種關切。而關于歷史與文學關系的探討正如野家啟一③在《物語的哲學》中提到的:歷史是通過物語才實現了其言說。而言說歷史的物語又總是離不開“時代”與“政治”的影響[5] 。
回顧井上靖西域小說的創作時期會發現集中在1950-1969的近二十年,而這期間正是日本經歷戰后重建的重要階段,尤其在戰后初期對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而言,日本傳統的東西都應該是重新予以審視的對象。井上靖也在題為《我與沙丘④》的紀行隨筆中寫道:“戰爭結束后,我迫切地想要表達自我,除了文學沒有更合適表達自我的工作的了”[6]。不言而喻作家通過“西域”表達的是對自我的關切,而并非流于表面的單純喜愛之情。那么對自我的關切為何要選擇從“西域”切入呢?
在井上靖和司馬遼太郎他們看來,日本人對西域的憧憬最早源于“日本人熱烈追求文化的時期,即從派出遣唐使的時代就開始了” [7]。其間他們也討論了讀到詩人李白描寫征夫之妻秋夜懷思遠征邊陲的良人的詩句“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時作為日本人的熱血沸騰感。而“這種體內感覺到的血脈賁張可能就是遺傳了古昔遣唐使們興奮的心情” [8]。而司馬遼太郎和陳舜臣在《對西域無限的憧憬》對談中提到:“要說我們對西域的偏愛是怎么回事的話,答案可能有點出乎意料,那或許是因為唐代長安士人對西域的憧憬被原封不動的凍結、保存在了日本” [9]。作家們在日本人對西域憧憬的時間始于遣唐使的唐朝似乎形成了默契。有關西域與日本文化的關聯井上靖個人則提到最想去的往昔都城分別是唐長安以及威尼斯和伊斯坦布爾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這些城市無一例外在當時都充滿了異文化的沖突。“將這些城市連接起來形成的文化之路最終都注入了法隆寺、奈良·平安的古都” [10]。由此我們不難窺見在現代日本作家眼中古代西域之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而近代“西域”與日本的相遇則要來到1902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所組織的西域探險,這次探險給日本留下了眾多寶貴的西域史料。以此為契機日本的史學界的“西域”研究在白鳥庫吉、桑原騭藏、藤田豐八等東洋史學者的推動下促成了日本學術界在觀念和制度上形成了取代“中國史”的“東洋史”。由于戰爭的緣故距離西域探險之后日本與西域的再次相遇到了戰后的1956年,主要成員有作家草野心平。隨后的57年包括陳舜臣在內的作家、記者在每日新聞的贊助下進入新疆調查。之后大批日本作家、記者、學者涌入西域,井上靖本人也從65年至77先后四次進入中亞、新疆進行文化交流和考察。
關于日本人為何會執著于對西域的喜愛,司馬遼太郎也有進一步的描述“我們的文化史里只有接受而沒有沖突,想象在被日本接受之前的某個陌生的城市發生過的激烈沖突,比自己卷入同時代的沖突可能更讓人熱血沸騰吧”[11]。通過上述日本作家們的對談,似乎“西域”作為一個異文化集合地成為了日本人的精神故鄉,對“西域”的言說也仿佛成為了日本作家探尋其文化根源的一種方式。而關于這一點我們在井上靖所寫的另外一篇文化隨筆《心的文化》中看出不同的端倪:“我們從同時代的中國引入大量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唐詩也傳入好多,可是它沒有對日本起到絲毫影響,唐詩表現的全部是長安繁華的街道,同時期的《萬葉集》里是無論如何想象不出”奈良城“的”[12]。井上靖在之后列舉了《萬葉集》中悼亡、戀愛、旅途紀行為主題詩歌對心靈的歌頌,并指出這種以心靈為中心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了日本文化的主流。
總而言之,日本作家井上靖通過《明妃曲》和 《宦官中行說》兩部作品構筑了以漢室中原文化為他者參照下,兩位漢朝歷史人物做出的西域文化認同這一選擇投射出了其自戰后以來的自我關切。在處理這一關切時,井上靖作為日本的作家首先是以日本人所屬文化的普遍性作為前提的。即對西域浪漫的書寫是日本遣唐使對唐詩中抒發的西域憧憬所激發出的鄉愁情緒被完整封存在日本的文化基因中,這種文化記憶又經近代明治以來日本人對西域的實地探索以后更加的牢固。表面上看對西域浪漫的書寫似乎是在緬懷日本熱烈追求異文化的遣唐使時期,實際上在井上靖看來《萬葉集》中以悼亡、戀愛、旅途紀行為代表歌頌心靈的詩歌才是日本獨特的傳統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西域浪漫的書寫只是對日本以心靈為中心這一傳統文化的繼承。
注釋:
①參見高橋英夫·他.井上靖 (群像 日本の作家)[M]. 小學館,1991:p183.本文在引用時省略了部分代表作品。
②“西域”作為一個歷史變化的地理詞匯,在《漢書·西域傳》中都被描述為“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役屬匈奴”。本文中的西域包含了文章開頭部分所列井上靖的所有西域題材作品涉及的主要區域你,因此本文將對匈奴和“西域” 作地理上的區分,文化概念統稱為“西域”。
③野家啟一(1949-),男,日本哲學家,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
④筆者譯,原文標題為「砂丘と私」。
參考文獻:
[1]葛兆光,從“西域”到“東海 ”——一個新歷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問題[J].文史哲,2010(01)P19.
[2]董學昌,等譯. 井上靖中國古代歷史小說選·敦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P484.
[3]同[2],P465.
[4]班固原著.呂祖謙編纂.漢書詳節卷二十八·外夷傳·匈奴傳[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596.
[5]轉引自孟慶樞主編:中日文化文學比較研究2014[M].吉林出版集團責任有限公司,2014. P240.池睿:論“一之谷之戰”的文學敘事.
[6]井上靖.井上靖全集(第二十七卷)[M].東京:新潮社,1997. P467.筆者譯.
[7] 井上靖.司馬遼太郎.西域をゆく[M].東京:文藝春秋,1998. P74.筆者譯3.
[8]同[7], P75. 筆者自譯.
[9]司馬遼太郎.陳舜臣.対談 中國を考える[M].東京:文藝春秋,1997. P209.筆者自譯.
[10]同[7], P77. 筆者自譯.
[11]同[7], P77. 筆者自譯.
[12]井上靖.東山魁夷等著.周世榮譯.日本人與日本文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