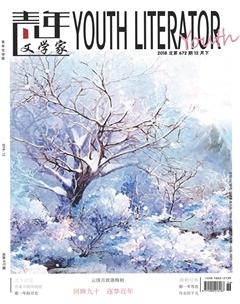《今昔物語集》中的“狐女”故事特點分析
摘? 要:狐貍在日本文化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狐女”這一文學形象尤其特別。她們在傳說中亦善亦惡充滿魅力。在日本古典文學中,《今昔物語集》中所包含的狐貍相關的故事最多。本文中將以文本為基礎探索該作品中“狐女”的特點。
關鍵詞:《今昔物語集》;“狐女”;狐信仰
作者簡介:吳倍倍(1993.1-),女,遼寧大連人,東北大學2016級碩士,研究方向:日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6--01
《今昔物語集》全文一共三十一卷,狐貍相關的內容主分散在卷五、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二十、卷二十六和卷二十七中,共有16篇,而其中“狐女”故事主要是卷五第十九話、卷十四第五話、卷十六第十七話、卷二十七第二十九話、第三十一話、第三十八話、第三十九話、第四十話和第四十一話,共9篇。本文想就這些“狐女”故事的特征進行探討。
《今昔物語集》中的“狐女”故事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她們自始至終都被當做異類對待,無法擺脫妖怪身份。日本民間傳說狐貍具有不為人知的與生俱來的神秘特質,日本人對狐貍的感情不僅僅是恐懼也有崇敬。這樣雙重的感情是由于狐貍附身這一說法的存在。狐貍附身是狐信仰的變種,與此相關的最早的故事是《今昔物語集》卷二十七的第四十話——《託人被取玉乞返報恩語》。坂井田瞳說:“狐貍對于我們日本人來說是有魅力的存在,但同時也被當做具有魔性的存在而忌諱,這是一種相互矛盾的狐觀。”由此可知日本人眼中的狐貍永遠都跟人之間有一線之隔。如《今昔物語集》卷二十七第三十八話《狐變女形值播磨安高語》中,安高最初見到“狐女”時為其美貌所吸引故而與其同行,但是由于懷疑其是狐妖又裝作強盜嚇唬她。這個過程中人類并非誠意而是抱了戲耍之心的,暴露了人類對“狐女”的警戒和偏見。而“狐女”受驚逃走后安高后悔沒有殺之而后快的心理又體現了人類對“狐女”的嫌惡與敵意。另外《今昔物語集》中還有與其結婚后因發現其是“狐女”而背棄的故事。因此,盡管“狐女”們或與人為友甚至成為愛人但永遠無法像中國志怪故事里的“狐女”一樣融入人類社會。
《今昔物語集》中的“狐女”幾乎都是帶著某種目的與人類男子相遇的。在這里筆者將9篇“狐女”故事按照不同目的劃分如下:報恩有卷二十七第四十話、卷五第十九話,共2篇;作祟有卷十六第十七話、卷二十七第二十九話、第三十八話、第三十九話、第四十一話,共5篇;自我保護有卷二十九第三十一話,一篇;另有其他分類一篇。
從以上內容來看,9篇典型的“狐女”故事中“狐女”的目的有報恩、作祟和自我保護。其中目的為報恩和自我保護加上其他共有4篇,作祟的有5篇。基本上屬于各占一半,這與日本的“狐女”作為神或者神使亦善亦惡的形象相符合。
大坪俊介在其《從<大雁草子>看異類婚姻譚的悲戀--以狐女譚比較為中心》中指出,在異類婚姻譚中,故事都是以人類與異類的分離為結局的。異類現出其本體后或者死去或者回到自己的世界。我們可以在《今昔物語集》的“狐女”故事中驗證這個特點。筆者將故事對應的結局整理如下:卷14第5話為救野干死寫法花人語——變成神回到異界;卷16第17話備中國賀陽良藤為狐夫得觀音助語——被男方發現,現出原形逃跑;卷27第29話話雅通中將家在同形乳母二人語——受驚逃跑;卷27第31話話三善清行宰相家渡語——聽到宰相的話后自己離開;卷27第38話話狐変女形值播磨安高語——受驚逃跑;卷27第39話狐変人妻形來家語——被男方捕捉,現原形逃跑;卷27第40話狐託人被取玉乞返報恩語——被僧人趕走;卷27第41話高陽川狐變女乗馬尻語——被火燒逃走。從以上的總結我們可以看出,《今昔物語集》中的“狐女”們最后無一例外都是離開了人類社會,且結果大都不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昔物語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搜神記》的影響。《搜神記》是中國東晉時期干寶所著的志怪類小說集,是中國志怪類小說的代表作。至今為止在日本發現的有關《搜神記》的最早記錄是在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年)藤原佐理所著的《日本國現在書目錄》中。《搜神記》是東晉(316-412)時期完成的作品,眾所周知,在這個時代之后有中日兩國文化交流非常頻繁的隋唐時代(581-907),從時間上來看我們可以推測在891年之前《搜神記》傳入日本的可能性非常高。并且,通過對兩部作品內容上的對比我們也能夠得到證實。《搜神記》卷十一有如下內容。“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于此遂愈。”而與此相對應的在《今昔物語集》卷九第三十二中的《河南人婦依姑令食蚯蚓羹得現報語》一則幾乎是相同的故事內容。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今昔物語集》中的“狐女”故事與中國的《搜神記》有所關聯。這些故事中的“狐女”首先永遠無法真正融入人類社會,且她們在與人接觸的最初都是抱著或好或壞的目的,但最終都不得不黯然離開,或者死去或者回到異界。
參考文獻:
[1]坂井田瞳.中日文化探索[J].名古屋:中京大學教養論叢第,1996,(36).1291-1330.
[2]柳垣陽子.狐譚研究―以《今昔物語集》為中心[J].松山:愛媛國文研究,1997,(47).1-13.
[3]小島孝之.志怪的講述方法―以《今昔物語集》卷二十七為中心[C].東京:成城國文學論集 ,2007 ,(31).93-112.
[4]大坪俊介.從<大雁草子>看異類婚姻譚的悲戀--以狐女譚比較為中心[C].東京: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2010.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