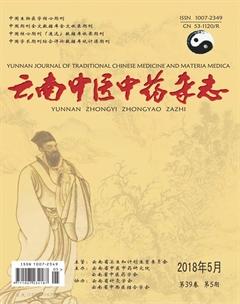趙淳教授病證結(jié)合治療高血壓病的經(jīng)驗
張惠斌 楊晟運 趙淳
摘要:介紹趙淳教授病證結(jié)合治療高血壓病的經(jīng)驗,認為中醫(yī)辨證肝陽上亢挾痰瘀證較為常見,論治應(yīng)以平肝潛陽為法,自擬定眩平壓方,運用于臨床,療效較好。
關(guān)鍵詞: 高血壓病;病證結(jié)合;趙淳;治療經(jīng)驗
中圖分類號:R5441? ?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8)05-0006-03
趙淳,云南中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暨云南省中醫(yī)醫(yī)院主任醫(yī)師、教授,第三、四、五、六批全國老中醫(yī)藥專家學術(shù)經(jīng)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云南省首批中醫(yī)藥師帶徒指導老師,云南省榮譽名中醫(yī),對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在國內(nèi)享有盛名。筆者在云南省中醫(yī)醫(yī)院進修,有幸侍診左右,蒙受教誨,現(xiàn)將趙老防治高血壓的經(jīng)驗介紹如下,以饗同道。
1 探究病機,明晰醫(yī)理
趙淳教授指出從現(xiàn)代醫(yī)學而言高血壓病(原發(fā)性高血壓)是一種由遺傳因素和環(huán)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多基因遺傳病。目前認為本病是在一定的遺傳易感性基礎(chǔ)上經(jīng)多種后天因素作用所致。后天因素包括:神經(jīng)、精神作用,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RAA)系統(tǒng)平衡失調(diào),胰島素抵抗,鈉過多,肥胖,吸煙,飲酒過度等。
從中醫(yī)學角度而言根據(jù)高血壓病的主要癥狀為頭痛、眩暈,故高血壓病可歸屬于中醫(yī)學頭痛或眩暈、薄厥等范疇。趙淳教授指出古代醫(yī)家早就對頭痛、眩暈的病因病機有精辟的論述,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類證治裁》云:“高年腎液已衰,水不涵木。”故高血壓病與肝、腎關(guān)系密切。朱丹溪認為:“無痰不眩,無火不暈。”李東垣謂:“凡頭痛皆以風藥治之者,總其大體而言,高巔之上,惟風可到。”《血證論》云:“瘀血攻心,心痛頭眩。”這些論述都說明高血壓病與風、火、痰、瘀等致病因素有關(guān)。高血壓病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常與情志失調(diào),飲食不節(jié),內(nèi)傷虛損等因素有關(guān)。高血壓病所引起的眩暈、頭痛,其病因雖然不一,但是肝腎陰陽失調(diào),心腦腎等臟器受損為其發(fā)病關(guān)鍵,病理因素有風、火、痰、瘀、虛。其病性多為下虛上實,虛實夾雜。肝腎不足為下虛,肝陽上亢,風火、風痰上擾為上實。病程早期多以實證為主或虛實夾雜,晚期常以虛證為主或虛實夾雜。
上述認識說明高血壓病的病因病機、病理環(huán)節(jié)十分復雜,故僅對患者單純降壓治療難以取得理想效果,只有采取中西醫(yī)結(jié)合綜合治療措施(包括生活方式干預,藥物治療等)對患者進行整體調(diào)節(jié)才能提高本病的控制率,取得滿意療效。
2 診治力求規(guī)范化與個體化相結(jié)合
趙淳教授指出對高血壓1級,低危與中危患者應(yīng)認真改變生活方式,并按中醫(yī)辨證論治,大多數(shù)患者即可達到治療目標;對高血壓2、3級,高危與極高危患者須立即開始對高血壓及并存的危險因素和臨床癥狀進行藥物治療。要充分發(fā)揮中西醫(yī)藥各自的優(yōu)勢,做到病證結(jié)合、優(yōu)勢互補,制定和完善中西醫(yī)結(jié)合優(yōu)化診治方案,實施個體化治療并持之以恒[1~2]。
3 辨治經(jīng)驗
趙淳教授指出高血壓病中醫(yī)辨證大致分為肝陽上亢、痰濁中阻、肝腎虧虛、痰瘀阻絡(luò)4個證型,各證型可單獨出現(xiàn),亦可相互并見,如肝陽上亢兼肝腎陰虛,肝陽上亢兼夾痰濁、血瘀等證,須詳察病情,辨證治療。臨床上高血壓病患者常伴有血脂異常、肥胖、糖耐量受損或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故中醫(yī)辨證以肝陽上亢挾痰瘀證,論治應(yīng)以平肝潛陽法為主,同時佐以運用滋養(yǎng)肝腎、豁痰降濁、活血化瘀通絡(luò)等治法,趙淳教授經(jīng)過多年的理論研究及臨床實踐,總結(jié)出定眩平壓方[1],運用于臨床療效較好。現(xiàn)將本方簡介如下:組成:天麻15 g,鉤藤15 g(后下),石決明30 g(先煎),夏枯草15 g,葛根15 g,桑葉10 g,菊花10 g,懷牛膝15 g,白芍15 g,炒杜仲15 g,桑寄生15 g,茯神20 g,夜交藤15 g,益母草10 g,丹參15 g,虎杖15 g,甘草6 g。功效:平肝潛陽,滋養(yǎng)肝腎,豁痰化瘀。主治:眩暈之肝腎陰虛,肝陽上亢,兼夾痰瘀證。現(xiàn)代常用于高血壓、腦血管病見上述證候者。方解:陰虛陽亢,痰瘀上犯清竅是高血壓病的重要病機之一。
方中天麻熄風平肝,止頭痛,定眩暈,鉤藤清熱熄風,石決明平肝潛陽、清肝明目,三藥并用為君藥;夏枯草、葛根、桑葉、菊花清肝瀉火,利頭目為臣藥;懷牛膝、白芍、杜仲、桑寄生補益肝腎,茯神、夜交藤養(yǎng)血安神,益母草、丹參清熱活血,虎杖豁痰化濁共為佐藥,甘草調(diào)和諸藥為使藥。用法用量:石決明先煎30 min,其他藥用溫水浸泡30 min,然后把藥混勻再煮20 min,煮3次,混合均勻,飯后溫服,每次150 mL,每日3次,每日1劑。現(xiàn)代常用中藥配方顆粒,服用方便,療效確切。注意事項:調(diào)情志,低鹽清淡飲食,忌肥甘厚膩之品。臨床應(yīng)用:陰虛較甚,舌紅少苔,脈細弦數(shù)者,可加生地、玄參、女貞子、首烏等以滋養(yǎng)肝腎之陰。若肝火亢盛,眩暈,頭痛較甚,耳鳴、耳聾突作,目赤,口苦,舌紅苔黃燥,脈弦數(shù),可加用丹皮、桅子、黃芩等清肝瀉火。便秘者可加用大黃、芒硝等以通腑泄熱。若眩暈劇烈,嘔惡,手足麻木或震顫者,有陽動化風之勢,加用生龍骨、生牡蠣、珍珠母、羚羊角等以鎮(zhèn)肝熄風。
4 病案舉例
何某,女,67歲,2011年6月14日初診,發(fā)病節(jié)氣芒種8天。患者訴頭暈脹痛反復發(fā)作1年余。自2010年1月始感頭暈,枕部脹痛,自服“去痛片”后緩解,1周后頭暈、脹痛再作,伴惡心、耳鳴,當時測血壓150/90 mmHg,之后多次測血壓均高于正常,在某醫(yī)院診斷為“高血壓病”、“頸椎病”。予“氨氯地平片”每日1片,口服,半個月后血壓降至正常,但出現(xiàn)雙膝以下肢體浮腫,遂來本院就診。刻下癥見:頭暈目眩,枕頸部脹痛,夜難入寐,心煩,手足心熱,耳鳴,口苦咽干,納食尚可,大便干,小便正常。舌質(zhì)暗紅夾瘀,苔薄黃,脈弦滑。身高155 cm,體重66 kg。西醫(yī)診斷:高血壓病1級,高危組,頸椎病。中醫(yī)診斷:眩暈 肝腎陰虛,肝陽上亢,兼夾痰瘀證。屬虛實夾雜之證。治宜滋養(yǎng)肝腎,平肝潛陽,豁痰化瘀,予定眩平壓方加炒酸棗仁15 g,茯苓20 g,澤瀉15 g,6劑,水煎服,每兩日1劑,每次150 mL,每日3次。囑暫停口服氨氯地平片。
二診:2011年6月26日,患者經(jīng)上述治療后頭暈痛,少寐,口苦咽干均見明顯改善,雙小腿已無水腫。但仍感心煩、手足心熱、,舌淡暗紅,苔薄黃,脈細弦。血壓140/80mmHg。心煩、口干苦、咽干、脈弦,此乃水不涵,肝腎之陰不足,肝熱猶存之征,故上方去茯苓、澤瀉,加女貞子15 g,枸杞子15 g,地骨皮15 g。6劑,水煎服,每兩日1劑,每次150 mL,每日3次。
三診:2011年7月12日,患者僅感夜間口稍干,余無不適,舌淡紅,苔薄黃,脈弦細。血壓140/80 mmHg。心率86次/分,律齊,A2>P2。此為肝陽漸臻平潛,陰虛陽亢之證已較輕微。以滋陰平肝法鞏固療效。守上方治療。6劑,水煎服,每兩日1劑,每次150 mL,每日3次。
停藥1月后多次來復查血壓均正常,無不適感。囑低鹽清淡飲食,控制食量、細嚼慢咽,適當運動,保持樂觀情緒。堅持長期服用具有滋陰潛陽作用的松
齡血脈康膠囊(鮮松葉、葛根、珍珠層粉)、杞菊地黃膠囊及具有活血化瘀、豁痰降濁之功的舒心降脂片以保健養(yǎng)生。
按:該患者年老體弱,肝腎虧虛,水不涵木,肝陽上亢,平素嗜食肥甘,久坐少動,傷于脾胃,健運失司,以致水谷不化精微,聚濕生痰,痰阻血脈,血脈不暢,日久成瘀,痰瘀互結(jié),則清陽不升,濁陰不降,以致發(fā)為眩暈。辨證屬肝腎陰虛,肝陽上亢,兼夾痰瘀證,治宜滋養(yǎng)肝腎,平肝潛陽,豁痰化瘀,予定眩平壓方隨癥加減施治,藥證相符,切中病機,故獲良效。
參考文獻:
[1]趙淳病癥結(jié)合救治急危重癥——趙淳學術(shù)思想與臨床經(jīng)驗集[M].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15:1
[2]劉紅英中醫(yī)心病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