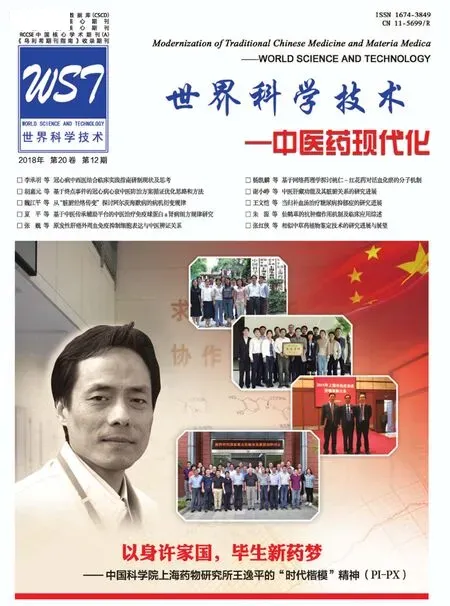冠心病中醫藥干預時機的循證研究設計與思考*
張曉雨,蔣 寅,孫 楊,劉 巖,張立晶,商洪才
(1.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中醫內科學教育部和北京市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700;2.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 北京 100700;3.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心內科 北京 100700)
目前許多臨床常用的中醫藥治療方案在起效關鍵環節的研究尚不清楚,如治療針對的適應人群、最佳干預時機以及遠后效應如何,影響中醫藥療效體現,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不良反應發生。在循證治療理念指導下優化臨床防治方案,對改善臨床用藥不合理現象,發揮中醫藥優勢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醫藥現代化研究”重點專項“冠心病(心絞痛-心肌梗死-心衰)中醫藥防治方案的循證優化及療效機制”項目總體設計下[1],結合課題二中醫藥在心梗介入圍手術期干預時機案例及國外的冠心病相關研究案例,對試驗設計要點進行梳理,希冀為以干預時機為關鍵環節的方案優化研究提供借鑒。
1 中醫藥干預時機的研究意義
中醫藥干預時機有兩層含義。宏觀層面,在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中醫藥可發揮不同程度的防治作用,在恰當的時機采取針對性干預策略有助于延緩或切斷疾病進展。以心血管事件鏈不同階段干預為例,疾病前期“三高”階段中醫藥干預著力控制危險因素(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改善體質,“未病先防”;在冠心病心肌缺血階段,控制心絞痛癥狀反復,預防不良事件發生;在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階段,發揮緩解癥狀,提高生活質量,改善預后的作用。微觀層面,某種中醫療法具體在什么時點應用效果最佳?如在發作期還是緩解期,亦或是一天的某個時辰;當與西醫治療聯合應用時,中醫何時介入最好?如在心肌梗死經皮冠狀動脈介入(PCI)治療術前還是術后。明確干預時機,是使中醫療法發揮最佳療效的關鍵環節之一,也是臨床決策的重點,值得研究關注。

圖1 中醫藥干預時機臨床研究文獻關系圖
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數據庫檢索中醫藥干預時機類文章共914篇,去重后剩674篇,其中篩選中醫藥干預時機臨床研究文章104篇,以針刺治療面神經麻痹、中風的干預時機研究最多(圖1)。但從臨床研究設計方面尚缺乏總結梳理。本文將從干預時機的選擇及臨床試驗設計要點兩方面進行闡述:
2 干預時機的選擇
2.1 基線調查
發現研究或實踐中是否存在治療干預時機混亂不清的問題,需要首先進行基線調查,通常可從系統評價或觀察性研究中獲得線索。雖然目前中醫藥臨床試驗及系統評價存在研究質量不足的問題,使得研究結果難以直接轉化應用,但仍可為臨床試驗提供改進建議等隱形證據,為進一步研究指出問題與方向[2]。我們在系統評價中醫防治心梗介入圍手術期無復流的研究現狀時發現,有幾個中藥品種可能有潛在效果,但療效指標測量方式不一,使得結果難以合并,且試驗數量少、樣本量小、質量偏低,難以得到確定性結論。此外,我們還發現不同研究中中藥干預的時機不同,即使同一中藥在不同研究中的給藥時機也不同,如分別在PCI術前、術中或術后干預(圖2),提示我們中藥防治無復流的最佳時機和可能機制尚不清楚,需要進一步研究。
另一種則是從回顧性的數據分析中發現問題。如通過大型回顧性隊列研究,探尋華法林相關顱內出血后重啟抗凝治療的最佳時機。研究人員回顧了2869名患者的隨訪數據,并集中觀察第一周生存患者和具有心血管抗凝指征或先兆卒中的患者數據,發現大約10-30周后重啟華法林治療,再發顱內出血或缺血性中風的復合風險最低[3],而既往有研究認為重啟華法林治療在2周內、72小時后可能比較安全。該結果為進一步開展研究干預時機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提供了更清晰的線索。此外,分析藥物臨床應用數據也會給予很多研究提示。如基于醫院信息管理(HIS)系統,對上市后“真實世界”丹紅注射液臨床應用情況進行分析,發現丹紅注射液用藥療程在8-14天的患者最多,其次是4-7天、1-3天、15-20天及≧21天,并且治療冠心病的用藥時間較缺血性腦病的用藥時間短[4],為接下來干預時機研究設計提供了有價值的基線信息。
2.2 作用機制

圖2 中醫防治心梗介入圍手術期無復流的系統評價結果
干預時機的選擇最好有機制研究方面的依據。以中醫防治心梗介入圍手術期無復流研究為例。介入術后無復流是一個動態過程,涉及心肌腫脹、組織水腫、內皮破壞以及炎癥反應等多個病理生理機制[5],在不同階段的干預重點可能略有不同,因此將治療時間窗分為介入術前、術中及術后[6]。基礎實驗研究發現相關中成藥有緩解氧自由基和鈣超載導致的損傷[7],調節內皮一氧化氮合酶合成[8],減輕炎癥反應和血管收縮作用[9-11],預防性應用可減少血清粘附因子和促炎性細胞因子含量[12],直接或間接對再灌注后微循環功能產生影響。根據機制研究提示有側重的選擇干預時機,有助于明確藥物在關鍵作用環節上起效機制。
3 臨床試驗設計要點
3.1 結局指標設置
結局指標的設置要充分考慮研究目的和可行性。如果選用中間指標,那么是選擇臨床常用指標還是不常用但更精確的實驗室指標?指標對真實結局的代表性怎么樣?如何測量?選擇有創指標還是無創的可持續觀察的指標?研究成本和時間能否支撐?在研究干預時機的臨床試驗中,指標測量時間點的設置也非常關鍵,是采用同一時間截點,還是在治療后間隔相同長度的時間進行測量?都需要視具體情況考慮。
3.2 樣本量估算
樣本量估算需要注意組間效應值差異大小。干預時機研究中,因為應用同一種干預手段,只是干預時間先后有差別,因此主要結局指標的組間差異可能較小。如果直接進行比較,希望得出兩個時間點干預效果是否有差異的結論,則需要較大樣本量。然而,研究不同干預時點療效差異的前提是,應用該療法可能更有效,否則對什么時間點應用該療法的研究就沒有意義,因此需要增加一組對照,可以采用三臂試驗設計。
三臂試驗在樣本量計算時有兩種思路,分別對應兩種研究目的。第一種是三組間進行兩兩比較,如研究對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進行侵入性冠脈造影的最佳時機[13],按1∶1∶1的比例將患者隨機分為三組:直接冠脈造影組(隨機后2小時內給予)、早期冠脈造影組(隨機后10-48小時內給予)、選擇性冠脈造影組(視實際情況給予),研究希望評價直接冠脈造影是否優于早期或選擇性冠脈造影。該研究選用的主要指標為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的峰值,樣本量計算需要設定任意兩組間效應量差值的均值和標準差,應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獲得。另一種思路是兩個試驗組均與同一對照組比較,而兩組間不進行直接比較。如血栓抽吸后給予冠脈內注射腺苷或硝普鈉對預防PCI術后微循環障礙的研究[14],患者按1∶1∶1的比例被隨機分為三組:腺苷組、硝普鈉組、生理鹽水組,研究目的是評價血栓抽吸后冠脈內注射腺苷或硝普鈉是否優于單用血栓抽吸,主要結局指標是ST段回落率。樣本量估算采用兩樣本率的計算方法,即治療組與安慰劑組間的比較。
3.3 盲法設置
干預時機試驗的盲法比較復雜,需要在預設的兩個干預時點均進行干預,但只有一個時點給予真正的治療,另一個時點給予安慰劑。該方法多適用于藥物評價研究,對手法或手術干預難以實施,但這種情況下至少應給予盲態評價。在比較院前或院內給予替格瑞洛,對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冠脈再灌注效果的試驗中[15],患者知情同意后被隨機分配到兩組,一組院前給予替格瑞洛,院內給予安慰劑;另一組院前給予安慰劑,院內給予替格瑞洛,做到了雙盲,并且在指標評價時,將冠脈造影數據和心電圖記錄送到專業中心進行盲態判讀,使得結果更加客觀可信。
3.4 數據分析
試驗設計中的干預時機多指一個范圍,如入院前給予干預,那么患者實際接受干預則是在這個范圍內的不同時間點。對時間與療效數據的分析能否提供關于最佳干預時機的新提示?在病例報告表設計時注意使臨床研究者詳細記錄操作的具體時間,方便進行事后分析(post hoc analysis)。如在研究PCI術前給予300 mg負荷劑量的氯吡格雷能否減少終點事件發生的臨床試驗中,事后分析探尋氯吡格雷的最佳起始治療時間[16]。回歸分析顯示,與安慰劑組相比,氯吡格雷應用時間>15 h組可降低主要終點事件,提示越早的氯吡格雷負荷量使用,可帶來越大的臨床獲益。
4 結語
中醫強調時間醫學,認為治療時機與療效有密切聯系,而在中西醫療法聯合應用的時代,對如何選擇干預時機更是賦予了新的內涵,本文對干預時機臨床試驗要點的梳理只是針對治療-時間關聯研究中的一部分內容。通過開展中醫藥干預時機的循證優化研究,為指導中醫藥治療方案的臨床合理應用,提高中醫藥療法的臨床療效,優化資源配置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