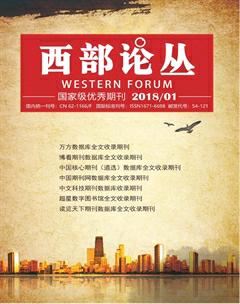從審美特征的角度探析二十世紀的西方女性文學
王小燕
【摘要】二十世紀是西方女性文學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西方女性文學成果更豐富,女作家更多,藝術水平更高。二十世紀是西方女性在繼承以往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開拓創新,使西方女性文學更加枝葉繁茂,本文試從審美特征的角度來探討二十世紀的西方女性文學,希望對西方女性文學的認識有所益處。
【關鍵詞】二十世紀 女性文學
二十世紀是西方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轉型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也是一個女性想象力得以馳騁的黃金時代,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女性文學產生的時期。在這個世紀里在婦女權益和生活狀況得到巨大提高的基礎上,西方女性文學傳統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婦女取得的多種成就顯耀在世人面前,婦女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從事作家、律師、醫生、政治,經濟、商業,創辦企業,寫作暢銷書,并相繼取得了選舉權、財產權、離婚后孩子的監護權。所謂的“婦女問題”也成為了二十世紀末想家們討論的主要議題。就西方女性文學的發展而言,二十世紀的西方女性文學不僅表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審美特征,而且,作家人數劇增,涌現了一批才華出眾、卓爾不群的女作家和許多經典作品。
一、性別意識與文化意識的交融
二十世紀尤其在后期是多元文化既交融又沖突的時代,性別意識與文化意識的交融是二十世紀西方女性文學的一個顯著的審美特征。對具有雙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的女性作家來說,由于對文化有特殊的敏感,她們對與本民族傳統文化不同的文化體驗似乎成了激發她們想像力的因素,因而能更加細致更加深刻地以自身的文化經歷和種族身份來表達不同的女性經驗。她們往往更能深切地感受文化交融與沖突所帶來的影響,她們的創作過程常常也成為尋找身份和發現自我的歷程。性別、代溝、文化間的沖突,邊緣身份的失落感,社會性別所屬的邊緣文化,少數民族的身份,是她們共同的創作主題。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她著名的文學論著《生存》中,她關注加拿大文化的獨立,發展加拿大自己的文學,她同時的關注點是婦女問題,振興加拿大獨立的民族精神。美國作家托尼·莫里森要向美國社會傳達黑人婦女的聲音,尋求美國黑人的文化之根,探索生活在充滿種族偏見的美國社會的黑人的喜怒哀樂,致力于為黑人創作。莫里森試圖再現廣大美國黑人的歷史和生存現狀,對美國的家庭關系、男女關系、女性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以關心黑人社會中的種種關系。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努力尋求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掙扎在統美國黑人文化與現代文明、黑人的信仰和白人的價值標準的矛盾與沖突中。美國華裔女作家是二十世紀的移民文化產生了許多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湯亭亭的《女勇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緣于作者及其作品中所展現的多元文化特質,她作為弱勢種族和邊緣文化的代表要向強勢種族和主流文化喊出自己的聲音。《女勇士》也反映了東方女性在主流白人社會中一直在進行的抗爭,描寫了東方女性在白人種族社會中所受的種族、性別的歧視,以及華裔女子在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中國家庭所受的歧視。另一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用“講故事”的敘事手法,以母女關系為主線,以作家本人母輩經歷為起點,描繪了母女兩代所代表的兩種文化之間相互沖突、相互融合的心靈歷程。他的《喜福會》使她能夠以獨特的生命體驗和視角,在兩個世界、兩種文化、兩個聲音、兩種語言之間,審視生命、關注存在,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為華裔作家提供了可以言說的素材以及富含隱喻的功能。
二、既反抗又依賴的語言膠著特征
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既反對“菲勒斯”中心話語,又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菲勒斯”中心話語,從而表現出~種“無能為力感”,這既是“女性的焦慮”。西方女權主義者為了反對男女“二元對立”的框架,又不至于落人“男女平等”而加深女性的“異化”,以寫作作為“對抗”的策略,但身處兩難的處境,事實上這是一種“話語”境遇里的“二律背反”。按照福柯的話語理論,所謂說話,歸根結底就是說話的權力。“話語”是一種壓迫和排斥的權力形式。話語又是權力爭奪的對象,一種特殊的對象。權力如果爭奪不到話語,它便不再是權力。話語與權力(不是狹義的“政權”,而是廣義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之間存在著復雜多樣的關系。這里女性主義的“兩難”境地既包含了上面所說的“話語”使用的尷尬境遇,也包含了更深層次的“二律背反”。
其一,女權主義強調“差異”的目的在于瓦解父權制表面上接納婦女而實際上把她們同化的策略,它是一種反策略,也是女權主義者建構女性文化的出發點。但是,強調差異的結果又落入了性別同一的窠臼,反性別歧視甚至導致了女權主義的性別歧視,最終使自己成為性別的囚徒。
其二,在揭露菲勒斯批評的偏見的同時,女權主義者也注意到了父權制的美學在女性身上的內化。婦女不但接受了支配群體對她們作為女人的界定,還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父權制美學對她們寫作的評價。當女作家由于陷入了劣勢,受到環境的限制,因而普遍表現出某種“閨閣習氣”或“神經官能癥”的混亂時,她們的作品正好加強和證實了支配群體對女性寫作的界定。“她們維持了男性的目光短淺,她們在用扭曲的形式為女性塑像的同時,也做了復制父權制秩幫手,正是在這些扭曲的形式中,男性投射了他們自己,連女作家本人也能覺察出這種形象的虛假性質”
二十世紀西方女性主義作家,其“語言的膠著”所產生的“焦慮”就更為深重。她們常常陷入一種窘境:因為“失語”,所以要“說話”,但那套“話語”既不是自己“民族”的母語,也不是“女性”的話語,更不是“女性者”的話語,但是,如果要生存,并且要有尊嚴地生存又必須“說話”,那么,用什么語言說話?這種兩難處境使她們甚至從創作角度對語言提出了質疑,同時也表達了作為作家不得不用語言來否定語言的承載能力時的窘境。事實上,這也是當代許多作家的窘境,他(她)們一方面認為語言不足以承載他(她)們所要表達的全部,然而他(她)們卻不得不使用語言來否定語言,用語言來贊美“無言的靜默”。盡管如此,二十世紀西方女性主義作家依然頑強地以其寫作實踐表明了“話語”的囚籠能夠被打破的“可能性”。
三、話語上以不定位來定位的特征
二十世紀西方女性作家的“以不定位來定位”的話語策略的基本涵義,它既有女性的內容,也有后現代的理論運用。在具體的文本寫作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靜默”主題
“靜默”既是二十世紀女性反抗這種規定的方式,也是社會性別角色或種族角色對二十世紀女性的規定。它連接著二十世紀所關注的語言、民族性問題,在二十世紀文本中具有特殊的隱喻意義,是許多二十世紀女性主義作品所熱衷表現的重心之一。
“靜默”是二十世紀女性“失語”的痛苦狀況。他(她)們不得不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為他(她)們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表述。非洲裔女作家努貝茜·菲利普在詩集《三文魚的勇氣》中指向了與失語緊密相連的種族與性別問題,其“靜默”的意象是通過“失語”表現出的。在另一部詩集《她用舌頭,輕輕打破了靜默》里,對無語的靜默的渴求實際上是對失語狀態下的痛苦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不得不在語言的使用中品嘗“異邦的痛苦”,由于喪失了真正的母語才不得不將父語作為母語,進一步從不同的方面和視角展示了“失語”的困境,即作為母語的語言并非真正的母語。菲利普在其詩化小說《尋找列文斯頓:靜默的奧德塞》中,作者所要強調的是,“人類現在使用的話語已經被污染了,它給人們帶來痛苦就像上帝施給人類為的懲罰,它帶有種族和性別的色彩。”作者在小說中表明:作為對這種失語的撫慰,作者開始尋求一種無語的靜默,由于是在有語言可用的情況下才產生的失語感,因此,不如回歸靜默。
在二十世紀女性文學作品中,不同的作者用“靜默”來表現不同的隱喻意義看,因為女主人公多是以沉默寡言的形象出現的。印度裔女作家阿妮塔·德塞,她筆下的女主人公的“靜默”主要用來展示一群類似“局外人”的流放者,因為她早期的小說受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較深,這是由于自幼生長在印度,后多年在美國和英國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小說《城市的聲音》中的女主人公莫尼莎選擇了孤獨,她覺得只有在靜靜的孤獨中她的心智才是自由的,選擇了在“靜默”中自我流放。她直到最后選擇死亡這一無聲的舉動來對世界提出她的反抗,她始終躲在自己內心的監獄里,總是用一種冷漠的、靜默的、反叛的態度對待這個世界。死亡后的她本身是“靜默”的。作品的意義在于用表現“靜默”來打破“靜默”
(二)對口頭文學形式的運用
作家對于過去和口頭傳統的使用不僅僅是一種懷舊,借口頭傳統使得它更加契合二十世紀現實。凱圖·卡特拉克在其《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種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論》一文中指出:“對口頭文學傳統的運用,其本身是非殖民進程中的一個戰略戰術。婦女作家在運用傳統形式以及徹底修正諸如小說、短篇故事和戲劇的形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找到了適合后殖民歷史時空特征的新的文學形式——比如,口頭證詞就是現代書面短篇故事的基礎;民間的儀式形式是現代戲劇的基礎;諺語、謎語、歷史事件的用于現代書面長篇小說。”加納女作家阿瑪·阿達·艾杜在她的短篇小說和戲劇中就有意地使用口語傳統。其短篇小說集《這里沒有甜蜜》里對口頭故事講述中的呼喚和應答模式以及對話和戲劇傳統的運用尤為突出。牙買加“姐妹團”的作品最好地說明了她們對民間故事、儀式和個人證詞為基礎的戲劇和短篇小說等文學形式的修正。作為姐妹團的書面小說《獅心女郎:牙買加婦女的日常生活》的基礎,就是口頭傳統的一部分。《獅心女郎》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它將口語形式和書面形式結合起來。15個故事中,有13個都是基于工人階層婦女的日常語言的口頭證詞和采訪記錄。這些小說非常有效地消除了婦女作為生育的母親和浪漫的農村生活的代表的神秘性,也消除了她們在性別和暴力方面的神秘性。“所有的證詞,都因為有了從少女到成人、從鄉村到城市、從孤立的個人經驗到更為政治化的集體意識的過渡而得到了強調。”在姐妹團運用的故事傳統中,在她們的戲劇中使用的非洲儀式中,在借鑒口語傳統中的人物形象中,她們“發現了文化當中許多強有力的東西。語言和文化形式成了抵抗新殖民主義思潮、抵抗壓迫婦女之權力的有效工具”。
(三)文體的越界與混雜
所謂文體的越界與混雜,主要是指“邊緣交叉的文本,將不同類型的體裁、風格、語義、表現手法混淆在一起,重組一種新的文本二十世紀西方女性主義作品通常表現“體裁的越界”或體裁混雜的特征。加勒比海黑人女作家、后移民加拿大的黛奧尼·布蘭德把敘事和詩歌混雜在一起,試圖跨越題材的界限,挑戰所謂“高雅的文化”。評論家說:“布蘭德的詩是史書、是政論,布蘭德的小說則是詩,其詩歌《充滿敵意的太陽編年史》更多地依靠各種人物對歷史的評述、見證、實錄等來構建敘述語言和整部詩篇的結構;而她的小說則有厚重的歷史感但又非常注重小說的寫作技巧,短篇小說集《逍遙》不僅按歷史發展的時間進程編排小說順序,且在文體風格上表現出“越界”特征:其中《圣瑪麗的房子》和《照片》是兩篇在內容上相關的回憶錄式的小說,同名小說《逍遙》用詩話的語言、細膩的描繪、舒緩的節奏來敘述故事。魯斯·普拉瓦·杰哈布瓦拉是德裔猶太人,后定居印度。在她的內心,深切地感受到東西方兩種文化撞擊所產生的壓力。于是她在創作中宣泄這種心理壓力,她的《炎熱和土地》借鑒了古典小說的技巧,在敘述中穿插了摘錄日記和書信的引文,但小說的整體構思確是電影式的。
總而言之,從審美特征上看,二十世紀的西方女性文學呈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其內容從歷史到現狀,從精神到身體,無所不及;其形式,從風格到題材,可謂多元并陳,色彩各異。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精神風貌,也向我們展示了二十世紀西方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與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