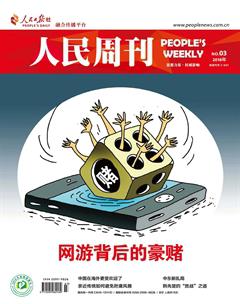中印“冷和平”打破之后
張家棟
2017年,在外交方面,印度與美國(guó)、日本的外交關(guān)系繼續(xù)推進(jìn),對(duì)華政策也一反常規(guī),通過(guò)一次洞朗對(duì)峙事件展示了印度的強(qiáng)勢(shì)外交政策。
印度外交正在快速轉(zhuǎn)型
印度外交正快速遠(yuǎn)離不結(jié)盟外交傳統(tǒng)。在雙邊層面,印度促進(jìn)了與美國(guó)、日本等國(guó)家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是在政治和軍事領(lǐng)域的關(guān)系。印度對(duì)外政策與美國(guó)對(duì)外政策的相似性在提高。莫迪訪問(wèn)以色列,與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發(fā)生在同一年,表明印度在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選邊站的清晰立場(chǎng)。
周邊安全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印度的主要目標(biāo)。印度新政府則更是打著“周邊優(yōu)先”的旗號(hào)上臺(tái)的。除了大國(guó)外交以外,印度幾年來(lái)的外交動(dòng)作是由近逐漸及遠(yuǎn)的模式:2014年的外交重點(diǎn)是南亞鄰國(guó),2015年是印度洋地區(qū)國(guó)家,2016年的外交重點(diǎn)是中東和波斯灣地區(qū)。
印度的外交收獲,主要在印度洋地區(qū)和國(guó)際舞臺(tái)上。印度在印度洋地區(qū)的合作機(jī)制建設(shè)也穩(wěn)步推進(jìn),一些以印度為中心的地區(qū)和次地區(qū)合作機(jī)制繼續(xù)推進(jìn)。在美歐日的支持下,印度在國(guó)際舞臺(tái)上也有收獲。2016年底,印度加入導(dǎo)彈計(jì)劃控制機(jī)制(MTCR)。2017年12月8日,印度加入瓦森納安排(WA)。這表明印度融入西方秩序的速度在加快。
但是,印度外交有得有失。隨著印度外交重點(diǎn)的不斷轉(zhuǎn)移,最先拿起的往往也先被丟下。到2017年,印度在南亞國(guó)家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大多喪失:尼泊爾剛剛結(jié)束的大選結(jié)果已表明印度對(duì)尼泊爾政策的階段性失敗;印巴關(guān)系惡化,中印關(guān)系惡化;斯里蘭卡西里塞納政府在觀望一段時(shí)間后,也正式與中國(guó)簽訂了港口租讓協(xié)議。印度在抵制南盟以后,轉(zhuǎn)而推動(dòng)BBIN倡議,但由于不丹議會(huì)的否決而沒能正式生效。這表明印度以文化軟實(shí)力和國(guó)家潛能為基礎(chǔ)的外交政策,得不到硬實(shí)力支持,很難轉(zhuǎn)化為真正的外交優(yōu)勢(shì)。
中印關(guān)系面臨著嚴(yán)峻挑戰(zhàn)
2017年是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lái),中印關(guān)系最為困難的一年。1962年中印邊境武裝沖突以來(lái),中印關(guān)系基本是一種“冷和平”狀態(tài)。但是在2017年,中印關(guān)系基本被“冷對(duì)抗”所取代,中印在戰(zhàn)略層面直接對(duì)撞的風(fēng)險(xiǎn)上升。
一是,印度對(duì)“一帶一路”倡議的態(tài)度更加明確,從以前的消極觀望發(fā)展到直接反對(duì)并提出對(duì)應(yīng)性倡議。2017年5月,印度成為大國(guó)中唯一缺席“一帶一路”全球合作論壇的主要國(guó)家,并提出一些沒有中國(guó)參與的地區(qū)聯(lián)通倡議,如2017年印度與日本合作推出的亞非增長(zhǎng)走廊(AAGC)計(jì)劃。
二是,中印洞朗對(duì)峙事件提示了中印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和敏感性。這起對(duì)峙事件在中印兩國(guó)間的類似事件中,規(guī)模不是最大的,時(shí)間不是最長(zhǎng)的,代價(jià)也不是最大的,但影響卻是最大的。這是中印之間第一次在非兩國(guó)爭(zhēng)議領(lǐng)域的對(duì)峙,對(duì)中印關(guān)系造成的損害和風(fēng)險(xiǎn),如何強(qiáng)調(diào)都不過(guò)分。這為未來(lái)類似事件以及升級(jí)提供了心理可能性。對(duì)峙雖然和平結(jié)束,但如兩國(guó)處理不當(dāng),在未來(lái)擦槍走火甚至是發(fā)生一定程度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反而上升了。
三是,中印兩國(guó)在印度洋地區(qū)的競(jìng)爭(zhēng)態(tài)勢(shì)日益明顯。在印度洋上,為了應(yīng)對(duì)“地區(qū)外國(guó)家保持近乎長(zhǎng)期的駐軍”的趨勢(shì),印度海軍把12~15艘“任務(wù)待命軍艦”長(zhǎng)期部署在印度洋北部各咽喉點(diǎn)和關(guān)鍵海上通道上,還得到海軍“魯克米尼衛(wèi)星”(GSAT-7)和P-8I海神偵察機(jī)的支援。印度還于11月召開首次由10個(gè)印度洋沿岸國(guó)家參加的果阿海帶會(huì)議(GMC),加強(qiáng)于地區(qū)內(nèi)國(guó)家在海上情報(bào)交流等領(lǐng)域的合作。
總體來(lái)看,2017年見證了中印“冷和平”狀態(tài)本身所包含的風(fēng)險(xiǎn)與危機(jī)。冷和平狀態(tài)可以長(zhǎng)期在中印關(guān)系中有效存在,是因?yàn)檫^(guò)去兩國(guó)的能力和國(guó)際地位有限,既被喜馬拉雅山在地理上隔離,也都沒有進(jìn)入國(guó)際政治的中心地帶,相遇甚少。但是現(xiàn)在,一些新的因素出現(xiàn)了:中印兩國(guó)加強(qiáng)對(duì)邊境地區(qū)控制的能力和意愿同時(shí)上升,使得邊境爭(zhēng)端更難管控;兩國(guó)國(guó)際地位的提高,使得兩國(guó)在國(guó)際公域中相遇的頻率上升,戰(zhàn)略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更加復(fù)雜;隨著印度發(fā)展制造業(yè)的愿望上升,兩國(guó)貿(mào)易不平衡問(wèn)題更易影響民意;隨著新媒體的出現(xiàn),兩國(guó)民眾參與外交事務(wù)的門檻下降,雙邊關(guān)系更易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
中印兩國(guó)同時(shí)崛起,在多邊、地區(qū)和國(guó)際層面相遇的機(jī)會(huì)越來(lái)越多。這意味著傳統(tǒng)的通過(guò)保持距離以維持和平與穩(wěn)定的模式,將很難持續(xù);繼續(xù)發(fā)展人文與經(jīng)貿(mào)聯(lián)系但繼續(xù)在政治和軍事領(lǐng)域低調(diào)的平行外交模式,雖然在目前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選擇,但是也將面臨更多的挑戰(zhàn)。
在“亞洲世紀(jì)”的共同愿景下,中印關(guān)系已經(jīng)到了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要么為中印關(guān)系尋找到一個(gè)適合的定位與機(jī)制性安排,要么讓中印關(guān)系成為兩國(guó)可持續(xù)崛起的負(fù)擔(dān)。中印提前到來(lái)的“龍象之爭(zhēng)”,對(duì)兩國(guó)尤其是對(duì)印度的發(fā)展前景構(gòu)成了新的不確定性。
(作者為復(fù)旦大學(xué)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