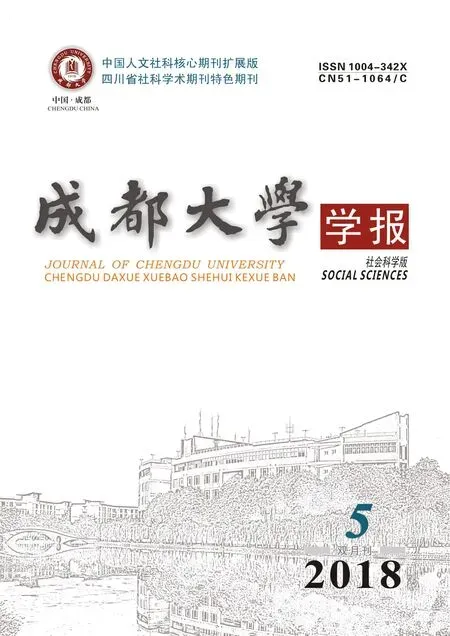論君子文化的時代內涵*
程碧英
(四川文理學院, 四川 達州 635000)
君子文化源于先秦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價值理念,君子文化集中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集聚的精神力量,受到了歷代思想家的廣泛推崇。從漢至清,董仲舒、孔穎達、朱熹、王陽明、王夫之、梁啟超等都對經典文獻中的君子文化進行了考辨詮釋。后來學者進一步繼承發揮,張岱年、余英時、樓宇烈、葛榮晉、劉述先、楊國榮、陳俊明、趙敏俐、王宏亮、任福申、李長泰等從哲學、文獻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傳播學等角度對君子文化進行了廣泛研究和學術審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光明日報》陸續推出錢念孫、王小錫、劉寶蒞、楊朝明、朱萬曙、蔣國保、何善蒙、王鈞林、盧風、張述存、孫欽香等學者的“君子文化”主題文章,并就君子文化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與踐行進行了充分辨證。同時,浙江大學、安徽省社科院、江蘇省社科院、湖南省等分別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中心,目前已舉辦三屆全國性君子文化論壇。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歷經歲月沉淀而又常說常新的君子文化如何順應時代需求煥發生機,如何進入現代公共文化視野,如何實現文化正能量的價值引領,需要我們結合歷史語境與現代語義分析君子文化的語義生成,充分挖掘君子文化的時代內涵,以進一步明確君子文化價值定位,實現君子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君子文化的語義生成
“君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符號。李飛躍《“君子”義繹》一文指出,“君子”一詞“源起甚早,貫通古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形態中起著重要作用,對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產生了深遠影響”[1]。具體說來,“君子”最早見于《尚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其后多見于儒家經典。考察君子詞義的歷史演變,余英時認為,“‘君子'之逐漸從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質的內涵自然是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開始, 但卻完成在孔子手里。"[2]就“君子”詞義何以如此變化的緣由,蕭公權指出,“君子舊義是‘就位以修德’,新意為‘修德以取位’,孔子推陳出新,提出新的君子人格,反映了孔子改革社會文化及政治的信念,即‘為救周政尚文之弊’。”[3]
自此以后,君子詞義逐漸穩定,這為“君子文化”這一概念的形成奠定了語義基礎。筆者認為,“君子文化”是一個集體概念,是以“君子”語義元素為基礎,在其發展過程中吸收眾家文化所長而成。從歷史語境與現代語義角度分析,君子文化是眾多文化元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廣義文化范疇,經由歷史發展,涵蓋了由“君子”語義所生成的眾多文化概念,如君子理想、君子德行、君子精神、君子修養、君子品格、君子作風、君子治國理念、君子人文教育等,既關涉君子語義生成的文化淵源,也包含君子文化演變的歷史經驗。
二、君子文化的時代內涵
挖掘君子文化的時代內涵,自然離不開對《論語》的關注。在《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頻次高達一百零七次,從首章《學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4]到末章《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4],可謂相互呼應,貫穿始終。“君子”的高頻次出現不是偶然,而是真實表達了孔子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和教育講學的使命。馮友蘭認為,孔子是教育家,“他講學的目的,在于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之人,并不在于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書,學各種功課。”[5]可以說,從周游列國的失意中歸來的孔子,培養君子以改變“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成為了他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美國漢學家郝大維、安樂哲在《通過孔子而思》一書中對“作為典范的君子”進行過如此評述,“個人修身必然包含對家庭和社會政治秩序的積極參與,不僅僅是為他人服務,而且是利用這些場合喚起同情和關懷,以利于個人的成長和完善”[6],所以,“對孔子來說,君子是一個質的術語,表明一個不斷致力于個人發展的人,其成長過程通過修身和社會政治領導能力展現的。”[7]
綜上我們不難理解,當孔子將興辦教育的出發點與歸宿集中在讀書人群體如何實現成為君子這一目標時,讀書人自然成為了實踐君子文化的主體。也就是說,君子文化語義所指正逐漸由享有特權的精英階層轉化為讀書人這一大眾群體。自此以后,君子文化涵養了一代代讀書人心憂天下的人生情懷和責任擔當。走入現代生活,君子文化豐富的時代內涵得以凸顯。
(一)家國情懷
君子文化與家國情懷的語境表達,在《論語·憲問》篇中有如此記載,子路問老師如何成為君子,孔子通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層層推進的方式回答了子路的提問,我們也豁然開朗于孔子對君子責任的建構。《禮記·大學》所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順序,也正是讀書人家國情懷的充分表達。
可以說,家國情懷是自古以來讀書人心憂天下的情感表達,也是讀書人實現自我的實踐力量。當孔子孜孜以求追尋“天下歸仁”的社會理想時,弟子曾子不由感嘆讀書人任重道遠,《論語·泰伯》篇記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在這種精神的引領下,孟子道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感慨;屈原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感嘆;范仲淹展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張載明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蘇軾提出“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的警戒;鄭板橋抒懷“衙齋臥聽簫簫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擔當;左宗棠書寫“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的情懷。
在生活中,我們常把“做君子”作為自身的價值追求,甚至人生目標。這其中所表達的詞義內涵,自然有著屬于我們當代人應有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擔當,這無疑也是家國情懷的現代表達。于丹《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轉換》一文中指出,“當談到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轉化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坐標系,即我們是站在當下去激活傳統文化中的文化基因,而并非讓傳統文化全面統轄當下,我們不走復古的路,我們也不會泥古不化。”[8]因此,當家國情懷成為群體文化追求時,現實語境便變得鮮活可期。
當君子文化走出歷史語境對話現實生活,家國情懷便超越宗族譜系而走入現代人的精神空間,文化的力量由此變得溫潤而非支離破碎。因此,家國情懷表達的是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與天下百姓同衷共濟,與時代脈搏緊密相依。君子文化家國情懷的表達,既高揚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追求,更是“常懷愛民之心、常思興國之道、常念復興之志”的責任書寫。
(二)道德遵循
陸建德《文學中的倫理:可貴的細節》一文中指出,“倫理是發展變化的,深深嵌陷在一定的歷史過程、社會場域中,不能用絕對的、靜止的觀念來看待。”[9]對于君子文化而言,在表達倫理觀念語義上也的確如此。如上文所言,君子文化的語義表達除了關乎社會責任與人生使命的宏觀敘述外,隨著漢以后君子文化詞義的逐漸穩定,君子文化在倫理道德、人格修為等語義領域的表達也逐漸穩固。
其一,以仁存心。孔子訓導弟子,尤其強調“仁”德的重要。《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關于“仁”,《論語·陽貨》篇記載弟子子張就此請教老師,孔子如此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進而言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還提出“仁者不憂”“為仁由己”“天下歸仁”等話題,皆說明“仁”這一道德遵循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與獲得的強大的社會價值。
到了孟子那里更是提出:“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10]故此,“仁者愛人”流行于后世,也被當作道德遵循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視野。
其二,義以為質。孔子講“義”在《論語》中多見。《論語·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衛靈公》“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熹《四書集注》言:“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干。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11]除此外,《論語》中還提出“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見得思義”等命題,用我們現在的話說,“義”就是自身行為規范,而“仁”是與他人形成的社會關系。
在其后的文化發展中,便有“舍身取義”“從容就義”“大義凜然”“多情多義”“仗義執言”等說,“義”成為了一種重要的道德責任。涂可國《儒家之“義”的責任道德意蘊》一文中指出,“儒學所闡發的責任倫理既包含意圖倫理或義務倫理又包含結果倫理,但它又區別于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功利主義。”[12]
其三,博文約禮。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是作為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而加以存在,其背后是強大的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為仁”,《論語·八佾》“禮,與其奢也,寧儉。”在后來的禮制文化發展中,“禮義廉恥”“禮賢下士”“以禮相待”“知書達禮”“彬彬有禮”“讓禮一寸,得禮一尺”等說無疑豐富了其內涵。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禮文化進入人們生活視野的是關于典章制度和禮儀規范的遵守,實現禮儀文化的傳承和儀式感的延伸。
因此,歷代君子通過“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積淀有完備的知識儲備和完善的道德遵循,剛毅進取、坦蕩中和,自然成為了歷代人們追慕的道德典范和人格范式。這對我們當前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為著力點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啟示作用。同時,君子文化也是促進公民素質教育的重要載體,在對傳統君子文化的現代轉換過程中,建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君子文化教育機制,為國民素質教育、思想道德建設和家風家教家訓傳承提供范式參考,為當今思想政治教育、黨風廉政建設等提供可操作之法,亦可為加強和完善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提供決策參考。
(三)人格力量
當君子文化走過歷史演變,回歸到現實社會語境中時,我們不難理解君子文化成為了高尚的人格力量的代名詞。李翔海在《生生和諧——重讀孔子》一書中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在傳統社會中通過科舉考試與官吏選拔制度,成為整個社會知識精英階層的人格典范。與此同時,通過意識形態的作用,以及知識精英階層的影響,君子人格還進而成為全社會景仰、信從的人格規范。”[13]裘士京、孔讀云在《論語君子觀及其現代啟示》中指出:“《論語》中的君子是孔子對周代貴族所崇尚的君子人格的重新闡釋和再次規定,是歷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為境界。”[14]這些說法是有見地的。如今,置身新的時代,當君子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概念被論及,其詞義所指已跨越知識精英階層而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精神得到倡導,表達的不再是單一維度的道德君子范型,而是立體多維的積極進取的人生存在方式。
因此,遵循“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規律,在高揚仁愛崇禮、誠實守信、公平正義、敬老愛親、謙遜友善、淡泊寧靜等人格力量基礎上,積極構建文化認同、轉化發展和協同創新機制,按照“大眾化、常態化、生活化”原則,通過教育引導、平臺傳播和實踐養成等方式實現君子文化的現代轉化和傳承發展。
三、結語
君子文化所構建的思想價值體系,不能只是抽象的存在,而應滲透在日常生活與一言一行中。陸建德指出:“心靈接受價值必須是主動積極的,價值或信仰內化以后就變成生命的熱量,行為的動力,而不是一種撐門面的標榜。”[15]因此,君子文化的各大范疇既獨自存在,又相互關聯。理論建構的可貴之處在于,超越支離破碎而渾然一體,走出歷史語境而對話現實。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成為君子并非可望不可及,而是我們每一個社會公民通過努力都可以承擔的社會責任,可以達到的人生境界,從而實現從個體修為到集體人格的成長。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做好君子文化的現代轉換過程中,君子文化的創新性發展也是隨之而來的重要話題。因此,當君子文化以昂揚的姿態進入我們現代生活的道德修為、公共價值、文化實踐時,君子文化的現代轉化和創新發展也就得到了最大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