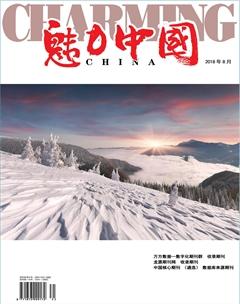論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及其現實意義
摘要: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主要是指主體間通過語言的溝通和交流,求的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為。生活世界作為主體間進行交往活動的背景,它的結構在現代社會遭到嚴重破壞,即產生所謂殖民化問題。哈貝馬斯試圖通過實現交往合理性為生活世界殖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出路,交往合理性就是要尋求交往行為的合理根據,這個根據主要是交往主體間普遍認同和遵循的規范,實現交往合理性還需要交往主體選擇合適的語言、開展有效的對話活動。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把語言作為達到理解和共識的中介,提過重新界定理性,將交往理性從理論層面擴展到實踐層面, 為解決交往異化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交往合理性;借鑒意義
一、交往行為概念及其合理性
交往行為概念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范疇,哈貝馬斯指出“交往行為總是要求一種在原理上是合理的解釋”。在《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中,哈貝馬斯把社會行為區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目的性行為,它是行為者權衡各種手段并選擇一種最理想的達到目標的手段,比如,“勞動”就是這種工具性的“目的—手段”式的行動;第二類是規范調節的行為,這種行為一般只能發生在一個受共同價值約束的群體內,群體內各成員以群體的共同價值規范作為行為的取向,規范嚴格控制行為并滿足“普遍化的行動要求”;第三類是戲劇性行為, 這種行為重在表現自己,“行動者在他的觀眾面前,以一定方式進行自我表述……想讓觀眾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和接受到自己的東西”; 第四類是交往性行為, 即行為主體之間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的符號相互協調,通過對話達到行動上的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為的核心。哈貝馬斯認為,在上述四種類型的行為中,只有交往行為是最為合理的,因為交往行為較之于其他三種行為來說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哈貝馬斯把“世界”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即 “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即“外部世界”、“客體世界”;“社會世界”即合法化的個人關系的“總體”;“主觀世界”是人的自發的經歷總匯成的世界。在上述四種類型的行為中,只有交往行為作為不同主體間的關系是在主體與“客觀世界”、主體與“社會世界”、主體與“主觀世界”三種關系的背景下發生的,交往行為相對于其他幾種行為而言,吸收了其他三種行為的優點,是一種世界性的、多方位的行為, 本質上更具有合理性,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組成的世界稱為“生活世界”。
二、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源自于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格爾的解釋學。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運作于生活世界之內,生活世界是主體間從事交往活動的歷史舞臺,“它不是行為者與三個世界中的任何一個世界的關系,而只是行為者之間通過對三個世界的解釋而達致相互理解,取得一致意見的關系”,“可以把生活世界的概念首先作為理解過程的關系而引入進來”。生活世界包括三個層次即文化、社會、個體, 這三個層次相互聯結, 形成一個復雜的意義關系網,是交往行為者的“信念儲存庫”,“信念儲存庫”就是它為交往行為主體在交往互動中提供思想“信念”的源泉。在這三個層次中,文化知識以符號形式體現出來———體現在使用對象和工藝中、體現在格言和理論中、體現在書籍和文件中(還不少于體現于行為中); 社會體現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規范或規范調整的實踐活動和使用的交織物中; 個性結構體現在人的有機體的根基中。由此看出,生活世界的本質是由知識構成的, 交往主體通過共同的生活世界理解和表達存在于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的事物。系統是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它是一種技術性的事物,是物質再生產總體的總稱, 如社會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和系統的雙重發展推動著社會的進化,一方面,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系統一體化的新的機制組織化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隨著生活方面理性化的發展,不同社會成員間不協調的因素也越來越多,這就造成西方社會生活世界與系統嚴重分化甚至脫節,于是產生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由于技術、科學及一些中介性媒介造成物質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當這些中介因素(如金錢、權力)進一步滲入到政治、經濟和家庭關系中從而造成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受到嚴重侵占, 抵消了生活世界對于社會整合應起的作用。正如哈貝馬斯所說:“自主的子系統的要求從外滲入生活世界,就好像殖民主義者侵入一個部落社會,并強迫其同化。”
三、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路徑選擇
怎樣解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問題呢? 哈貝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這一解決辦法,他認為只有實現交往合理性,使理性在社會生活中變為現實,在與目的合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統借助金錢和權力媒介對生活世界的侵蝕,才能使人們的生活世界走向合理性。哈貝馬斯試圖借助團結和正義進行自由的交往與對話來建立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首先、交往主體要建立一套規范準則,承認和重視一定的規范準則才能有效地達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才能順利地開展對話與交流。這些規范準則影響和約束交往主體的行為, 便于維持正常的社會關系。哈貝馬斯強調規范的普遍性,他說:“每個有效的規范都必須滿足如下條件, 即那些自身從普遍遵循這種規 范對滿足每個個別方面的意趨預先可計產生的結果與附帶效果,都能夠為一切有關的人不經強制地加以接受。”這里的普遍性有效規范必須是大家都能自愿接受的,“普遍性”是與商談和論證結合在一起的,要通過商談和論證,容許一切參與者發同的見解并最終找到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的觀點,規范準 則是人們相互理解的重要基礎。其次、交往主體應選擇合適的語言。哈貝馬斯認為: “我把交往行為視為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行為, 在那里所有行為者都致力于調節他們的交往行為,都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并且只追求這些目的 ”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成了促成“交往合理化”的關鍵因素,有交往行為的地方就會有語言的出現,語言行為受阻或被 歪曲的地方便不會有合理的交往行為。交往對話的時候,交往雙方必須選擇一種能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正確的語言表達自己。哈貝馬斯認為:“把語言理解成所有社會制度都得依賴的一種元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社會行為形成于日常的語言交往中。”他把交往行為變成了交往主體通過符號協調的相互作用, 是以語言為中介的主體間的溝通,他進而指出“語言運用中的四種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 保證了語言理解的主體間性,體現了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結構的理性內涵。”這說明在交往過程中,主體要盡量滿足這“四種有效性要求”,才能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再次、交往主體應開展對話活動。對話是人們達成共識最有效的方法,對話就是交往,只有在對話中,交往主體的利益才能被充分考慮到, 交往雙方提出的各種要求都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在民主、平等、和諧的氣氛中,人們能在沒有任何外來的強加的壓力下充分論證各自的觀點, 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話語的所有潛在參與者均有同等參與話語論證的權利, 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發表任何意見或對任何意見表示反對,可以提出質疑或反駁質疑”、“所有話語參與者都有同等權利作出解釋、主張、建議和論證,并對話語的有效性規范提出疑問、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對、任何方式的論證或批評都不應遭到壓制。”這樣交往主體在討論和論證的過程中, 都獲得了“機會均等”的權力。只有保證交往主體享有平等、自由的話語權利才能擯棄權力濫用而壓制話語民主的做法、才能通過交流與對話達到相互理解、才能克服“生活世界”與“系統”間的裂痕而導致生活世界“殖民化”(如生活世界的商品化、金錢化、官僚化)的趨向,實現社會的公正與平等。
四、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現實意義
哈貝馬斯批判繼承了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他認為語言是最基本的交往媒介,語言符號系統在交往行為以及社會進化中起著重要作用,通過語言的交往可以達到相互理解、行為合理化和普遍的共識,并以此來整合社會。雖然這一方法帶有濃厚的解釋學色彩,但這一思維視角非常獨特,拓展和加深了對語言問題的研究。交往行動是交往主體借助一定的交往媒介開展的活動, 這其中必然涉及到人們共同理解和接受的感性中介系統———語言符號系統的作用,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語言符號系統是人類改造外部世界的重要中介,通過語言符號系統有利于實現交往主體在思想、情感、信息上的溝通和對交往活動本身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作是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媒介,在溝通過程中,言語者和聽眾同時從他們的生活世界出發,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以及主觀世界發生關聯,以求進入一個共同的語境”,“交往行為模式貫穿于由米德的符號互動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概念、奧斯汀的言語行為概念以及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等共同開創的不同的社會科學傳統, 并且充分注意到了語言的各種不同功能。”馬克思也認為“從事物物交換和互通有無的傾向……是運用理性和語言的結果”。哈貝馬斯還深入研究了語言交往的種類與規模、言語行為的可能理解性的先決條件及其有效性基礎,他的這種對交往問題的語言學轉向對于實現“文化體系的合理化”也具有重要價值。
話語(商談)倫理學在哈貝馬斯的交往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哈貝馬斯試圖通過話語倫理學的建構完成交往理論體系的論證,將交往理性從理論層面擴展到實踐層面,進而尋求解決交往異化的新思路。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學體現了普遍化原則、論證性原則和交互主體性原則的結合。普遍化原則即“每個有效的規范都必須滿足如下條件,即那些自身從普遍遵循這種規范對滿足每個個別方面的意趨預先可計產生的結果與附帶效果,都能夠為一切有關的人不經強制地加以接受。”也就是說在理性基礎上建立的有效的規范和道德命令能代表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意志和利益,能為大家自愿地接受和遵循。普遍化原則體現了哈貝馬斯對康德的絕對命令(內心的道德規則)的改造。哈貝馬斯認為論證在話語倫理學中具有無可否認的必然性,從交往的前提和規范中可以歸納出普遍化原則。人們在進行話語商談時必然有意或無意地承認和接受各種“先驗性的”前提,因而會以各種方式遵循一些行為規范的要求,這其中也必定包括理智論證的過程。哈貝馬斯把倫理原則的普遍認同看作是一個共同論證的過程,人們通過相互商談將各方提出的意志進行充分的討論最后確定共同認同的普遍的規范。哈貝馬斯強調了商談過程的相互性即交互主體性,由于每個人都會意識到自己具有充分的理性思維能力和交往能力,其他人也是如此,因此相互之間就會平等商談, 通過商談和對話形成共識,人們出于理性通過商談論證創立了普遍的道德準則,即“普適主義的道德”,人們也就自覺地接受道德律令和社會規范的指導,并通過接受指導而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哈貝馬斯話語倫理學的這種主張用普適主義的精神和平等對話的方式來解決不同文化間的沖突的療法為解決交往異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為探討與人類和世界未來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開辟了新的思維視角。
參考文獻:
[1]劉偉. 先驗性與經驗性的融合: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實質[J].理論探索,2016,(05):29-33.
[2]單麗娟.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研究[J]. 世紀橋,2012,(23):29-30.
[3]方明豪,李玉媛.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視閾下的微博輿論的理想言談情境[J].文化學刊,2012,(03):73-76.
[4]周博.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及其啟示[J]. 沈陽大學學報,2010,(06):106-108.
[5]韓小榮.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簡析[J]. 勝利油田黨校學報,2010,(05):21-23.
[6]繆赤彤.略論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及其借鑒意義[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1):290-292.
[7]洪波. 論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建構[J]. 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1):20-24.
[8]張方政.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德育意義[J]. 宜賓學院學報,2006,(02):112-114.
作者簡介:韓旭,女,1993年1月12日,工作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學位職稱: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及專業: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