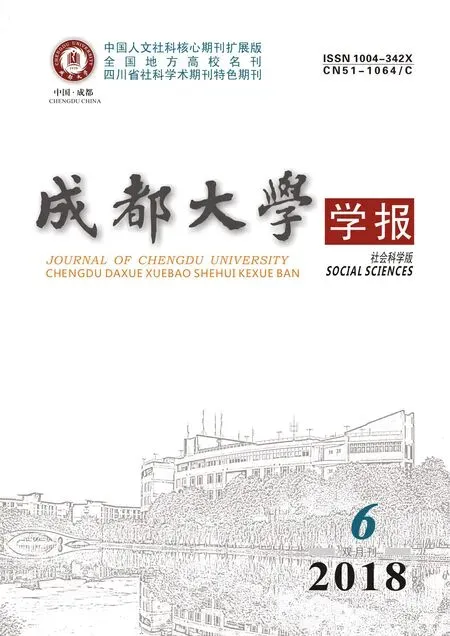日常生活還原與重構:“民國文學”想象芻議*
關 峰
(西北大學 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7)
“民國文學”的提出既是學科自覺和反思的結果,也是世紀之交社會、文化思潮和心理的體現。在陳福康提議“退休”[1]3和張福貴主張“時間概念”[2]6之際,無獨有偶,陶東風也在《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上撰文呼吁文藝學學科反思,批評“文藝學研究與公共領域、社會現實生活之間曾經擁有的積極而活躍的關系正在松懈乃至喪失”,以為知識生產“不能積極有效地介入當下的社會文化與審美/藝術活動,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藝術活動,尤其是大眾的日常文化/藝術生產與消費活動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陳福康之所以不滿“現代文學”的現名,主要是圈外人“幾乎誰都不懂‘現代文學’指的是什么”,用來“很不方便”。[1]3張福貴則表示,“民國文學”作為時間概念具有多元性、中間性和歷史的慣性,強調時間的方式“能最大限度的保持文學史的完整性因而不會被某種‘意義’所限定”[3]314。綜合來看,上述三位研究者的求變初衷都有日常生活的要義在:或者打破故步自封局面,打通日常生活現場;或者回歸慣例和常識,重構日常生活空間。到目前為止,“民國文學”的熱議已基本告一段落。在此基礎上,冷靜的審視與理性的體察或者已有必要和可能。本文擬就此生發,聊以芹獻罷了。
一、“民國文學”生產及其日常生活語境
正如新文學、現代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生產一樣,“民國文學”的發起也源于社會與歷史語境交互作用的“匯集”。開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并沒有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的轉折點上受到阻遏,反以“世紀末”和千禧年的不同方式展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其表現就是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經濟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此寬松而又極具活力的氛圍之中,學術研究和討論也變得活潑而有生氣起來。事實上,與20世紀50-70年代宏大史詩的“神話”相比,經過80年代的過渡,到90年代似已開啟了一個日常生活的新時代。不同于政治與革命的意識形態建構,日常生活意在表達相對寬泛而開放的立體空間與多維范式。以后現代理論為例,自杰姆遜1985年到北京大學講學,出版《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一書以來,后現代就大有超越現代之勢。比較而言,“就是后現代以其多元化對抗現代的一元化,以差異對抗同一,以相對主義對抗絕對主義,以地方性對抗普遍性……”[4]60。后現代的取向和追求未嘗不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姿態和方式。社會結構中的日常生活層面成為最大多數人事的“協商”之地。“民國文學”的發動和策劃或可視為日常生活諸文化元素合力催生的事件。實際上,李怡提出的“國家歷史情態”與“民國文學機制”概念也都鮮明地打上了日常生活的烙印。在李怡的“詞典”中,“國家歷史情態”“除了國家的政治形態之外,還包括社會法律形態、經濟方式、教育體制、宗教形態和日常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的生產、傳播過程等”[5]66。而在有關“民國機制”的答問中,他也表示“‘民國機制’就是從清王朝覆滅開始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動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并提醒“機制”“并不僅是外在的社會體制,它同時也包括現代知識分子對各種體制包圍下的生存選擇與精神狀態”,還強調文學研究“生命體驗”的重要性,號召“返回我們的歷史情境”。[6]154這一解釋明顯帶有新歷史主義的色彩,而新歷史主義正是打通不同領域知識的日常生活式思維。
圍繞“現代文學”命名問題的爭議似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最初提倡白話文學的新派中人以“新文學”與文言形式的舊文學劃清界限,顯然有批判與維護的用意在。即便像錢基博這樣守舊的文學史家也以“肇造日淺”“不愿奉民國之正朔”“斯亦廑矣”等因由而“不題‘民國’”,[7]7足見民國作為各方勢力政治無意識拉鋸之地的尷尬地位。“新文學”用名的動搖預示了當代文學的醞釀和建構,如研究者所說,“‘新文學’與‘現代文學’概念的更替,正是為‘當代文學’提供生成的條件和存在的空間”,換句話說,“當文學界用‘現代文學’來取代‘新文學’時,事實上是在建立一種文學史‘時期’劃分方式,是在為當時所要確立的文學規范體系,通過對文學史的‘重寫’來提出依據。”[8]144相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倡導則是由分到合的努力,其動機“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9]104。與文學自覺時代的20世紀80年代思潮相應,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合實際上是現代文學的深化和拓展,突出表現在政治與文學的博弈上。隨著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轉型持續而深入的開展,回到本身及個體自覺的日常生活語境逐步得以建立。作為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文學的關聯性及政治性都遠非其他各個部門所能比,因而也就在變革的順序上來得較遲,不用說在經濟起決定作用又占主導地位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展現中也最晚浮出歷史地表。
“20世紀中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的提議實際上并沒有立即引起巨大反響,而是在世紀之交才激起回響,很大原因是改革深入和經濟轉型所致。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甚至不亞于此前政治變革所達到的效果。正是在觀念解放和經濟主導的社會轉型推動下,人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才充分表現出來。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就是對此所作的反應。而在世紀之交發起的包括“民國文學”“現代文學史分期討論”等在內的文學史爭論正是遲到的反應,其原因除了由社會到創作,再由創作到批評的常見滯后外,也因為經濟對文學的決定作用還要通過政治的中介才能夠實現。“民國文學”的提議并沒有及時得到積極的直接響應的原因恐怕也與此不無關系。同時,歷來文學史思維和認知的慣例也維系其中,同樣制約了反應和認同,如嚴家炎所說:“文學史分期必須從文學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看重‘首尾貫穿的特色’,可以與歷史的分期不一致,不一定跟著朝代走。近代就有這樣的例子: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國,卻很難成為文學上劃分不同階段的依據。”[10]1為此,他提議:“還是先改用‘20世紀中國文學’(時間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下限暫不設定)這個相對穩定的概念為好”[10]3,后來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的出版正是這一預想的成果。針對書中提出的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三大發現”及現代性線索問題,張福貴并不認同,還就“以政治時代代替文學時代”的質疑堅信道:“就中國文學來說,以重大政治事件來劃分文學史恰恰能表征文學的本質,因為無論是文學時代的整體風貌還是某一階段的文學主題和風尚都與政治密不可分”。他希望:“面對歷史,我們還是一直期待一個合適的,自由表述的空間”,并從海登·懷特的思想出發,認為“我們每個人不一定都有參與歷史的機遇,但是都應該有評價歷史的權利。當我們不能對歷史作出自由表述時,就可以試著從方法論上尋找突破。”[11]84-85顯然,這一文學史認識論帶有日常生活時代的印跡。無論是“個人”,還是“方法”,都是一種日常生活式的表述。實際上,隨著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愈益重要以來,日常生活的自覺時代也就愈加突顯起來。回歸自身和現代性審視成為硬幣的兩面,而“民國文學”的熱烈討論正是這一趨勢和方式的自然結果。
二、“民國文學”場域及其日常生活取向
詹姆森(杰姆遜)曾就“‘歷史主義’的兩難處境”解釋說:“當我們要決定分析關于過去的形式或客體時,我們首先要在相同與差異之間作出隨意的選擇,我們的選擇支撐著我們與過去的聯系”[12]19。他指出,如果“從一開始就贊同陌生客體與我們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的話,那么所有導向理解的大門都對我們關閉起來,我們發現自己被我們的整個文化密度與定為異己的客體或文化隔離開來,因此我們無法接近異己的客體與文化”[12]20。就“民國文學”的倡導而言,既然日常生活語境促成了這一重構過程,那么與之相連的“民國”歷史語境恐怕也有異質同構的相似性。換句話講,在“民國文學”提倡者那里,“民國文學”的產生和生產同樣是在日常生活的歷史情境之中,或至少帶有可觀的日常生活色彩。不僅“二福”(陳福康、張福貴)的“通俗易懂”(陳福康語)和“回歸于簡單和直接”(張福貴語)是如此,就是秦弓(張中良)、李怡等人的方法論也打上了日常生活的印記。張中良在《歷史還原是現代文學學科拓展的有效途徑》中提出,把中國現代文學還原到民國歷史文化背景下去認識與敘述,“是要還原民國歷史文化的原生相”,而“在這一環境中發生發展的現代文學生態系統才能清晰地梳理出來”。丁帆主張“民國文學”的理由則是“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引進西方啟蒙時代以后普遍的民主價值理念,它不僅是從國家政治的層面確定了它對公民與人權的承諾,同時它也是在民族精神的層面倡導了對大寫的人的尊重。所以,才有了后來的所謂五四‘人的文學’的誕生”[13]170-171,還斷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精神理念作先導,其新文化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14]301。化用王德威的說法,就是“沒有辛亥,何來五四”。事實上,作為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之前與其后的日常生活也許并沒有多么翻天覆地的變化,如魯迅所諷刺的那樣:“竟不知道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15]185,倒是開歷史倒車的事例所在多有。不過,反過來說,事件性質本身畢竟是一種斷裂,由此未嘗不可開辟或衍生出新的意義空間。
不論倡導者希望依朝代劃分中國文學歷史的慣性思維來確立“民國文學”的概念,還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文學史邏輯,究其實質恐怕大都建立在日常生活成規的意義之上。理論上講,辛亥革命本身也是從皇權到民權的日常生活運動,雖然正如魯迅的小說所深刻揭示的,革命的結果也只是剪掉了一根辮子,但在社會變革的意義上畢竟開啟了朝向日常生活的“閘門”。拿1912年起在《民權報》連載,1913年出版單行本的《玉梨魂》來說,主人公何夢霞與白梨影和崔筠倩三人的愛情糾葛就塑造了新時代的日常生活詩學。白梨影的寡婦身份約束她不敢公然對抗舊式道德倫理秩序,而在同樣遭受來自父母之命的舊禮教迫害的崔筠倩也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泥淖。兩位無辜的女性先后在日常生活的羅網之中辭世。孤獨抑郁的何夢霞無力承受打擊,最終在武昌起義的革命中殉國。“革命+戀愛”的小說模式成為后來大革命時期“光赤式的阱”的先聲。分別省察可知,每個人的行動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都是社會和個人雙重作用的結果。白梨影的顧全大局是日常生活使然,崔筠倩的抑郁而死又何嘗不是維護新的日常生活理想的決絕呢?至于何夢霞的馬革裹尸更是時代日常生活的見證,與崔筠倩對信念維護的用心異曲而同工,同樣是建設公共日常生活的壯舉。有意思的是,小說本身就源于作者的日常生活經歷,只不過結局上大相徑庭罷了。民初流行的蘇曼殊的小說雖遭胡適痛罵,但與蘇曼殊私交甚好的陳獨秀除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號連載《碎簪記》外,還從“無論善惡,均不當謂其不應該發生也,食色性也”[16]7的日常生活習性出發,解讀其超越性意義。錢玄同也高度評價蘇氏“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17]5。周作人后來稱蘇曼殊為鴛鴦蝴蝶派的大師,并認為他“比一般名士遺老還要好些,還有些真氣與風致,表得出他的個人來,這是他的長處”[18]117。即便是胡適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上所攻擊的“獸性的肉欲”及“受今日幾塊錢一千字之惡俗之影響”兩點,也未嘗不見日常生活的風氣,排斥的背后恐怕只是不合他白話文的標準罷了。
辛亥革命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和框架理論上提供了現代性發展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契機,但因根基不深卻頓挫反復。不過,反抗壓迫的世俗現代性還是不斷生長,只不過大率媚俗和一味迎合罷了。包括幕表戲和黑幕小說在內的所謂世俗藝術樣式意在遷就日常生活中的無聊趣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西方現代性(或啟蒙現代性)追求大異其趣。錢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上鞭撻“戲子打臉之離奇”,以為“中國之舊戲如駢文”,至于“叩其實質,固空無所有”。周作人也在《論“黑幕”》中指出“黑幕”小說表達的“是一種墮落的國民性”,認為“黑幕是一種中國國民精神的出產物,很足為研究中國國民性社會情狀變態心理者的資料,至于文學上的價值卻是‘不值一文錢’”,[19]121還以為新文學并不就是通俗文學,并以“平民的文學”為例,說明“并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胡適也從歷史的文學觀念出發,否定了此前文學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引發爭議的是,新文化提倡者以“歐化”的方式或標準來替代自發的現代性,所謂“歐洲少年血性湯”(胡適語),“中西結婚的寧馨兒”(聞一多語)就是為此所開的藥方。“民國文學”的命名有可能還原種族、環境和時代的歷史時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動態平衡結構,而不是單一體系的主導生態,正如王德威對尋找“共相”的有機性文學史的反省,推崇梁啟超的文學流變的“互緣”“共生”觀念。梁啟超強調,在文學的流變里,“重要的聲音,重要的主體,它們怎么樣因時俱變,與時俱變,‘互緣’是相互激蕩之間所產生的一種‘不共相’”。換句話說,“正是在這種‘互緣’、‘動相’的激動之下,文學史里面的人物,文學史里的事件,思考以及它的成就,永遠是在互動的情況之下激發出新穎的、變動的成果”。[20]17實際上,世俗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并沒有改變更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狀況,及至新民主主義階段,以人民的現代化生活為最高目標和動力的空前的現代性實踐才確定了日常生活的取向,“民國文學”的日常生活性質才過渡到更新的階段。
三、“民國文學史”設想及其日常生活態度
作為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文學史既是時代和社會背景下文學實績的歷史,同時也是觀念和邏輯建構的歷史。對于前者而言,雖然我們不可能真正地還原歷史,所謂“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赫拉克利特語),但歷史時空現場和相互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原生態)仍是文學史最基本和最經常的目標。自律和他律的文學史即分別透露了個中消息。對于后者而言,百年來的文學史實踐更是證明了文學史編寫的政治或意識形態效果。如研究者所說:“歷史敘述事實上是現在和過去的相遇,是它們之間展開的對話。如果‘過去’不能轉化為‘現在’的問題,它們就很可能不會成為我們的‘記憶’,不會成為歷史事實”。[21]18文學史觀的背后實質上是時代精神的風景。就像章培恒和駱玉明的《中國文學史》是建立在“深入地揭示出文學所反映的人性發展的過程和文學之人性發展中所顯示的積極作用”[22]174一樣,“民國文學”的提出也是“一切歷史都是個人史”(張福貴語)、“致力于來自‘中國經驗’的思想主題與思維路徑”、“原生態地呈現國家、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種因素”[5]65等日常生活話語和經驗的顯現。這樣的文學史觀顯然是對革命或政治主導敘述的某種平衡。實際上,隨著對國外各種不同的文學觀和方法論的大量引入和借鑒,文學史的書寫范式也在廣度和深度上發生了多樣化的轉變,“民國文學”就是某種轉變和調適。當“新文學”概念在20世紀30年代被廣泛認可和運用時,新文學史的操作者并不諱言這一命名背后的多元化格局,如“不帶太明顯的黨派群體色彩”的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首先給人的印象,是內容比較豐富”[23]32。同樣,周作人在全力維護新文學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原始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作用和意義,如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一講關于文學之諸問題》中指出“一般研究中國文學或編著中國文學史的,多半是從《詩經》開始,但民間的歌謠是遠在《詩經》之前便已產生了,拋開了這一部分而不加注意,則對于文學的來源便將無法說明。”他在《答蕓深先生》中提出“文學史如果不是個人的愛讀書目提要,只選中意的詩文來評論一番,卻是以敘述文學潮流之變遷為主,那么正如近代文學史不能無視八股文一樣,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就不能拒絕鴛鴦蝴蝶派”并在《關于通俗文學》中聲稱“我們研究文學,單看一方面是不夠的”,以為要講文學史,非得從通俗文學去找材料不可,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將全部文學拿來看一看”。“民國文學”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盡量剝去政治或文學的先驗框架的外衣,而重建民國文學鮮活多樣的社會與文學生態。這一文學史視角和視野顯然是欣欣向榮和蒸蒸日上的日常生活時代的課題和要求。
文學史是歷史的文學顯現,除文學之外的各個社會部門都作為資料吸收或參與到文學之中,只有在動態的交互作用過程之中才能有效地把握文學及其流變。同時,文學史又是建構的歷史,建構主體決定了文學史的性質和面貌。如卡爾所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回答交談”[24]28。由此產生出兩種對立的態度:一是以過去(歷史)為主體,所謂“倘我們有時回顧過去,這目的只在看清我們從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巴枯寧語)。一是拿現在來衡量。歷來的歷史劇重在借古喻今,文學史同樣致力于解決當下的問題,這也正是文學史有限論和無限論爭論的焦點所在。有限論的根據在于辯證法的方式,而無限論則強調主客體生成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史大體以科學性為主,輔之以一定的能動性。關于前者,錢基博明確表示:“文學史者,科學也”[7]4。周作人也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認為:“既然文學史所研究的為各時代的文學情況,那便和社會進化史、政治經濟思想史等同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這課程便應以治歷史的態度去研究”。他相信:“這樣地治文學的實在是一個歷史家或社會學家,總之是一個科學家是無疑的了”。至于后者,更是文學史不斷創新和尋求突破的不竭動力,即如胡適就提出寫出時代變遷和文化進退的文學史,而其實踐則是從“民生文化”和“草野田間”的日常生活之中覓來。[25]160再如關于文學史的個人色彩問題,研究者大都認為,“完全沒有個人色彩的文學史著作,是不存在的”,堅信“歷史不在個人切身體會之中,是很難真正獲得理解的”。從寬松和包容的學術理想出發,“民國文學”的設想就不失為活躍文學史編寫的嘗試。
海登·懷特曾在《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一文中就歷史的“本文性”解釋說:“歷史就不僅是關于事件,而且也關于這些事件所體現的關系網。關系網并不直接存在于事件之中,它存在于歷史學家反思事件的腦海里。”循此構筑了他的“元歷史”的內在邏輯。“民國文學”提法的“反叛性”也隱含了這一前提。首先,“現代”和“當代”的命名本身就具有歷史的權宜性。“當代”一直下去的尷尬和后現代對于現代的沖擊都使得這些概念的歷史局限性凸顯出來,而包括“新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學”在內的文學史規劃也都不無罅隙和癥候。作為替代,“民國文學”的思路和框架無愧為首選。與此前或政治或文學的路向不同,這次的文學或文學史“運動”完全是自身的修正,打破了長期繞開的禁區,直擊民國日常生活生態。事實上,大量的文學史實踐都有它主客觀局限的相對性,并非呆板僵硬、不便通融的。拿學科專業上約定俗成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來講,從起點到最新趨勢的認知,似皆眾說紛紜,甚至截然相反。究其原因,恐怕與相對自由和寬容的日常生活時代密切相關。在這一時代語境下,文學史的活力終被激發出來,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繽紛景觀。“民國文學”的最大意義也許就在于此。《新青年》雜志的文學革命運動之所以能激起強烈反響,取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辛亥革命的推動和促成。無論是“打倒孔家店”、“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是白話文的提倡及對“人”的尊重,實際上早在晚清都已齊備,俱見篳路藍縷之跡。無怪乎《新青年》時代的周氏兄弟并不熱情,連編輯部組稿也不為所動。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他們兄弟“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卻“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敗”,雖就古文立論,但也隱含了超前的意義在。十年后幾乎是第二次的新生運動的成功不能不歸功于辛亥革命所奠定的現代性基礎。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沒有辛亥,何來五四”的說法并非簡單戲仿,而自有其歷史邏輯的道理在。反過來說,日常生活時代同樣可以誘發內在“民國文學”題中的應有之義,舉凡通俗文學、舊體詩詞,甚至所謂反現代的現代性,都不無生發或重構的可能。但正如梁啟超在《史學之界說》中對“公理公例”和《史之意義及其范圍》中對“因果關系”的偏重一樣,“民國文學”也自有其概念語義鏈和自身體系的特性。
四、結語
“民國文學”概念之所以在世紀之交的關節點上被提出,而作為歷史選擇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學史邏輯及學界內部復雜纏繞的糾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轉型后的重置和機制所致。新寫實小說所直面的日常生活走上前臺,成為意義和價值再生產的加工之地。“民國文學”的認識論和知識論大都得益于此。其實,任何文學史命名的背后幾乎都有等量的反作用力的解構在。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意在佐證他自己的歷史文學觀念,這在當時就有不同意見。同樣,作為新文學史基礎和前提的進化論不僅被敵對的《學衡》派同人所批駁,就連同一戰壕的新文學同人也不以為然,承認新舊之別的無力,所謂“太陽之下并無新事”,更不必說“現代”和“當代”這些從時間到性質轉換和沿革的概念了。“現代”和“當代”的使用反映了文學史命名的假定和約定。“現代”概念雖不乏自我整合的西方資源和動力,但在時代和社會發生嬗變的新形勢下,包含了歷史局限性的概念本身也將因內外矛盾的擴大而生裂隙。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極大地刺激了個人和民族的雙重自覺。固有的價值觀念由動搖走向瓦解,新世紀以來更是日新月異,尤其是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舉辦,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作家們中間也出現了“大踏步撤退”(莫言語)的聲音。“現代”也淪為被清算的概念。王德威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實質上是對理性和清醒的晚清探索的重估,背后未嘗沒有對于至今流行的“現代”概念的檢討。而“偉大的中國小說”(哈金語)和“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顧彬語)的對立觀點也未必不是在說明同一個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欲望、底層、網絡等大眾修辭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如果說日常生活審美化還可有爭議的話,那么作為社會文明重要尺度的日常生活的充分敞開就像打開了一扇大門,“民國文學”正是這“大門”里的風景。如果說此前有意無意的遮蔽可視為俯視的話,那么日常生活的視角和回望則是平視,是期望回歸歷史情境的矯正。總之,日常生活是人類社會的“大地”,最寬闊也最神秘。“民國文學”反響的熱烈恐怕也與此相關。
“民國文學”的思路蘊含了多種預設:首先是科學和真理的指涉。從系統論出發,“民國文學”被置于科學的分析對象的地位。受古來“六經皆史”之說影響,“民國文學”希望建立科學實證主義的價值自覺體系,如章太炎所主張:“史家載筆,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本不必以一二字為褒貶”。[26]146周作人也在《希臘之馀光》中特別賞識希臘史家都屈迭臺斯“嚴正的客觀”的求真態度,以為“足為后世學人的理想模范”。福柯注意到文學史的研究和方法“已從原來描繪成‘時代’或者‘世紀’的廣闊單位轉向斷裂現象”。他希望“探測中斷的偶然性”,并特別強調,今后,文學分析“是將一部作品、一本書、一篇文章的結構作為單位”[27]4。撇開與“民國文學”主張的不同不談,這里的“斷裂”或“結構”顯然指示了實驗室解剖或化驗的方向,帶有科學研究的意味。“民國文學”期望回歸歷史日常語境,而將“民國”分離出來作整體考察也就不無“斷裂”或“結構”的意趣。自然,真理只能在歷史文化系統的社會生態中才能找到,如張中良在《還原民國文學史》中所說:“民國文學史研究的旨歸,小則是要呈現真實的民國文學史風貌,豐富人們的歷史認知,大則是要普及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精神,保障社會穩步前進”。其次是主體意識的自覺和學術精神的張揚。對固化的文學史體制和慣例異議的動力既來自重寫文學史的潛能,更重要的是對日常生活氛圍的呼應。在此氛圍中,主體感、參與感與學術自覺的意識增強。海登·懷特聲稱:“只要史學家繼續使用基于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他們對于過去現象的表現以及對這些現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會是‘文學性的’,即‘詩性的’和‘修辭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認的明顯是科學的話語”。[28]1他把日常與歷史聯系在一起,目的就在證明歷史的文學性。詹姆森也指出“我們只能通過預先的本文或敘事建構,才能接觸歷史”,如存在歷史主義就認為,“歷史經驗是現在的個人主體同過去的文化客體相遇時產生的”[12]30。“民國文學”作為問題譜系的成立也是日常生活需求的結果。即如較早回應“民國文學”的趙步陽等人的文章就主要是從南京民國歷史文化旅游資源保護和開發的現實要求中產生的。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主張歷史不必“將古人寫得更死”,看他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文章大都活潑靈動,顯然,關鍵就在他強烈的社會和主體自覺。“民國文學”的成立恐怕也正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