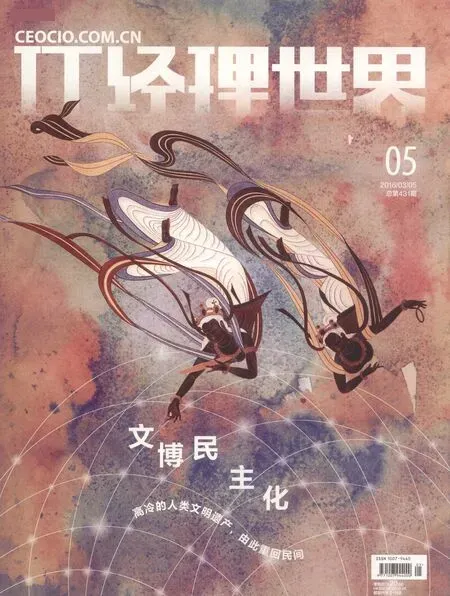遲到的區塊鏈營銷
栗建
舊的已經離去,但新的還未到來。整個營銷圈都在等待一場遲到的救贖。
在緊張的等待中,籠罩在麥迪遜山景城和金寶街酒仙橋的上烏云正在醞釀一場風暴:廣告主正在集體拋棄數字營銷。
2月聯合利華在一項聲明中表示,如果谷歌和Facebook無法在廣告透明度、平臺信息健康度上作出一定改變,他們將撤下所有投放在這些平臺上的廣告。根據去年聯合利華的數字廣告投放測算,這筆錢大概相當于24億美元。
另外一個重量級玩家寶潔公布了一組更讓數字營銷圈“寒心”的數據:2017年,寶潔公司減少了2億美元的數字廣告投入,但是品牌品牌曝光和到達(reach)卻增加了10%。

還沒有機會證明價值的數字營銷成為預算縮減大棒下的冤魂。寶潔公司首席財務官喬恩-莫勒(Jon Moeller)透露,該公司已經將廣告代理和生產成本削減了7.5億美元,預計將在“下一階段”再節省4億美元。
這兩家公司的“看空”很快演變成全行業的#MeToo(算我一個)運動。“不透明”、“注水作假”和“太多的中間商和太過的差價”正在讓數字廣告成為品牌營銷疲軟最大的替罪羊,即使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也無濟于事。無論中外,程序化購買廣告市場已經哀鴻遍野。
失效的數字營銷
不僅是數字廣告,整個數字營銷也步入了油膩的中年。
“雙向互動”和“消費自創內容(UGC)”早已被“大IP”和“品牌大制作”取代。無論是Facebook還是微信,都退化成投放的渠道。營銷活動中的“社交屬性”被逐漸邊緣化,一個營銷的活動的成功越來越依賴于大制作和大明星,而非觀眾的參與和互動。
“沒錢只能做數字營銷”已經變成了“沒錢做什么數字營銷”。
在視頻當道和體驗為王的大環境下,大部分品牌已經高攀不起。
這一切的根源,是互聯網的“反噬”和“原罪”。科普作家史蒂夫·約翰遜(Steven Johnson)在最近一期紐約時報雜志上撰文指出,互聯網的“烏托邦”正在崩塌。幾乎所有我們面臨的“社會疾病”都因它(互聯網)而起:虛假新聞和仇恨言論在網絡上蓬勃發展,個性化和社群化正在引導人們的偏見,權利和財富正在向極少數極客精英集中……
很自然地,看上去“無所不能潛力無限的”的區塊鏈被拉來救場。即使這種無法用人類語言簡單解釋的新生事物也在深處泡沫之中。
作為金融和投資工具,區塊鏈可能是一個大泡沫;但是作為信任和價值交換的載體,它可能會成為真正的革命性突破。在數字營銷領域尤其如此。
遲來的區塊鏈營銷
但讓大家著急的是,區塊鏈在營銷領域的進展遲緩。遠遠比不上如今大紅大紫的區塊鏈供應鏈以及區塊鏈金融等應用。
業內著名區塊鏈研究機構馬克婷不消停(Never Stop Marketing)公司最新的發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區塊鏈營銷技術地圖》報告,收錄的區塊鏈技術平臺和公司才剛剛過百。
作為對比,斯科特·布林克爾(Scott Brinker)編制的營銷技術地圖收錄的數字營銷技術平臺和公司已經超過了5000。
這并不能說明區塊鏈營銷技術地圖的編制者杰里米·愛潑斯坦(Jeremy Epstein)不如斯科特·布林克爾勤奮。這位曾供職微軟和社交媒體管理平臺Sprinklr的區塊鏈營銷意見領袖實在是找不到足夠的公司來填空。這份地圖上22個細分區塊鏈營銷領域還是空白。
區塊鏈營銷進展遲緩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營銷圈的“自我保護”。區塊鏈營銷之于營銷,就像客戶關系系統(CRM)之于銷售,透明和效率并不全是好事。
這是一個與虎謀皮的博弈。
剛剛弄清楚什么是大數據和程序化購買的4A公司和甲方“馬克婷”們,面對突如其來的區塊鏈,內心是忐忑的,身體是拒絕的。
對這一技術有深入洞察的人,會預見到區塊鏈營銷會帶來不可預見性的顛覆。當區塊鏈讓一切都透明,消除了賺差價的中間商,營銷產業鏈上所有玩家的定位和游戲規則都將改寫。
根據Forrester分析師的調查,如果在數字廣告產業鏈上去掉中間商,廣告平臺的千人展現成本(CPM)的收入將從1美元提升到5美元。換句話說,以往品牌需要花5美元做成的事情,其實只要1美元就可以做到。分布在數字廣告產業鏈條上的各級各類中間商賺取了4美元的差價。
對于那些外來的顛覆者——區塊鏈營銷領域的創業公司,他們對于發行代幣ICO的興趣可能要遠遠大于技術的實際應用,盡管ICO后來大部分都成了騙局。
廣告公司Prism的CEO和聯合創始人詹姆斯·克里爾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無論是BitClave還是Brave, 他們對營銷產生的作用還遠沒有顯現。
盛名在外的區塊鏈搜索平臺Brave或者區塊鏈廣告交易平臺AdToken的發展速度和用戶增長遠低于人們原本的預期。
甚至,所有的致力于區塊鏈廣告交易透明的平臺都面臨一個傳統但強大的對手,美國互動廣告協會(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IAB)的ads.txt解決方案:只要向廣告平臺植入文本文件,就可以解決網絡廣告交易的透明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廣告主被迫選擇和IBM等技術咨詢公司直接合作,探索區塊鏈營銷的可能性。聯合利華已經于IBM達成區塊鏈廣告投放上的合作。目前,這兩家公司已經將區塊鏈技術用于廣告投放的監測。IBM iX負責區塊鏈項目的巴布斯·朗格亞(Babs Rangaiah)之前曾在聯合利華工作了14年,他透露IBM的區塊鏈業務未來將延伸到廣告購買和用戶數據管理,建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實時競價和消費者數據加密和管理系統。
IBM還是沃爾瑪和雀巢等公司區塊鏈技術的合作伙伴。新加坡航空則選擇了與KPMG和微軟合作,探索區塊鏈在旅客獎勵計劃項目中的應用。
真正的考驗
數字營銷的真正考驗,圍繞著價值交換問題展開。這才是區塊鏈技術被寄予厚望的地方。
如果說營銷的本質是品牌與消費者的價值交換,現在的數字營銷并沒有很好完成這個任務。 在互聯網剛起步的時候,品牌還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信息來交換消費者的時間。品牌扮演價值布道者和潮流引領者的角色,以品牌故事和優質內容換取消費者的忠誠和注意力。
但是互聯網逐漸抹平了信息的不對稱,品牌的角色和作用被大大削弱了。曾經作為信息平臺的企業網站訪問者寥寥,曾經被基于厚望的網絡粉絲群在一次次的平臺更替中消散。
在占領消費者心智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上,品牌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魔力。
所以,即使區塊鏈解決了數字營銷的透明度和“中間商”問題,還面臨更棘手的問題:如何幫助品牌換取消費者的忠誠和注意力。
漢堡王的“漢堡幣”和新加坡航空的“以里程換代幣”并未觸及到這一問題的核心。
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一個大膽的方案是基于區塊鏈、讓注意力可以量化和流通的“社交幣”。“社交幣”和蒂姆·奧萊利所說的“人類幣”類似,區別于機器基于生產和計算產生的“機器幣”或者“比特幣”。
比特幣產生于計算機礦機的“算力”,但本質是稀缺性。比特幣產生于維護分布式賬本的工作所獲得小額、日益稀缺的比特幣回報。如果你把計算機的一半處理周期都用在了幫助比特幣網絡進行正確計算,從而抵御黑客和欺詐的話,那么你會收到一小部分比特幣。中本聰設計了這個系統,讓比特幣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難以獲得,從而確保了系統中一定數量的稀缺。
我們的注意力也具有“稀缺”的屬性。羅振宇創造過一個概念,叫做國民總時間GDT。意思是人是一定的,每個人的時間也是一定的,所以這個總的加起來的時間注意力是一定的。
具有“稀缺性”屬性的注意力,除了被騰訊和阿里巴巴無償收割,也可以成為“社交幣”,像比特幣一樣具有價值,并可以用來投資、購物和交換 。
基于區塊鏈的社交貨幣可以讓隔壁王小美每一次搜索、曬圖、購物、分享和點贊都獲得獎勵。這不是夢想,在區塊鏈社交媒體平臺 Steemit上,一個來自中國的小姐姐寫了一篇土耳其卡帕多西亞的游記,一天之內賺了834.43美金。
聽上去有點像微商和傳銷。才不!
Steemit是一個基于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社交網絡平臺,并且透過Steem代幣來獎勵平臺的參與者。發帖或者點贊留言,都能夠獲得Steem的代幣。這家網站去年的注冊用戶還不到100萬,但今年全球訪問量排名已經進入前1200。
比steeemit更更進一步,JavaScript之父Brendan Eich倡導的基本注意力貨幣(Basic Attention Token,BAT)是更具平臺屬性的“社交幣“。
BAT是一種支付系統,它獎勵和保護用戶,且可以為廣告客戶提供更好的轉化,給發行商帶來更高的收益。它能夠解決發行商內容營利的重要問題,同時也保護了用戶隱私。
BAT應用于上文提到的瀏覽器Brave。在Brave平臺上,愿意打開廣告的人或者點擊品牌內容可以獲得代幣獎勵。這就是傳說中的“看廣告也能賺錢”的區塊鏈版本。但Brave高明指出在于,它的相關內容是精準推送的,降權或者屏蔽那些以賺錢為目的的用戶。
但無論是steemit還是BAT社交幣系統,都還是著眼于“用戶端”問題的解決,缺乏“品牌端”的解決方案。因為“付費看廣告”并不能實現長久健康的“價值交換”。
真正的考驗才剛剛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