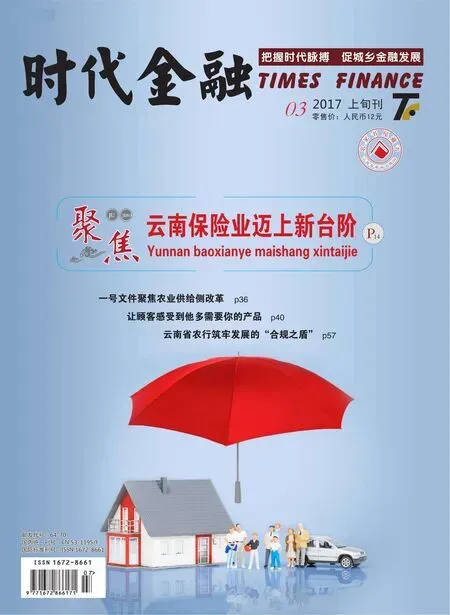大學生實習豈能變高校撈錢項目
姜春康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1月23日報道,“被學校強迫實習了一星期,不止一次有了想死的念頭。”在微博上,山東聊城大學學生寫下一封“求助信”。這位學生透露,學校要求數百名大三同學寒假期間到昆山康佳電子有限公司、蘇州佳世達科技有限公司實習。
近年來,大學生“被實習”現象時有曝光。無獨有偶,河南省教育廳的一紙“組織中職學生赴某企業頂崗實習的緊急通知”,讓部分學校變相強制學生去企業實習的做法備受質疑。雖然有關方面強調,“絕無強制,一律以自愿為基礎”,但“不去實習就不發畢業證”的要求,讓很多學生感到這種自愿成了“變相強制”。
這些現象的共同點是,名義上是實習,實則通過與勞務中介簽協議,把學生“賣”給工廠流水線當工人。因為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不少學生不愿意,但有的學校卻以不發畢業證為“威脅”,導致學生敢怒不敢言。從本質上看,這些學校已經將實習課程變為撈錢項目。
大學生“被實習”,豈能變成撈錢工具?首先,工作時間從早晨7:40至晚上11:00,因為承受不了這么大強度,很多同學發燒感冒,一直不停工作,不少學生因零件磨損手上起泡,如此強度已經僭越了真正實習的范疇,而成了“低價獲利”的工具。其次,上述兩家實習單位在網上一直在招聘流水線普工,條件是“初中文化以上”。很多學生認為,來這里實習跟他們本科所學專業關系不大,但有教師解釋,“只有貼近了工人才能了解安全”,更像是辯解,更關鍵的是學校老師“軟硬兼施”,聲稱實習是一門必修課,不實習沒法領畢業證;還暗示將來老板和導師都不愿要“受點罪”就發牢騷的學生。這樣的“沒法”,已讓大學生“被實習”成為“鐵證”。
校園實習為何變了味?還有多少學生“被實習”?為何該現象屢被曝光卻又有出現?一方面,學校的做法并不厚道。為了保證就業率,為了在招生上“吃飽”,就用這樣的“副業”來打著實習的旗號獲利,并讓實習變得“好看”,他們完全不顧及一些學生們的反對,就采用“脅迫”方式,這充滿著嚴重的不道德意味。從本質上看,這和教育部一再強調的“不準以各種方式強迫畢業生簽訂就業協議和勞動合同”有著相似之處,都是學校用類似于霸王條款的方式讓學生們“入甕”。另一方面,對類似學校的處理上,很多地方只用不疼不癢的方式去通報批評糾偏,卻并沒有真正去嚴厲懲處,地方保護和形式主義的保護,使得該現象大多停留在“滅火”階段,而不是深究追責的“刮骨療傷”。要知道,嚴厲的制度更需要實打實落地才能防止“拳打棉花”,才能避免禁令在執行中被稀釋。無論是學生“被實習”還是“被就業”,都透露出一些高校的傲慢來,他們的我行我素,深層原因是違規成本低于他們的“撈錢”渴望,因為并沒有受到嚴厲“制裁”,這在無形中也容易助長一些高校繼續玩躲貓貓游戲,繼續讓學生“被實習”“被就業”。
大學生實習成了某些高校的撈錢項目,既讓人痛心又讓人氣憤。建議上級主管部門認真查一查,揭穿學校“軟硬兼施”背后的遮羞布,并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追責。當然,要徹底杜絕該現象,首先需要國家層面祭出禁令,讓政策規定“硬”起來。其次,要嚴厲執行政策,對違規者不能手軟,尤其對一些院校的處理,不能讓地方保護主義摻和進來,只有提高違規成本,才能掐滅某些高校躍躍欲試的小火苗。再者,建議暢通舉報通道,建立全民監督機制,不讓該現象輕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