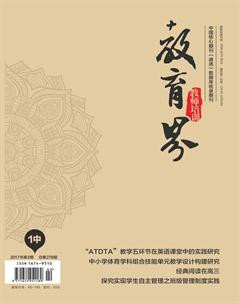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陸嘉明
(續(xù)前)
80
有人說(shuō),歷史是中國(guó)人的信仰。
是的。真實(shí)的歷史能體現(xiàn)人類文明進(jìn)程的歷史精神。
還有,英雄的史詩(shī)以及通過(guò)宏大的歷史敘事或藝術(shù)化的表達(dá)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文化思想和“力與美”。
歷史的信仰,文化的信仰,藝術(shù)的信仰,民族精神的信仰。
羅氏的“三國(guó)”,是小說(shuō),不是歷史的如實(shí)敘說(shuō)。既為小說(shuō),就有情節(jié)的虛構(gòu),細(xì)節(jié)的刻畫和渲染;就有典型人物的塑造,臧否人物定然出乎作者秉持的思想傾向和文化立場(chǎng)。
因此,在羅氏筆下,劉備持抱“正統(tǒng)”文化,故而是了不起的英雄。所謂“正統(tǒng)”文化,即在政治立場(chǎng)上是維持和復(fù)興大漢的一統(tǒng)天下;在思想傾向上,是以儒家文化為行為的旨?xì)w;在情感態(tài)度上,是以“忠君”和謀取天下太平為人格標(biāo)準(zhǔn)……劉備的“匡漢”和“仁義”道德,前文表過(guò),無(wú)須贅述。至于孫權(quán)守業(yè)其本,“隱忍”其性,謀“和”求“平”,基本屬于儒學(xué)的中庸之道。故而偏于江南一隅而為王為君統(tǒng)治50余年,其中在吳帝位凡23年,這在“三國(guó)”亂世絕無(wú)僅有。當(dāng)然無(wú)愧乎英雄一生矣。
那么曹操呢?“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用說(shuō),在羅氏小說(shuō)中,全然是一個(gè)亂臣賊子的形象,集權(quán)謀奸詐殘忍兇狠于一身的反面人物的典型,一個(g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十惡不赦的殘暴惡人。在文化立場(chǎng)上,他好像全都站在“正統(tǒng)”的對(duì)立面上,即使功業(yè)有成、統(tǒng)一北方,也仍然是一個(gè)大逆不道的“奸雄”形象。
說(shuō)來(lái)有趣,愚之對(duì)曹操的認(rèn)識(shí),卻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漫長(zhǎng)而曲折的過(guò)程。好像自覺不自覺地在“正統(tǒng)”與“非正統(tǒng)”的文化之間搖擺起來(lái),乃至也生出一些新的想法來(lái)。
早在20世紀(jì)五十年代初,我,一個(gè)青澀少年,只要口袋里有一二百塊錢(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一二分錢),一放學(xué),就一溜煙閃過(guò)禾家弄11號(hào)家門口,過(guò)雙井,越虹橋,直奔中市河畔的小人書攤,向精瘦精瘦、眼珠子骨碌骨碌打轉(zhuǎn)、活像一只老猴子的攤主,氣壯如牛般亮出手中的小票子來(lái),斷斷續(xù)續(xù)地租看《三國(guó)演義》連環(huán)畫。就這樣有錢就看,看一本是一本,看得天昏地暗,看得心旌搖蕩。曹操嗎?壞人啊!奸臣、國(guó)賊、惡棍、梟雄……梟雄是什么人?還真不懂。總之是“奸細(xì)白鼻頭”,徹徹底底壞人一個(gè)。不過(guò),本事倒是有的,氣魄也大,敢說(shuō)敢為敢當(dāng),不可一世,是個(gè)人物。
六十年代初,負(fù)笈石城,正當(dāng)自然災(zāi)害時(shí)期,校方動(dòng)足腦筋來(lái)豐富學(xué)生的精神生活。打太極拳,跳交際舞,聽音樂(lè)會(huì),看露天電影,還有幸看了一場(chǎng)話劇《蔡文姬》。這是郭沫若編的一出歷史劇,記得是焦菊隱導(dǎo)演、北京人藝演出的。
話劇表現(xiàn)了曹操不惜用金璧贖回流落南匈奴的一代才女蔡琰即蔡文姬的故事。且不說(shuō)“文姬歸漢”時(shí)悲欣交集的情感抒發(fā)對(duì)我的心靈震撼,倒是劇中的曹操形象一時(shí)顛覆了我少時(shí)形成的印象和感覺。那個(gè)一向認(rèn)作白臉奸雄的人,竟如此憐香惜玉珍重人才,胸襟豁達(dá)落落大度,且儀態(tài)大方舉止灑然,并富有令人怦然心動(dòng)的人情味。
依稀聽聞當(dāng)時(shí)學(xué)界頗有爭(zhēng)論,說(shuō)是斯劇為純粹翻案,有褒有貶毀譽(yù)參半。我一懵懂學(xué)子,不諳于歷史學(xué)問(wèn),且不管它,只是促使我讀了蔡文姬的《悲憤詩(shī)》和《胡笳十八拍》,感動(dòng)之余,又讀了曹操的詩(shī),諸如《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等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反映出來(lái)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思想感情,倒是一位胸懷雄圖大略并深切同情民生疾苦的詩(shī)人形象。哪里像羅氏小說(shuō)中的那個(gè)權(quán)謀奸詐、兇殘狠毒的佞臣惡人呢?
如詩(shī)中描繪漢末軍閥混戰(zhàn)給軍民帶來(lái)的災(zāi)難:
……鎧甲生蟣虱,萬(wàn)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wú)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dāng)嗳四c。
——《蒿里行》
……行行日已遠(yuǎn),人馬同時(shí)饑。 擔(dān)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shī),悠悠使我哀。
——《苦寒行》
亂世混戰(zhàn)如此慘烈,如此艱辛,詩(shī)人又如此體察民生哀傷憫惜,乃至寸腸欲斷猶抱安定天下之志。這正如明譚元春在《古詩(shī)歸》中所說(shuō):
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
是啊,我等后人于吟誦之際,怎能不感到這位詩(shī)人的“熱腸”呢?
魯迅先生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曹操是一個(gè)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gè)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wú)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不僅魯迅佩服他,連毛澤東對(duì)他也是極盡頌揚(yáng)之詞的:“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浪淘沙·北戴河》)。”那是一個(gè)多么高大的文武雙全的英雄形象啊。
其實(shí),曹操這個(gè)人,歷史上是一個(gè),詩(shī)文中是一個(gè),民間傳說(shuō)里、文學(xué)作品里又是一個(gè)……這并不奇怪,前者是歷史形象,后者是藝術(shù)形象。無(wú)論是歷史記載還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衡量人物的文化尺度不同,即會(huì)得出各不相同的結(jié)論來(lái)。
羅氏的小說(shuō),雖有一定的歷史依據(jù),但畢竟是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造,除有虛構(gòu)的成分之外,也有據(jù)史實(shí)描寫而進(jìn)行的文化傳承和弘揚(yáng),唯因過(guò)分堅(jiān)摯和夸大了“正統(tǒng)”,往往掩蓋了它因襲固化的局限性和負(fù)面影響;過(guò)分誤解甚至歪曲所謂的“非正統(tǒng)”,往往會(huì)抹殺文化因時(shí)而化的開放性和歷史價(jià)值的正面效應(yīng)。
其實(shí),“正統(tǒng)”與否不是絕對(duì)的,對(duì)立的雙方常常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通過(guò)撞擊和突破,乃至裂變和分化重組,或互補(bǔ),或包容,或滲透,或交融,形成多元形態(tài)的文化格局。當(dāng)然,在社會(huì)文明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陳腐而消極的劣質(zhì)文化,必將在大浪淘沙中日漸銷聲匿跡,據(jù)傳統(tǒng)而創(chuàng)新的優(yōu)秀文化,則必將在潮來(lái)潮去的時(shí)代選擇中蓬勃發(fā)展,并不斷深入人心傳之久遠(yuǎn)。
惜乎羅氏不懂,或不愿。一味“正統(tǒng)”,一貫持單一評(píng)價(jià),則難免失之于文化偏頗。然則其幸乎懂文學(xué),又熟稔塑造人物和審美描寫,留有名著行世,給人以豐沛的藝術(shù)享受。
愚認(rèn)為,在藝術(shù)形態(tài)上,曹操是其筆下最為生動(dòng)、鮮明而個(gè)性犖犖凸顯的人物,為中國(guó)文學(xué)的人物畫廊增加了一個(gè)不朽的典型形象。
只是歷史上的曹操,有點(diǎn)冤枉,有點(diǎn)委屈,或說(shuō)有點(diǎn)倒霉了。
流布民間,代代相傳。這也是沒(méi)有法子的事情。
不過(guò),從文化視角觀之,劉備“仁義”,似近乎“偽”;孫權(quán)“隱忍”,或近乎“屈”;曹操“狂放”,則最為“真”。
他活過(guò),活出了“真自我”;活出了“真生命”。他勝過(guò),勝出了“真智慧”“真功績(jī)”“真價(jià)值”;他也敗過(guò),卻敗出了“真胸襟”;他更霸道過(guò),卻又霸出了“真情性”。
當(dāng)然,他曾負(fù)世人,但也曾惠當(dāng)世;他有過(guò)失,但也曾逐鹿中原建功立業(yè)。
因此,他根本無(wú)須用“正統(tǒng)”來(lái)證明自己的歷史價(jià)值;更無(wú)須用他人的評(píng)斷來(lái)改變自己的文化風(fēng)致。
在凜冽的風(fēng)聲中,可以聽得見錚錚作響的血性漢子。
在烽煙彌漫的天空下,可以看得見雜色斑駁的真英雄。
81
這好像與羅氏的描述和評(píng)價(jià)大相徑庭了。
其實(shí)也不能以單一視角論之。
評(píng)價(jià)確乎不同,但我們完全可以超越作者的文化觀,于歷史和小說(shuō)的鏈接處以及寫實(shí)的情節(jié)和虛擬的細(xì)節(jié)若即若離之間,隱隱約約看到一點(diǎn)人物真實(shí)的自然表情、微妙的心理狀態(tài)、復(fù)雜的思想感情和影影綽綽的背影。尤其是在成敗得失的邊緣和形勢(shì)詭異的時(shí)空交集之際,即可約略抽衍出人物的文化性格和是非交錯(cuò)的邏輯關(guān)系,從而觸摸到史脈劇烈的文化搏動(dòng),并真真切切地蠡測(cè)出這一人物形象游走在藝術(shù)世界而黑白交互的本相和靈魂。
雄豪于亂世,快意于江湖。
曹操,叱咤風(fēng)云于小說(shuō)中的歷史人物,思想和情性雖迥異他人,然細(xì)究起來(lái),其實(shí)也曾受惠于傳統(tǒng)文化,只是從不受囿于傳統(tǒng),甚至挑戰(zhàn)和顛覆了傳統(tǒng),故而一生雖正邪交賦波瀾迭起,卻始終巍巍然兀立在急湍的時(shí)代漩渦中;一世戎馬倥傯出生入死,卻始終灑灑然穿越在重巒疊嶂險(xiǎn)象環(huán)生的危途上。
意欲何為?行欲何往?
在史書和他的詩(shī)文中,當(dāng)可一窺端倪,做出較為近乎歷史的真相和其人本心來(lái)。
然而,愚今品讀小說(shuō),所評(píng)者則是羅氏筆下的文學(xué)形象。羅氏雖持褒劉貶曹的文化傾向,但因多據(jù)史實(shí)用筆,那么,可否從小說(shuō)藝術(shù)描述的間隙所透露出來(lái)的一點(diǎn)客觀消息,抑或作者不期然流露出來(lái)的人物個(gè)性以及客觀評(píng)價(jià),做出一點(diǎn)合乎文化多元觀或歷史價(jià)值觀的見解來(lái)呢?
愚想是可以的。
當(dāng)然,這還得以小說(shuō)為本,只能適當(dāng)以史實(shí)和詩(shī)文作為印證,乃至反證,在文學(xué)形象和歷史形象的互襯相映之間,洞察一個(gè)真實(shí)的人,一個(gè)非凡的人。
然而,“真”,未必“善”,未必“美”。也許是“惡”,是“丑”。抑或二者錯(cuò)雜交混難分彼此。
一個(gè)如獅虎嘯吟獨(dú)步天下的人,一個(gè)具王者風(fēng)度的亂世靈魂。但是,因其好壞美丑糾纏在一起,人性之優(yōu)劣轉(zhuǎn)化無(wú)常,心志與權(quán)謀羼雜不清,實(shí)在也太復(fù)雜了,太混沌了。無(wú)怪乎歷來(lái)備受質(zhì)疑、猜度、非議,甚至貶斥、丑化、詆毀。于是,這個(gè)亂世梟雄,在羅氏筆下,更是一個(gè)奸雄形象,聲名狼藉,流傳于世,口口相傳。
貼近了看,庶幾近乎歷史真實(shí);放遠(yuǎn)了一看,又似乎遠(yuǎn)離了人物的文化情致和其恪守內(nèi)心的人生詩(shī)意。
當(dāng)然啦,一個(gè)人,只要真實(shí)地活過(guò),愛過(guò),恨過(guò),擔(dān)當(dāng)過(guò),歌哭過(guò),人生的行跡,在大地上留痕,轟轟烈烈也好,平平淡淡也罷,不銹的,是天道和人性的陽(yáng)光;銹蝕的,是時(shí)間風(fēng)化的青銅印記,終而于幾代人的心中化為千年一嘆,在滄桑歲月里孕育出文化的氣息……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