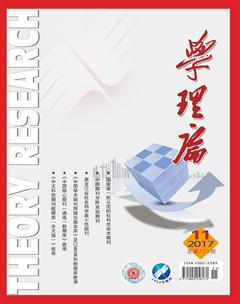儒家“仁”之倫理不同于關懷倫理
尚貴君
摘 要:儒家倫理學中關于“仁”的概念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又一貫是學界所關注的傳統論題。有學者認為,儒家倫理的“仁”倫理和關懷倫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可通約性,即這兩種理論被認為能夠出現兼容的可能。然而,儒家倫理并不僅僅囿于關懷的層面,它同時也表達了對于“禮”作為秩序約束效用的需要。因而,重新厘清儒家倫理學說中“仁”與“禮”的關系,明確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認識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的本質區別,還原儒家倫理中“仁”的本來面貌,對于我們繼承與發揚儒家傳統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儒家倫理;仁;禮;關懷倫理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10-0078-03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一些觀念也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改變。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代表著特殊意義,應當為儒家文化的思想傳承與歷史發展尋找新的契機,故而他們提出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有著相似之處。儒家仁學倫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貫穿儒家文化發展的全過程,有著豐富的歷史傳統;而關懷倫理是20世紀初西方產生的一門新興學科,它是女性主義倫理的一個重要部分,其主要的內容就是“關懷”。一個東方,一個西方;一個歷史久遠,一個新興學科;雖然兩者都注重“關懷”,這是否就意味著兩個相差數千年的理論之間,就有著相似之處?是否儒家倫理也可以被認為是關懷倫理?還是說這種“關懷”外衣之下的相似僅僅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非本質上的相似呢?他們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引起了中國傳統思想研究者和女權主義者的回應。因此,我們也需要更加詳細地認識儒家仁學倫理,明確儒家仁學理論和關懷倫理之間的差別。
一、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的通約性
李晨陽在他的《儒家的“仁”的概念與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一種比較研究》一文中提出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有著相似之處。他認為,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存在著共同的哲學基礎。首先,他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仁觀念和女性主義關懷倫理都體現一種非契約型社會關系,這兩種理論完全區別于西方所建構的契約型社會關系”[1]。在西方傳統的契約型社會關系中各個社會成員之間需要相互簽訂社會契約,但是在儒家觀念中社會關系可以被看成是家庭關系的延伸,君臣之間的關系也可以像父子之間的關系一樣,沒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別,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沒有契約存在的。女權主義在家庭和社會關系中存在著相似的理論,女性關懷主義哲學家弗吉尼亞·赫爾德認為,“母親和孩子之間的關系應該被認為是首要的,也是其他社會關系的雛形和基礎,其他形式的人類關系都應該是這種關系的反應。”[2]家庭關系是其他社會關系的基礎,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成員之間不需要社會契約。所以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都反對建立這種契約型的社會,道德應該是自足的,而不是基于個人權利的,正如吉利根所言:“道德理解的建構并不是基于個人的首要和普遍權利,而是對世界的強烈的責任感。”[3]對于儒家來說,道德無關個人權利,而是社會中各種社會角色的扮演。所以,基于非契約型社會的討論,在儒家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最核心的就是仁,女性關懷主義體現的就是關懷。
其次,李晨陽認為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都反對兼愛,提倡愛有差別。墨子的兼愛學說認為:“視人之國若視己國,視人之家若視己家,視人之身若視己身”(《墨子·兼愛》),他提倡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的普遍關懷主義。儒家不贊同墨子的“兼愛說”,而主張“愛有差等”。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認為我們要尊敬自家的長輩,推廣開去也尊敬別人家的長輩;關愛自家的兒女,推廣開也關愛別人家的兒女。儒家主張要先愛自己的父母,推廣開來愛他人的父母,所以“仁”所體現的是從家族親親出發,以孝順父母,兄友弟恭為根本,然后再擴展為愛他人的境界。諾斯丁也體會到,“關懷經常是以自我轉移為特征的,我非常關心和我交往密切的人,而對離我生活較遠的人卻顯得有些冷漠……關懷的行為是隨著條件狀況和關系類型而改變的。”[4]這里體現的關懷倫理是以“我”為中心,根據人與人之間交往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這意味著無論是儒家的仁的倫理還是關懷倫理,都不可能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普遍的愛,所以,儒家“仁”之倫理和關懷倫理中的關懷體現的都是有差別的愛。
最后,李晨陽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仁”在概念上與關懷相同。李晨陽在文章中將“仁”理解為“仁者愛人”。雖然“仁”的概念也可以擴展為勇敢、智慧、美德等等,但是所有的這些概念都可以歸結為“關懷”。李晨陽認為,儒家對“仁”最清晰的定義就是“仁者愛人”,而愛就表現為關心,愛護;這種關懷首先體現在對家人、朋友之間的關懷。孟子所認為的幼子溺水,路人聞聲救助這種行為是一種“關懷”,而這種關懷是來源于人內心的情感。聽見幼子呼救,首先考慮到的不是我們施救的行為是否能獲得回報,而是人之為人想要幫助的內心情感。在女性主義關懷倫理中,吉利根認為對于女性來說,最重要的道德就是關懷。這不僅意味著女性去關懷或者說女性需要關懷,而且每個人都需要去關懷別人,同樣也需要他人的關懷。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關懷他人,那么世界就會變得剛好。所以,李晨陽認為不管是儒家的仁學倫理還是關懷倫理,關懷都是最高的道德準則。
所以,基于“關懷”的這些相同點,李晨陽認為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可通約性,儒家倫理是關懷倫理。看到了這些相同點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發現儒家“仁”倫理和關懷倫理之間的差別。
二、儒家“仁”倫理中“仁”和“禮”的關系
儒家倫理和關懷都反對兼愛,提倡愛有差別,但是這兩者體現出來差別是不一樣的,儒家倫理強調的是建立在“禮”的基礎上的愛有差等。儒家倫理中不能僅僅將“仁”理解為關懷,除了關懷更要理解儒家倫理中的“禮”,在儒家“仁”倫理中“仁”和“禮”缺一不可,兩者相輔相成,互為一體。明確“仁”和“禮”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理解“仁”。李晨陽只在“仁”的基礎上分析儒家哲學才會認為儒家倫理是關懷倫理。但是我們如果注重“仁”和“禮”的關系的基礎上解釋儒家倫理,就會發現儒家倫理不同于關懷倫理,兩者的區別是本質上的區別。所以,本文嘗試通過“仁”和“禮”的關系來論述儒家“仁”倫理和關懷倫理是不同的。
在儒家倫理中最具儒家代表的是《論語》,本文主要是基于《論語》這本書來討論。儒家倫理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但是孔子并沒有給“仁”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5];“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孔子認為“仁”是關愛,也是剛強、堅毅、樸實、謹言這些美好的品德,同時也表示行仁必須守禮。所以對于“仁”的理解不僅僅是關愛,也體現的是一個人具有的內在品德或者也體現的是遵守禮的行為規范。“禮”的意義也非常廣泛,《禮記》中講:“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之間的一切事物,一以貫之的秩序就是禮。荀子說:“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達者,禮也。”(《荀子·大略》禮是人們實踐的依據和規則,偏離禮就會造成混亂。所以,禮不僅僅是人自身行為的規則,也是治理國家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理念。所以,“仁”體現的是人的內在修養,而“禮”則是外在的行為規范。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沒有“禮”的約束,空有仁必然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如果只有“禮”,缺乏“仁”,社會會變得不近人情。所以,我們不能離開“禮”來單獨談論“仁”的概念,“禮”所表達的是“仁”的實踐層面,“禮”和“仁”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兩者缺一不可。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認為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社會的混亂不堪都是因為人心變壞,為了能夠拯救人心,孔子提出了“仁”。如果一個人能夠有仁心,那么他就會恢復本心,遵守規則禮制。同時孔子也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孔子認為只有恢復社會原有的禮制法度,大家都按規則做事,社會才會充滿仁。所以,在孔子看來,“仁”和“禮”同樣重要,“仁”體現的是道德修養,而“禮”應用在社會實踐活動。仁和禮的具體關系均體現了仁和禮緊密的相互關系,可以從三個具體方面來加以闡述:個人、社會和國家,都體現了仁和禮的密切聯系。
(一)個人修養
在儒家思想中,圣人之性在于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想成為一個仁者最重要的是修身,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孔子認為真正的仁者能夠公正的喜歡人、厭惡人。當我們用這個標準來評價一個人時,“仁”體現為個人的品德。“之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孔子認為一個仁者需要具有恭敬、寬厚、誠實、勤敏和慈惠這五個優秀的品質,這些品德成為評價一個人是否是仁者的標準。但是孔子同樣認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在孔子看來,恭敬、謹慎、勇敢、直率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質,但是如果沒有禮的種種要求和規范來加以節制就會產生煩惱不安、膽怯、犯上作亂和尖刻傷人這樣的禍端。所以,一個人的品德不僅要符合“仁”的修養,同時也要符合“禮”的規范。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世》)孔子認為不學詩就不懂得如何正確地說話;不學習禮就不懂得如何立身于世,所以禮不僅是人的基本的行為規范,也是人行為處事的基本方法。孔子還指出“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是努力學習,博學多識,卻不在禮儀方面加強自身修養,也一樣不能達到人生的境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孔子認為不懂得知命的人就不能成為君子,同樣不懂得禮儀的人,也不能在社會上立足。所以,在儒家倫理中,作為一個君子,要“立于禮”“約于禮”,用禮儀來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遵守禮的道德規范,才能稱為一個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
(二)社會生活
在個人的行為素養中“仁”的實行需要以“禮”為行為規范和行動準則。在家庭之內,孝悌是儒家提倡的基本倫理觀念。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孔子對何為孝的回答是無違,何為無違?即不要違背禮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按照禮儀規定來侍奉他們;父母死去的時候,我們要按照禮儀制度安葬他們,祭祀他們。所以,在家庭中孩子對于父母的孝不僅是愛護和關心,更是需要按照禮儀規定來孝順父母。只有在禮制基礎上的孝順才是真正的孝順。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認為真正的孝順,不是簡單地贍養父母,而是需要孝敬父母。有禮才有敬,有敬才能稱得上孝。
“禮”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聯結,更是社會關系的規范;父子、兄弟、朋友之間都要遵守禮。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顏回死了,他的父親請求孔子賣掉自己的車子給顏回買一個外槨,但是孔子拒絕了。因為周朝的禮規定當過大夫的人在公眾場合必須要有車,如果孔子賣掉了自己的車子那他就要步行,但是這不符合周禮,所以孔子為了遵循周禮,拒絕了顏路的請求。雖然顏回死了,孔子非常悲慟,但是他還是堅持禮儀規則,維護禮制。
禮是社會的規范,我們不能為了關懷他人,就放棄禮制,也不能空有禮制而不近人情。在儒家倫理中我們是在遵循禮制的基礎上孝順父母,關愛朋友,禮是社會的規范,我們不能為了關懷他人,就放棄禮制,也不能空有禮制而不近人情。“禮”和“仁”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兩者缺一不可。
(三)國家管理
仁和禮的緊密聯系也體現在國家層面上,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好的德行能夠幫助君王治理好國家。“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如果君主用刑法來管理百姓,百姓會不斷涌現犯罪行為。但是如果君主用禮制來教化民眾,令民眾知道規則禮制,懂羞恥,明白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那么犯罪的概率會大大地減少,社會會太平許多。那么什么樣的禮制可以教化百姓呢?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這意味著作為君主就應該做君主應該做的事情,而作為臣子就應當履行臣子的義務,父母就應該做到父母應該盡的職責,孩子也只應該做孩子該做的事情。在孔子看來,人們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他們所應該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春秋戰國時期,舊的政治秩序和禮儀制度趨于崩潰,禮崩樂壞,名分顛倒,犯上作亂的行為屢見不鮮。社會中出現混亂不堪的現象就是因為缺失了禮的約束,造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盡不到父的義務,子盡不到子的義務。所以最終孔子提出“克己復禮”,大力提倡恢復周朝的禮制,重新建構政治秩序,讓人們了解自己的角色與定位,以此來約束大家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中,君對于臣來說是高貴的,臣對于君來說是低賤的,父親對于兒子來說應該是尊,子對于父親來說則應該是卑。孔子恢復周禮就是想讓人們清楚這種高低貴賤、上下尊卑是不能更改的人倫之道,每個人都應該遵從這種禮,并且按照各自在社會中所處的相應位置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孔子認為治理國家必須以道德教化為根本,同時君主也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他認為的治國應該是禮治思想和為政以德相互統一的體系。所以,儒家“仁”倫理中仁和禮是缺一不可的。
三、儒家“仁”倫理的關懷本質
從仁和禮的關系可以看出,儒家倫理不僅僅是關于“仁”的哲學,也是關于“禮”的哲學。“仁”體現的是人的內在品德,而“禮”是外在的行為規范。儒家的“仁”倫理不僅體現的是一種道德素養,內在的修養,也是成為圣人的重要標準。但是空有“仁”沒有外在的禮制來約束,那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仁”。所以儒家的“仁”倫理也是關于“禮”的倫理。
儒家倫理和關懷倫理的根本區別在于儒家倫理體現的是“禮”基礎上的等級人倫,而關懷倫理體現的是女權主義視域下的自由平等。在儒家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儒家的關懷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的親疏有別,貴賤有序。以家族宗親為根基,以人的倫常為條件,以尊卑貴賤的宗法等級為原則的愛人。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是不一樣的。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主對臣下要以禮相待,臣下對君主要顯示忠誠。不同關系的人,他們之間所體現的愛的方式和內容也是不一樣的。在當時體現在的最明顯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關系,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以,這種關懷是一種帶有明顯強制壓迫因素的等級系統。
而關懷倫理建立在女權主義運動的基礎之上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觀念,關懷倫理的提出者吉利根認為道德理論不僅是男性的而是整個人類的道德發展,女性應當具有屬于自己的道德體系,即關懷。關懷倫理的立足點是兩性之間的差異,在關懷倫理看來,兩性之間存在著心理發展,道德思維模式、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異,而對于女性來說更傾向于關懷,因為女性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時候,更容易產生幫助別人,關懷別人的情感。所以,“婦女的不同聲音體現出關系倫理學的真理,體現出關系和責任之間的聯系。”[6]關懷倫理是一種源于人的內在情感的自然關懷,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他人的關懷,所有人也可以擔當起關懷他人的責任。所以,關懷倫理是將人類看成是道德平等的成員,關懷倫理強調差異,關注責任和關系,追求公正和自由平等。
一言以蔽之,儒家“仁”倫理和關懷倫理雖然都體現出了關懷的指向,但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儒家中的“仁”不僅體現的是一種好的品德,更是在“禮”的基礎上的具有等級秩序的愛有差等的關懷。而關懷倫理的目的則是追求政治道德上的平等和公平。所以,從本質意義上看,儒家“仁”之倫理不同于關懷倫理。
參考文獻:
[1]Li Chenyang.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 and the Feminist Ethics of Care:A Comparative Study[J] .Hyp atia. February 1994.
Vol 9. Issl.
[2]范偉偉. 儒家“仁”之倫理與關懷倫理可否兼容?——關于這場爭論的評述[J].倫理學研究,2009(3).
[3]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171.
[4]Noddings Nel.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86.
[5]論語譯注[M]. 楊伯峻,楊逢彬,譯,注.長沙:岳麓書社,2009.
[6][美]卡羅爾·吉利根.不同的聲音[M].肖巍,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