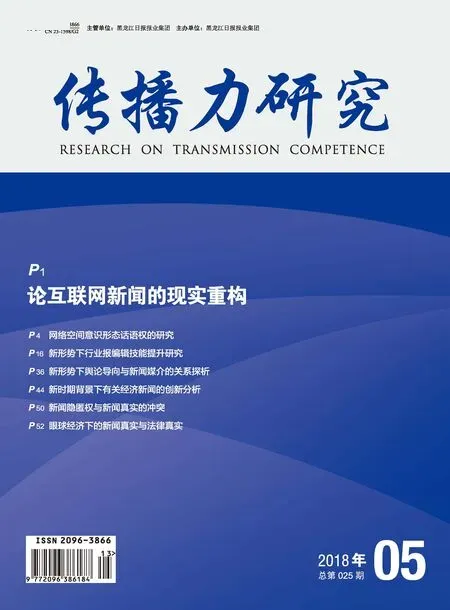“似花還似非花”
——以《我的前半生》為例淺析電視劇改編原則
馮譯萱 天津師范大學
一、似花還似非花
中國古典文學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中包括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兩大部分,是本土藝術的實踐和理論的有機統一。《藝概》是劉熙載對自己歷年來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訂。他的寫作目的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觸類旁通的目的。本文選取了《藝概—賦概》中的一些文論來進行電視劇改編的分析,用文化的主體性將中國古代文論與影視劇結合,以期我國影視劇能有更好的發展。
劉熙載在《藝概》中提出了“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的理論命題。他說“按實肖像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詩,可移之賦。”所謂“象物”就是對外界的“物”的描繪,不僅僅限于自然景觀,客觀加以臨摹,真實的再現景物。同時還需要借助創作者自身的生活閱歷及經驗進行想象、虛構。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影視劇改編亦是如此。既要以小說作品為基礎,又要發揮編劇的審美思想以及結合視聽語言的特殊性。在兩者的辯證關系中,要變現出“不似之似”或“不似似之”,既要與原著相似,又要不相似,在似與不似之間才能鍛造出精品。
劉熙載把握了這一藝術規律,他的文藝批評往往是一語破的。如他在《詞曲概》中所說:東坡《水龍吟》云“似花還是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所謂“不離”就是不脫離客觀事物,所謂“不即”就是不膠柱于和局限于客觀現實的物象本身,而在似與不似之間。要離形得似而反對襲其形似,這就是他所說的“似花還似非花”的本意。
二、忠于原著——不離
影視劇改編多選取于小說題材,因為二者在敘事上的共通性使二者的結合成為大勢所趨。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改編自亦舒的同名小說,而亦舒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又是改編自魯迅筆下的《傷逝》。三代子君,都經歷了愛情關系的變化,結局同樣是遭遇拋棄。
亦舒是香港都市言情小說家,亦舒認為子君的婚姻悲劇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她對丈夫的過度依賴,喪失了自我意識。在這一點上,編劇秦雯和她不謀而合,將子君刻畫成了一位矯揉造作的典型上海小女人的腔調。兩代子君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讓觀眾看完又氣又有一絲心疼,可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后作家和編劇更加著重于子君離婚后的精神重建,婚變后她走出家庭重返社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人生的價值。電視劇尊重了原著的主題精神,同樣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卻又立足于當下進行適當改編滿足于視聽媒介要求。“可謂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一句話深刻點出了當今影視劇在改編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既要忠于原著又要有所創新,才能贏得收視、口碑雙連冠。
三、創造性改編——不即
小說創作雖然和影視劇創作都隸屬于文學體裁,但由于傳播媒介的不同,兩種體裁在表現方式上也各有不同。小說是通過紙質媒介傳播,需要讀者通過個人想象力與生活經驗來二次創造人物形象。而影視劇則是通過電視媒體,將視聽感官真實呈現給觀眾的。悉徳-菲爾德曾說,“一部小說通常涉及的是一個人的內在生活……在小說中,你可以用一句話、一個段落、一頁稿紙或一個章節,來描寫人物的內心獨白、思想、感情和印象等等,小說常常發生在人物的腦海里”,而影視作品“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體的細節……一個用畫面來講述的故事,它發生在戲劇結構的來龍去脈之中”。所以,在進行影視劇改編時編劇們往往會根據影視劇的特殊性對小說劇本進行改編。
人物和情節的再創造是電視劇《我的前半生》的一大重要特色,編劇秦雯對于人物進行了不小的變動。在保留了主要人物不變的條件下,大膽刪減了小說中次要人物,同時為了保證情節的沖突性與節奏性,增添賀涵、白光等人物,增強了電視劇的可看性,也滿足了不同受眾群體的情感訴求。人物是敘事藝術的核心,影視劇改編過程中,人物性格也要符合劇情的設定與其自身的邏輯心理。
影視劇改編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編劇要將小說敘事化具象為造型化,主題和立意要符合當下的時代發展特征,人物和情節的設定要符合主題、貼近實際。要是做到這些,必須與原著拉開一定的距離,又不能完全脫離原著內容,似近非近似熟非熟,須如禪家所謂不粘不脫,不即不離,乃為上乘。
[1]王錕,胡智鋒.中國電視劇的話題性研究[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7(01).
[2]黃敏.比較魯迅《傷逝》與亦舒《我的前半生》女性觀之異同[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03).
[3]李秀清.時代、環境與人物命運——《傷逝》和《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命運的比較[J].名作欣賞,2007(14).
[4]梁文晶.似花還似非花——淺談詠物詩不即不離的寫作技巧[J].科教文匯(中旬刊),2010(07):57+67.
[5]朱光潛著.談文學[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