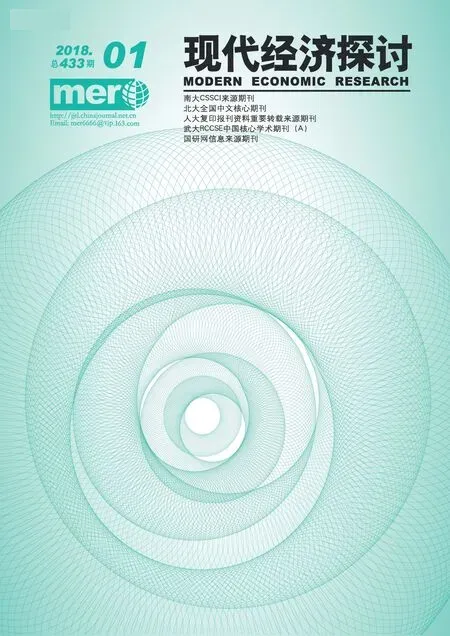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促進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嗎?*
唐保慶 韓守習 陳啟斐
一、 引 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升,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焦點是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優化問題(夏杰長,2008;宣燁和余泳澤,2014),服務業規模擴張基礎上的結構優化不僅僅反映了服務業自身發展的技術水平和“含金量”,而且是我國實現服務業高端化發展和走向服務業強國不可逾越的重要環節,這甚至有助于增強我國在全球服務經濟發展中的“話語權”。然而反觀我國服務業發展現實卻發現,我國的服務業發展呈現出“低端慘烈廝殺、高端嚴重短缺”的結構性失衡,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有效供給遲遲無法跟上。因此,我國服務業領域的結構性失衡已經充分展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服務業領域實施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注重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甚至應當成為經濟結構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影響服務業結構變動的諸多因素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一個尚未引起學術界足夠重視的制度性因素,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兩大類行業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敏感度差異,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作為主要受益者會在整個服務業部門中的占比有所上升,服務業內部結構由此得以升級。當然,在注意到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同時,也應當考察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可能對服務業結構升級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由于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通過市場擠出效應和壟斷勢力效應強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在服務業市場中的既得利益,這不僅會削弱在位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競爭,也會降低在位企業的后續創新動力,這反而不利于服務業結構升級。
從上述邏輯來看,知識產權保護是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制度因素,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促使服務業實現結構轉型和技術升級的關鍵“抓手”,更進一步地,只有通過實施“最適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才能夠在更大限度上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因此,本文將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機制,并且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增加值占整體服務業增加值的比例刻畫服務業內部結構,運用“距離指數”和“鐵路密度”構建的工具變量進行經驗檢驗;此外,本文還將研究“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潛在阻礙作用,以此尋求意在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
二、 文獻綜述
現有關于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的文獻大多沿著三條路徑開展研究:一是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基于一定標準劃分的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變動狀況;二是對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進行跨國比較研究;三是運用計量方法研究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因素。
1.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的統計分析
Wieczorek(1995)從就業維度較早研究了服務業內部結構的演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提高,美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在整體服務業部門就業人數中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以年均近1%的增長率上升,這是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的重要標志。Langhammer(2008)研究了俄羅斯的服務業結構變遷,發現俄羅斯2000年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整個服務業中的占比相比于1990年提高了7.6%。夏杰長(2008)的研究表明,總量增長緩慢與結構性缺陷兩種矛盾相互交織共同制約著我國服務業的增長,重點發展生產者服務業是推動我國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政策著力點。馬風華和李江帆(2014)運用偏離-份額法把服務業結構變動分解為服務業結構合理化和服務業結構高級化兩個方面,并且認為服務業結構合理化比高級化更加能夠促進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而且“結構獎賞”和“結構負擔”效應同時存在。上述部分文獻較為完整地刻畫了我國服務業近年來內部結構的典型化事實,指出了我國距離服務業大國之間存在的明顯落差,同時運用“標準化”、“合理化”以及“高級化”等指標對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進行了更加多維的解讀,把服務業內部結構的特征事實分析引向深入。
2.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的跨國比較研究
Broadberry & Gupta(2010)比較了印度與英國的服務業內部結構,認為印度在服務業領域的創新資源投入不足是印度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比落后于英國的重要原因,進而指出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是提升服務業競爭力的必由之路。程大中(2008)的研究發現,中國帶有較高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本含量的生產者服務業在整個服務業部門中的占比不足,表現出服務業結構低下的特征,而且這在很大程度上由社會誠信、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制的約束所引致。李江帆和朱勝勇(2008)運用投入產出法比較了“金磚四國”的生產者服務業結構,發現我國勞動密集型生產者服務業的比重較大,知識密集型生產者服務業的比重偏小,通過提高知識密集型生產者服務業的比重來優化生產者服務業的結構是提高我國生產者服務業競爭力的關鍵。黃莉芳和楊向陽(2015)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方法比較了中美兩國服務業內部結構,認為我國服務業存在投入服務化程度低和服務業內部結構低端化等嚴重問題,這是我國走向服務業強國路途中必須突破的關鍵屏障。這些運用跨國比較所開展的研究基本上都揭示了我國服務業發展內部結構的相對滯后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差距,盡管不同國家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了國家之間難以進行直接的橫向比較,但是這些研究清晰地刻畫了我國在服務業結構方面與發達國家的落差,并且為我國的服務業結構優化提供了必要的國際經驗與啟示。
3.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因素研究
在清晰地認識我國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的基礎上,研究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因素則成為了一個關鍵點,這對于實施服務業行業結構優化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裴長洪和李程驊(2010)認為,城市經濟轉型與服務業結構升級是一個系統性的互動過程,提高城市的“經濟容積率”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突破性發展是一個協同并進的過程。Evangelista(2013)運用投入-產出法研究了OECD國家服務業的內部結構差異,認為制造業的生產率水平直接影響了對高端服務業的需求水平,進而形成了服務業內部結構跟隨制造業生產率變動的特征。王智淵和馬晶(2014)研究了服務業專業化集聚與服務業內部結構演進之間的關系,認為服務業專業化集聚能夠推動生產者服務業增長快于其他類型服務業增長,由此促使生產者服務業成為服務業部門中的主導產業,有利于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倪紅福和夏杰長(2015)基于中國省級投入產出表的定量研究指出,推進城鎮化、拉長制造業產業鏈、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以及服務業開放是推動生產者服務業增長以及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突破口。上述研究從各類經濟因素、城市發展因素以及服務業開放政策等多元視角研究了服務業行業結構升級的驅動力,這表明服務業行業結構的升級過程既包含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的經濟規律,也需要外部政策的配合與推進,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借助于積極的政策推動有利于加快服務業的結構升級。
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以下兩點:第一,從知識產權保護這一新穎的制度因素視角研究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機制,這不僅突破了傳統的經濟因素視角,而且尋找到了與服務品的無形性與高知識屬性高度匹配的制度視角;第二,研究“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并且檢驗我國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強度是否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理論上的“最適強度”,這對于我國審慎掌控知識產權保護的適宜強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 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框架
從理論上來看,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會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變化呈現出復雜的非線性傳導機制。下文將分別從線性影響和非線性影響兩個維度進行深入分析。
1.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線性影響理論機制
(1) 技術創新效應引致服務業結構升級。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目的是維護創新者的智慧投入和知識創造,以此確保創新者能夠在一定的時期中獲得創新活動所產生的經濟回報,并且由此塑造鼓勵創新、激勵創造的良好市場環境(Hodgson,2015)。從知識密集型服務品本身的特點來看,其無形性、高知識屬性和低邊際成本恰恰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全匹配,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能夠極大地受益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進而在整個服務業中的比重得以提高,服務業結構實現升級。首先從無形性來看,服務品的無形性特征決定了此類產品被非法競爭者進行剽竊和模仿的隱蔽性較高,這完全不同于實物商品在遭遇盜竊的過程中需要發生實物商品的空間轉移,在此情形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必要性更高。其次從知識屬性來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區別于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主要特點即為知識屬性,由于此類服務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創意、智慧和知識的投入,而這些關鍵要素又極易被剽竊和惡意模仿,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增長至關重要。最后從低邊際成本來看,由于知識密集型服務品的邊際成本較低,前期的創新投入一旦獲得市場認可,產品的規模提升會不斷降低平均成本(Rubalcaba et al.,2016),但是其前提是具備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發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功能。綜上所述,知識密集型服務品無形性、高知識屬性和低邊際成本的特點決定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夠促進其快速發展,并且提升在服務業部門中的占比,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
(2) 資源跨國流入引致服務業結構升級。在開放條件下,我國服務業領域正在逐步對外開放,這是我國本土企業從國外優秀服務業企業獲取技術溢出的絕佳時機。國外服務業企業的進入決策一方面與東道國開放政策有關,另一方面還與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強弱有關(Khoury & Peng, 2011)。當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弱時,競爭力較強的國外服務業跨國公司擔心其核心技術或專利被剽竊,這會極大地挫傷服務業跨國公司進駐東道國的積極性,也就是說,松散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會導致服務業跨國公司從主觀上放棄進入東道國的機遇。不僅如此,隨著世界各國關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不斷加強,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已經成為全球共識(Woo et al.,2015),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幾乎成為各國開展合作的“國際通行證”,一國只有在接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相關條約前提下,甚至還需要與特定國家簽署額外的知識產權條約,才可能開展經濟領域的合作談判。從這一角度而言,東道國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很可能導致服務業跨國公司由于受到國家之間經濟談判方面的羈絆在客觀上難以進入東道國。所以,我國只有在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夠引入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新興服務業經營模式和專利,并且促使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技術溢出,進而推動我國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升級。
2.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非線性影響理論機制
(1) 市場擠出效應阻礙服務業結構升級。在知識產權保護不斷得到加強的過程中,創新企業不僅可以通過創新激勵效應以及技術溢出效應獲得快速發展,享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所帶來的經濟成果,而且還成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領域的既得利益者。倘若知識產權保護措施進一步加強,那么新進入市場的服務業企業其創新產品只要與在位服務業企業的產品有些許的近似,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就有可能判定新進入企業存在剽竊或者非法模仿行為,新進入企業將會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Maskus,2008)。由此可見,過于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很容易使在位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獲得較強的市場勢力,并且阻礙了新進入服務業企業的發展,甚至有可能把新進入企業擠出服務業市場。不僅如此,具有進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市場可能性的潛在企業也容易受到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威懾而最終放棄進入服務業市場,這對于需要多元化創新和百花齊放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市場而言極其不利,整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市場的創新動力受阻。與此同時,由于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嚴苛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不敏感,或者說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難以阻礙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這會使得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整個服務業市場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服務業結構升級受阻。
(2) 壟斷勢力效應阻礙服務業結構升級。在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下,在位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不僅能夠對新進入服務業企業和潛在進入的服務業企業產生擠出效應,而且自身在研發與創新活動中的決策也可能發生變化。對于任何一個企業而言,創新和研發活動都存在一定的風險,倘若創新活動的預期收益小于創新成本投入,企業通常會放棄創新。在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件下,由于在位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較小,延續現有的經營模式依然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也就是說,在位企業無需從事具有一定風險的創新活動也能夠獲得較好的成長,因此其進一步研發和創新的動力趨于弱化。由此,過強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一方面導致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市場內部的創新資源長期無法得到補給,另一方面導致市場外部的創新資源無法進入,這自然會阻礙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服務業部門中占比的提高,不利于服務業結構升級。
四、 經驗檢驗模型與工具變量設計
1.計量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PR)作為計量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主要考察該變量的回歸系數。同時在模型中納入由現有研究文獻識別出的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其他諸多變量,以盡可能確保計量模型的一般性和核心解釋變量的外生性。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Upgradingi,t=β0+β1·IPRi,t+β2·Humani,t+β3·Marketi,t+β4·Openi,t+β5·Path_depi,t+μi+λt+δi,t
(1)
其中,Upgradingi,t表示服務業結構升級,IPRi,t表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Humani,t表示人力資本水平,Marketi,t表示市場化程度,Openi,t表示開放度,Path_depi,t表示路徑依賴,μ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λ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δi,t表示隨機擾動項。


(2)
從理論上來說,由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能夠受益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因此在位企業很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推動政府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服務業結構升級之間很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這自然會導致計量模型的內生性問題。為此,我們綜合運用OLS和2SLS方法進行估計,從地理因素這一外生因素構建工具變量(在下文做詳細說明),同時為了做穩健性回歸,我們運用了N-1變量方法,即除了某一省份以外的其他省份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平均值及其平方項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而開展2SLS估計。
2.變量說明
(1) 服務業結構Upgrading。本文首先把服務業各行業按照要素密集度劃分為知識密集型和非知識密集型兩大類,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增加值/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反映服務業的內部結構狀況。本文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教育業。數據來源于各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的歷年統計年鑒。
(2) 知識產權保護強度IPR。我們借鑒韓玉雄和李懷祖(2005)的方法,以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的實際執行效果乘以G-P指數,其結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強度。考慮到本文所運用的省際面板數據特性,我們主要基于各省份的非服務業人均GDP*非服務業人均GDP由人均GDP減去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得到,該指標不同于韓玉雄和李懷祖(2005)的人均GDP指標。之所以我們對此有所調整,主要是考慮到非服務業人均GDP中已經扣除了服務業增加值這一成分,這就能確保計算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時不會引入內生性。、成人識字率、律師比例、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時間以及是否為WTO成員等5個計算指標作為實際執行效果的計算依據,對于前面三個指標,各省份的數據并不相同,但是對于后面兩個指標,由于各省份都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其數值是相同的。*由于該指標的計算過程十分復雜,具體過程在此省略并且備索。該指標所涉及的數據來自于各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的歷年統計年鑒、教育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律師年鑒》。
(3) 人力資本水平Human。從理論上來說,人力資本是開展創新活動的核心要素,尤其對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這類以智慧和創新為核心競爭力的產業而言,人力資本更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考慮到數據采集方面的問題,本文采用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表征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具體而言,我們設定小學教育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和中專為12年,大專及以上為16年。該指標所涉及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
(4) 市場化程度Market。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過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來促進創新資源流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領域,進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中國市場化指數》全面刻畫了我國各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動態變化,我們直接從中獲得市場化程度的數據。
(5) 開放度Open。一國開放度越高,國內企業越容易獲得國外R&D溢出,本文用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除以GDP反映開放度。從理論上來說,對服務業發展產生影響的開放度應當用服務品進出口總額或者服務業FDI除以GDP表示,但是我們考慮到,用“服務品進出口總額(服務業FDI)/GDP”表示開放度可能會導致控制因素過度這一計量方法問題,因為前文在闡述IPR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時,其傳導機制包括服務業跨國公司是否會在特定IPR強度下進駐中國,因此我們改用“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GDP”表示開放度。數據來源于各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的歷年統計年鑒。
(6) 路徑依賴Path_dep。從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實踐的必要性來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規劃和政策通常具有一定的延續性,投資規模和領域也具有一定的慣性,以避免政策的頻繁切換所引發的經濟波動和就業不平穩,這使得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征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從邏輯上來看,路徑依賴也會影響服務業的內部結構演化,并且熨平其他沖擊服務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所帶來的劇烈影響。我們在此用被解釋變量服務業結構的滯后1期項反映路徑依賴的效果。
3.尋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工具變量
對于中國而言,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實際上產生于改革開放時期,而且這一時期制度構建的初衷是源于1979年的中美貿易協定。此后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尤其是建設經濟特區和設立沿海開放城市等重大舉措更是把市場經濟推向了新的高潮,建設經濟特區和確立沿海開放城市實質上是要在更大的自由空間里實現由市場來主導資源的配置,激勵創新和鼓勵個人理念、創意的自由綻放成為了時代的主題曲,這些特定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人們重新審視技術、創造和創新的內在價值,也引發了人們對技術、專利、個人財產進行保護以及建立產權制度的深入思考。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是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別于其他區域的特殊經濟區域,它們在作為經濟“試驗田”的同時也承擔了法制“試驗田”的任務,其司法質量和契約執行效率均高于其他地區(黃玖立等,2013)。因此,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對于當地以及全國后期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也為本文尋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工具變量提供了現實依據和啟示。
本文借助于各省份分別到北京、5個經濟特區以及14個沿海開放城市共計20個城市(地區)的最短空間距離(下文簡稱為“最短空間距離”)構造“距離指數”(Distance Index,DI)*5個經濟特區分別為:深圳、海南、廈門、珠海和汕頭,14個沿海開放城市分別為: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具體的構造方法詳見下文。,為構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工具變量奠定基礎。其理由是,5個經濟特區以及14個沿海開放城市是中國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最為充分的地區,是經濟活動最具有創新活力的地區,也是推崇依靠個人能力創造社會財富的地區,因此這些地區的企業和個人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具有較為前沿的認知。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是各項政策與制度的發源地,在獲得重要信息方面以及在貫徹國家的意志、戰略方針等問題上都要領先于國內其他區域,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真正推進也比普通地區更加堅定。因此,某一個省份的最短空間距離值越小,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有可能越高,故距離指數與各省份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此外,服務品一度被認為不可貿易品,即使某一省份離經濟特區或者沿海開放城市的距離較短,該省份的服務業也很難得益于臨近經濟特區或開放城市的快速發展。因此,距離指數也滿足外生性要求。
對于距離指數的計算,我們借鑒黃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海外市場接近度”的計算方法。由于本文的數據樣本為包含了時間維度的省際面板數據,但是上述構建的距離指數是僅僅隨橫截面而變化、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選取一個隨時間變化的、能夠反映距離指數涵義的外生變量與之相乘。為此,我們選取第t-1年的“鐵路密度”這一隨時間變化的變量與距離指數相乘得到既隨橫截面而變化又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作為第t年的工具變量。鐵路密度是指從某一省份到離其最近的20個地區(具體包含北京、5個經濟特區以及14個沿海開放城市)途中經過的所有省份的鐵路密集度。由此我們得到IVi,t=DIi×railwayi,t-1這一工具變量,鐵路里程數據來源于《中國交通運輸統計年鑒》。
本文接下來將運用1997-2015年27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經驗檢驗*由于受到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我們刪除了貴州、西藏、甘肅和新疆等4個省份的樣本。。
五、 檢驗結果與分析
1.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總體樣本檢驗
從表1的結果來看,知識產權保護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結構升級,這一結論在表1的5個回歸方案中都成立,擬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推動我國服務業由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進而實現結構升級的重要政策舉措。前文的理論研究表明,知識產權保護主要通過技術創新效應以及資源跨國流入效應等渠道促進服務業的結構升級,這與Woo et al.(2015)的研究結論相似,他們認為知識產權保護通過激勵創新和資源跨國流入渠道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對于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而言,創新驅動和進一步開放是推動經濟戰略轉型的關鍵,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傳導機制則是我國重大經濟戰略在服務業領域中的具體體現,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實施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革源頭。
2.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分地區檢驗
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資源稟賦特征等因素決定了地區間的服務業內部結構存在差異,而且各地區由于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執行力度不同會深刻影響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強度差異。因此,本文接下來以東部地區作為基準組,通過加入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虛擬變量的方法進一步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地區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表2中的回歸方案(1)顯示,Central和West變量均顯著為負,說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服務業結構升級方面顯著落后于東部地區,從邏輯上來說,這可能是由各地區的產業傳統、各類要素稟賦以及開放性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綜合所致。回歸方案(2)-(5)顯示,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依然顯著,回歸結果十分穩健。各回歸方案還顯示,IPR*Central和IPR*West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強,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服務業結構升級方面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不斷拉大。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這兩個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均遠遠低于東部地區,通過計算發現,在樣本期間內,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知識產權保護的平均強度比東部地區低75.4%和82.8%,中西部地區過于松弛的知識產權保護對于兩個地區服務業結構升級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而且拉大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我們通過進一步考察還發現,由于IPR*Central和IPR*West的回歸系數均為單獨相對于東部地區這一基準組而言的,對兩個回歸系數進行比較之后發現,在中西部地區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過程中,西部地區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效果比中部地區更差,其中的原因也在于西部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弱于中部地區。為了嚴謹地比較知識產權保護對中西部地區服務業結構升級效果的差異,我們以中部地區為基準組,設定西部地區虛擬變量進一步回歸,回歸結果同樣證實了上述結論,即由于西部地區知識產權保護弱于中部地區,其服務業結構升級效果差于中部地區*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我們省略了此處的擬合結果。。

表1 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總體分析)
注:表中的OLS回歸中之所以選取固定效應模型(FE)是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所確定;***、**、*分別表示在1%、5%、10%水平上顯著;( )內的數值為擬合系數的穩健標準誤,[ ]內的數值為檢驗統計量的p值。
3.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非線性影響檢驗
本文的理論研究指出,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應和資源跨國流入效應等渠道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市場擠出效應和壟斷勢力效應阻礙服務業結構升級,因此“最適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夠最大限度地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平方項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非線性影響,并且計算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最適強度”。結果見表3。
表3的結果顯示,IPR的擬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研究結論依然成立。同時,IPR2的擬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具有先促進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即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初始階段,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以正向促進為主,進入后期階段,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以反向阻礙為主。在表3的五個回歸方案中,每一個回歸方案都可以計算出一個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為了降低測算誤差,我們取5個回歸方案中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的平均值,即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2.818時,其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凈效應”達到最大。根據樣本期間的統計分析發現,我國2015年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強度為0.776,遠遠低于2.818這一“最適強度”,這表明我國目前仍然處于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階段。當然,需要警惕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越發展階段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反而不利于經濟目標的實現。以美國和西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對我國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出了詰責,并且通過相關的談判要求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但是本文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確定應當以該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目標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一味地滿足發達國家和地區提出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反而會對自身的經濟發展形成阻礙,本文的研究為我國制定適宜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供了理論邏輯和經驗證據。

表2 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地區差異分析)
注:同表1。

表3 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非線性分析)
注:同表1。
由于知識產權保護變量(IPR)是本文最核心的解釋變量,為了檢驗研究結論的可信度,有必要運用其他測度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指標做穩健性檢驗。為此,我們總共選取了3個不同的IPR指標,具體為: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數據庫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標(記為IPRWGI)、加拿大Fraser機構提供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標(記為IPREFW)以及樊綱和王小魯歷年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標(記為IPRFan)*由于本文的樣本期間為1997-2015年,IPRFan的最新數據只更新至2014年,所以2015年的缺失數據是基于1997-2014年的數據運用回歸方法推算而得到。。由于IPRWGI和IPREFW是國家層面的數據,因此有必要轉化為省級層面的數據。我們用專利侵權和其他糾紛結案量,查處冒充專利行為和假冒他人專利行為結案量兩個維度的指標計算各省份的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強度。回歸結果表明,運用不同知識產權保護指標的回歸結果與原始回歸結果十分吻合,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可靠的*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報告具體的回歸結果,此處的回歸結果備索。。
六、 研究結論、政策啟示與不足之處
本文從知識產權保護視角研究了服務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機制,并且運用省際面板數據開展了經驗檢驗,得到了以下重要結論和政策啟示。
(1) 知識產權保護通過推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增長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結構升級。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關鍵在于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為代表的匯聚智慧、創意和理念等高級要素的高端服務業的爆發式增長(杜運蘇等,2016),而智慧、創意和理念這些核心要素的無形性和非競爭性特征決定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激發創新者的創新意愿。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起步較晚,盡管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于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督促而被動地實施了大量完善措施,但是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提升我國服務業競爭力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必由之路。在此過程中,不僅需要國家制定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而且地方政府也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執行力度,并且輔之以宣傳和教育等措施使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深入人心,由此形成宏觀、中觀以及微觀層面多維度和立體式的政策體系。
(2) 知識產權保護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由于受制于較為松弛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兩個地區的服務業結構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趨于擴大。在全球制造業產業轉移浪潮中,中西部地區可以借助于服務業全球轉移的有利時機縮短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包括服務業的規模擴張和結構升級。首先,中西部地區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本,尤其武漢、西安和蘭州等地是著名高校的云集之地,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吸引高端人才在當地安家落戶,甚至吸引其他地區的優秀人力資源進入(張為付和張文武,2016);其次,中西部地區可以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措施打造良好的創新環境,維護健康的市場秩序,由此激發當地的創新活力,同時吸引優秀人才的流入,實現人力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
(3) 知識產權保護與服務業結構升級之間呈非線性關系,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呈現先揚后抑的“倒U”型特征。雖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能夠通過技術創新效應和資源跨國流動效應等渠道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但是政策制定部門應當考慮到其“兩面性”特征。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強度依然低于理論“最適強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所產生的正面效應大于負面效應,因此相應的政策措施應當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主。此外從我們的企業調研情況來看,被訪企業的多位高層管理者均認為我國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削弱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的創新熱情。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應當成為主旋律,尤其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尤為必要。
1. Broadberry, S. , and B. Gupta.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India’s Service-led Development: A Sectoral Analysis of Anglo-India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1870-2000.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 2010, 47(3):264-278.
2. Evangelista, R., M. Lucchese, and V. Meliciani. Business Services, Innovation and Sectoral Growth.StructuralChange&EconomicDynamics, 2013, 25:119-132.
3. Hodgson, G. M. Much of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Devalues Property and Legal Rights.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 2015, 11(4):683-709.
4. Khoury, T. A. and M. W. Peng. Does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ad to More Inbound FDI?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ournalofWorldBusiness, 2011, 46(3):337-345.
5. Langhammer, R. J. Sectoral Distortions and Service Protection in Russia: A Comparison with Benchmark Emerging Markets and EU Accession Candidates.EasternEuropeanEconomics, 2008, 46(6):70-83.
6. Maskus, K. 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Services.JournalofIndustryCompetition&Trade, 2008, 8(3):247-267.
7. Rubalcaba, L., D. Aboal, and P. Garda. Service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 2016, 52(5):607-626.
8. Wieczorek, J. Sectoral Trends in World Employment and the Shift toward Services.InternationalLabourReview, 1995, 134(2):205-226.
9. Woo, S., P. Jang, and Y. Kim.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atented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Value Added: A Multi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Technovation, 2015, s 43-44:49-63.
10. 程大中:《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及影響——基于投入-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經濟研究》2008年第1期。
11. 杜運蘇、丁靜、陳鑫:《醫藥制造企業的融資難與所有制歧視有關嗎——基于CCER、CSMAR數據的實證分析》,《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12. 韓玉雄、李懷祖:《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科學學研究》2005年第3期。
13. 黃玖立、李坤望:《出口開放、地區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
14. 黃玖立、吳敏、包群:《經濟特區、契約制度與比較優勢》,《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15. 黃莉芳、楊向陽:《中、美現代服務業內部結構演變趨勢比較——來自投入產出表的經驗證據》,《世界經濟研究》2015年第3期。
16. 李江帆、朱勝勇:《“金磚四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與影響——基于投入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08年第9期。
17. 馬風華、李江帆:《城市服務業結構變動與生產率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上海的經驗數據》,《上海經濟研究》2014年第5期。
18. 倪紅福、夏杰長:《區域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結構及其與制造業關系研究——基于中國省級投入產出表的分析》,《山東財政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19. 裴長洪、李程驊:《論我國城市經濟轉型與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20. 王智淵、馬晶:《服務業專業化集聚與服務業內部結構演進》,《產業經濟評論》2014年第4期。
21. 夏杰長:《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推動我國服務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途徑》,《經濟研究參考》2008年第4期。
22. 宣燁、余泳澤:《生產性服務業層級分工對制造業效率提升的影響——基于長三角地區38城市的經驗分析》,《產業經濟研究》2014年第3期。
23. 張為付、張文武:《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加、減、乘、除”策略研究——以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為例》,《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