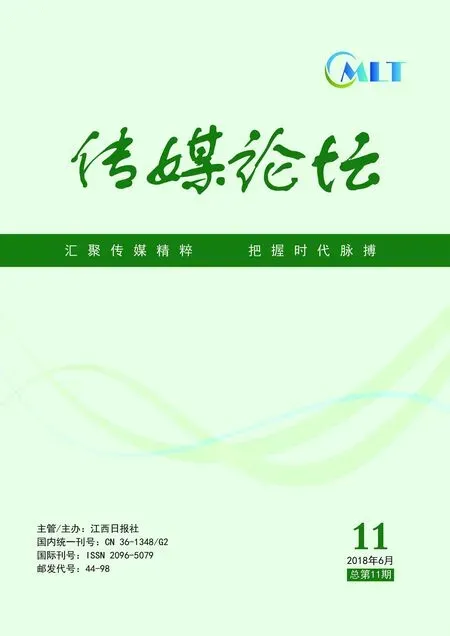論“無紙化”時代的閱讀
冀彩霞
(世界圖書出版西安有限公司,陜西 西安 710001)
電視的普及、互聯網的興起無一不給傳統出版業帶來巨大沖擊,傳統出版的讀者的大量流失已經無可避免,傳統出版業在走下坡路也是不爭的事實。有專家按照目前出版業的發展模式預測,到2020年,全球電子書的銷售量將完全超越紙質書。更有人斷言電子書是繼造紙術、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之后的第三個世界圖書業的大變革。斷言或許會應驗,預言或許會成真,但很明顯,這些變革的背后都是商家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
一、“無紙化”時代逼近,我們的閱讀觀發生了變化
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人們的閱讀習慣也在改變。尤其是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心無旁騖地靜下心來去閱讀,或是有些曾經真心喜歡閱讀的人也往往在閱讀的路上迷失方向。即便他們想閱讀,也不是手捧書本,而是手握手機,很多時候,總能看見他們的手指在手機屏幕上劃來劃去,那速度和頻率已經遠非“一目十行”之功力所能企及。
古代就以“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作為奉勸人讀書之“金玉良言”,在我看來,此“金玉良言”依然適用于當下。現如今,很多人把讀書當作一種實現自我功利價值的敲門磚,讀書只是為了更好地生存,只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殊不知,讀書最忌急功近利,一旦心存功利,往往適得其反。如果讀書只是為了應付考試,那么,閱讀的快感從何而來?閱讀的興趣怎能不被扼殺?很多實踐證明,并非真心陶醉于書本、享受閱讀本身的人是不會從閱讀的過程里得到快樂的,因為他們不會閱讀、不懂閱讀,自然不會有收獲。
二、“無紙化”時代逼近,人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變化
21世紀的中國已全面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電子產品及與互聯網相關的數據產品已經占據了人們生活的很多空間和時間。就拿電子閱讀器來說,就有Kindle、漢王、BOOX、博閱、雷麥、奧克沃斯、亞馬遜、索尼、掌閱等十幾個品牌,對于他們各自的特點與優勢我暫且不做比較,就它們與書籍相比,其伯仲優劣則不說自明。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們都敵不過手機。據調查,在閱讀方式上,選擇紙質閱讀的人占近三成,超過七成的人選擇電子閱讀。其中,80.2%的人通過手機閱讀,其次是網絡閱讀占48.7%,電子閱讀器占15%,MP4、MP5等電子產品和光盤占4.2%。可見,中國人對手機的依賴程度已然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有一項數據調查顯示,英國的地鐵上80.2%的人會選擇利用在地鐵上的閑暇時間手捧一本書閱讀,而中國的地鐵上90%的人則會保持同一種姿勢——低頭看手機,所以就出現了一個熱詞“低頭族”。然而,這些低頭族中間又有多少人是在玩手游,又有多少人是在聊天,更有多少人是在手機上閱讀,據我觀察,在手機上閱讀的人可謂是少之又少!撇開閱讀內容不談,僅這種反差對比,就諷刺得厲害!“一份報紙,一杯茶”“伴著雨聲讀心愛的書”這些曾經實實在在與閱讀有關的事情于現在多半已經成了一種“意境”,可望而不可即。
如今的中國已經悄然逼近“無紙化”時代,“無紙化” “碎片化”閱讀深受人們的追捧,尤其是年輕人。筆者認為,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關系。“碎片化”一詞是描述當前中國社會傳播語境的一種形象性的說法,在傳播本質上是整個社會碎片化、多元化的一個體現,而后再通過網絡的形式呈現出來,實現“無紙化”。現在,如果讓一個普通人描述自己十幾年前對于媒體的接觸方式,他們可以用簡單的幾句話就可以描述得很清楚:白天看報紙,晚上看電視。但是在信息傳播進入網絡時代以后的今天,報紙要“包攬天下”的操作難度顯然非常大,書籍也是一樣,也就是說要辦一份讓所有讀者都喜歡的報紙或出版一本讓所有讀者都喜歡的書籍,那是天方夜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眾口難調”就成了網絡時代背景下的編輯、記者們普遍的哀嘆。
三、“無紙化”時代的閱讀以及閱讀的價值
筆者認為,傳播文化之于媒體,只是傳播內容不同而已;傳播內容之于載體,只是傳播方式不同而已;閱讀之于讀者,只是閱讀內容不同而已。可見,閱讀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的傳播,是一種社會文化,能體現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整體面貌。全民喜歡閱讀和全民拒絕閱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前者能使全民素質不斷提升,社會得以持續發展;后者會導致社會文化倒退,甚至使文化生態遭到嚴重破壞。與閱讀緊密相關的出版業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也正在一步步地進入數字出版時代。出版社、報刊社作為文化傳播機構正在面臨一次大的變革,處在其中的當事人或觀望,或徘徊,或緊跟時代步伐。
總之,我認為“無紙化”閱讀改變的是人們的閱讀方式,而閱讀本身以及閱讀的價值并沒有改變。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抱怨“全民不閱讀”,而是要制造更多更豐富的精神食糧,吊起全民閱讀的胃口,并非為讀書而讀書,更不是為了擁有某種高端的電子設備而被動閱讀。無論何種形式,不管哪種載體,閱讀本身就應該是人類文明傳承的重頭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