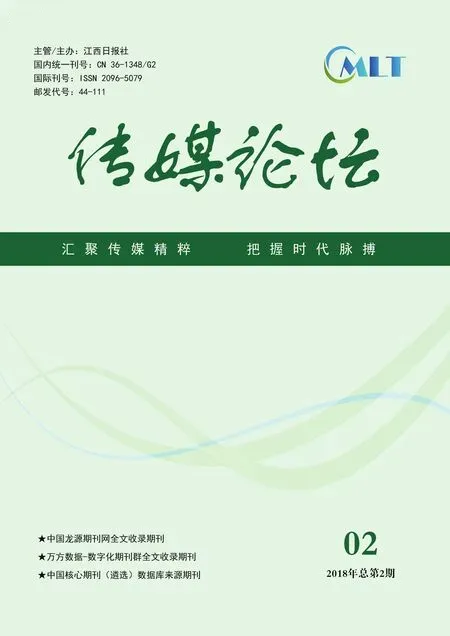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紀錄片發展的新趨勢
王 賡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一、引言
2012年,被業界與學界稱為“紀錄片品牌元年”,至此,中國紀錄片躍上新起點。紀錄片自誕生以來,一直被看作是“精英拍給精英看”的一門紀實電影藝術。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媒介技術的革新以及媒體融合進程的加速與推進,我國的紀錄片產業走向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紀錄片也呈現出了多種形態,播出平臺也在逐漸變化,不再局限于電視和電影媒介,很多新媒體或自媒體平臺成為了紀錄片的重要播放媒介。紀錄片就是通過拍攝現實生活中的影像并經過人為加工,將真實的人物、空間、事件等事實信息呈現在觀眾面前,將他們帶進新的世界之中,讓他們獲得全新的體驗。2012年至今,我國紀錄片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不僅以數量取勝,在質量、平臺、題材和觀念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在這種形勢和背景下,各級電視臺都在積極搭建播出平臺,拓展播出渠道,相繼推出了《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和《如果國寶會說話》等優秀且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說,我國紀錄片呈井噴式創新與發展,其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國家政策的支持、政府的導向,還有頻道和資金的支持,同時更要歸功于紀錄片創作人的共同努力。
二、從《我在故宮修文物》到《如果國寶會說話》看國產紀錄片的發展
我國紀錄片一直以來是電影市場上的冷門藝術形式,很多國產紀錄片都難以擺脫乏人問津的悲慘命運。自2012年被學界稱為中國紀錄片元年開始,我國紀錄片開始作為守望者逐漸復蘇并在電影市場上嶄露頭角,開始逐漸展示其社會價值。近幾年,我國紀錄片市場慘淡,但《舌尖上的中國》的出現卻成了叫好又叫座的紀錄片典范。緊接著,2016年,又一部力作橫空出世——《我在故宮修文物》,不僅獲得了全民關注,還成了新聞傳播學界研究的熱點。這些經典作品猶如時代的拋物線,能夠折射出不同地域的社會背景以及時代的變遷。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一部為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以修復古老文物為主題而創作的獻禮紀錄片。作為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系統拍攝故宮文物修復故事的大型紀錄片,其內容主要通過介紹各類的故宮修復專家,來展現中華藝術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還有師徒相傳承的“工匠精神”。《我在故宮修文物》在網絡的意外走紅成了很多學者和專家爭相研究的熱點,整部紀錄片共三集,卻耗時4個多月完成,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其實,以故宮為題材的紀錄片有很多,如《故宮》《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故宮100》等,這些作品在制作團隊、后期特效以及文本、構圖、解說詞等各個方面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制作成本上也要遠遠高于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但其在話題熱度和影響力上都遠不及后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播放平臺和傳播渠道的不同,導致了傳播力度和用戶討論度上的差異。
《如果國寶會說話》是一部百集紀錄片,從第一季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之后便獲得了很好的受眾反饋,因而有望成為繼《我在故宮修文物》和《國家寶藏》之后的又一個“紀錄片IP”。在新媒體時代,媒體內容的傳播呈現多元化、碎片化發展趨勢,《如果國寶會說話》這部紀錄片為了更好地適應了媒體融合以及傳播的表達和受眾的審美需求,因而采用了迥異于傳統紀錄片的方式,在時長設計、內容表現、手法解讀、影像構成等方面都做了很大調整和改變。節目中不再采用渲染獵奇和神秘的曲折表述方式,更沒有高冷的學術敘事,整體語言通俗易懂,貼近觀眾,從而給廣大觀眾帶來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
三、新媒體時代紀錄片呈現的新特征
1.受眾群體不斷擴大
根據2017年8月4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占全球網民總數的1/5。互聯網普及率為54.3%,并且媒介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
紀錄片是一種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并對其進行藝術加工與展現,以展現真實為本質,并用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電影或電視藝術。
作為一種獨特的電影藝術形式,紀錄片的發展要通過其傳播效果和受眾反饋來實現。而受眾是影響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受眾群體的不斷擴大也在客觀上催促著紀錄片形式與創作上的革新,因而就需要根據受眾的需求適時對紀錄片的創作方法等進行改進和創新。
2.創作隊伍不斷擴大
當前,紀錄片的創作主要是由電視臺、國家機構、民營公司制作和視頻網站自制,還有一小部分是由一些獨立的紀錄片制作人制作,此外還有一些網絡UGC作品。
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媒體平臺的大量涌現,讓建構參與式文化成為可能。新媒體以及自媒體平臺的崛起打破了信息傳、受雙方的界限,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話語權,也成為信息內容的生產者。這種參與主要為:第一,受眾成為創作紀錄片的主體,使得紀錄片由官方記錄轉變為全民記錄;第二,出現了紀錄片眾籌,即觀眾可以身體力行投入到紀錄片的拍攝中。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都要通過新媒體平臺實現全民參與式創作,從長遠來看,這種創作方式無疑更有利于紀錄片的長久發展,且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3.傳播方式的多元化
馬歇爾·麥克盧漢曾說過:“媒體的形式決定著媒體的內容”。在當下的媒介融合時代,媒介傳播過程和傳播形式也必然發生變革,因而紀錄片的傳播形式也在逐漸多樣化。
眾所周知,傳統媒體時代,紀錄片主要依托院線或電視媒體進行傳播,且囿于這種形式。但新媒體時代的紀錄片呈現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傳播形式,新媒體提供了更廣闊的傳播渠道,其中“微紀錄片”的出現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的,因其更加符合受眾對于碎片化信息的接受需求。此外,一些諸如愛奇藝、搜狐、優酷、嗶哩嗶哩、中國紀錄片網等視頻獨播網站也為紀錄片的發展設置了專門板塊,因而迅速擴大了受眾群體。隨著傳播方式的多元化,紀錄片的內容和形式也更加符合網絡傳播特性,題材也更加廣泛且切合實際。
四、新媒體時代我國紀錄片發展新模式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媒體融合的推進,我國紀錄片產業在經歷了慘淡經營之后迎來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紀錄片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多改變,如內容上更注重以人為本,打造全新的IP紀錄片,技術上更加注重合作互通,加強互聯網平臺的構建,在營銷上也一改傳統模式,形成產業鏈思維。融媒體時代下的中國紀錄片正在逐漸發展壯大起來。
1.“沙漏”模式的構建
盡管當前紀錄片的發展處于上行發展階段,近幾年也有很多口碑、收視很高且制作精良的優秀作品出現,但在影視產業內部,紀錄片依然是種受眾面狹窄的藝術形式,我國紀錄片的發展一直未能引起大眾長久的重視,且激發起興趣,究其原因:一是紀錄片內容同質化現象嚴重,如一些歷史類欄目以數量取勝,卻忽視了質量,在內容、視角等方面幾乎大同小異,長此以往影響著紀錄片朝多元化方向發展;二是互聯網具有海量傳播的特性,這一特性導致不同網站之間紀錄片內容的相似性極高,缺乏精品,無法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紀錄片資源的重復化現象極大地削弱了其他類型紀錄片的發展空間,嚴重阻礙了傳播渠道,即便一些高成本、大制作的大型紀錄片,因主題和內容專業性過強也未能在影視市場立足,而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局面。
這種形勢急需一種關于紀錄片未來發展理念的新模式的構建,于是,一些業內專家開始積極倡導并將“沙漏”模式轉型的理念提上了議程。何謂“沙漏”模式?即紀錄片的未來發展模式要像“沙漏”一樣呈現出“大小兩端”的發展形態。“大”主要指的是大投入、大傳播、大體量,《河西走廊》就是典型的大式品牌傳播,引進了國內外的頂級制作團隊,以展現中國歷史、地理以及人文藝術的宏偉廣闊,展現山河秀麗,還有中華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為主旨,傳播效果極佳,獲得了很高的社會贊譽。這種“高端”紀錄片的共同特點就是以“中國夢”作為社會背景和創作主題,緊跟時代步伐,緊扣社會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將平民百姓的個體夢想與宏大的中國夢融合起來,向社會傳遞出了逐夢的正能量從而激發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加之國家廣電總局政策的支持和導向,誕生了諸如《追夢中國人》《百年潮中國》等一系列主旋律題材的優質紀錄片,且反響良好。
和“高端”紀錄片的高投入、大體量相比,“小”則更傾向于低投入、低成本、接地氣兒的微紀錄片。尤其在當下新媒體環境下,微紀錄片憑借其傳播迅速、性價比高、制作相對簡單且投入低等優勢已經逐漸成為了時代的寵兒和受眾的審美選擇。我國第一部微紀錄片是以詩歌為題材的《我的詩篇》,因其具備微時長、微周期、微投資等特征,實現了全民參與和全網制、播,更是有效降低了成本。同時,這部微紀錄片憑借其內容簡潔卻內涵深刻而獲得了多項紀錄片大獎。因此,“高端”與“低端”紀錄片呈互補共生的發展態勢,相得益彰,這種“沙漏”模式才是未來我國紀錄片需要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標。
此外,IP紀錄片的打造也是我國未來紀錄片行業的發展方向。IP一詞運用到影視行業領域主要指由明星參演且具有很高收視率和點擊率,同時保證流量的影視劇,但在紀錄片領域,IP則主要是指一些制作精良、發行收入可觀且極具典范性和代表性的優質紀錄片。最典型的就是在江蘇衛視首播即獲高收視率的《本草中國》,緊接著又出現了收視和口碑極佳的商業化美食類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以及文化類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如果國寶會說話》等,這類紀錄片均可稱為“IP紀錄片”的典范之作。在“互聯網+”時代,結合大數據資源,并以“沙漏”模式和原創內容為支點和特色,同時與中國本土文化內涵相融合,創作出故事性強、彰顯時代特色和文化底蘊的系列紀錄片,從而不斷打造紀錄片IP這一品牌,也是未來我國紀錄片在內容創新上的突破。
2.建設互聯網平臺實現融合傳播發展戰略
“融合傳播”是指原本不同形態的媒介傳播通道的融合與互通。傳媒經濟是一種注意力經濟,在當前形勢下,解決紀錄片發行以及經濟和社會效益問題的重要途徑就是爭奪更優質的傳播渠道,通過“融合傳播”能夠實現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的互利雙贏。
我國紀錄片市場正在積極實施渠道融合的重要舉措,主要表現在:一是電視平臺上的融合互通。自2014年廣電總局實施的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的調整政策以來,所有上星綜合頻道媒體都要求播出時長為30分鐘的國產紀錄片,這就大大增加了國產紀錄片的播放量,從而進一步拉動國產紀錄片的產量,同時也提高了價格,獲得了更好的效益。二是電視端與視頻網站的融合互通。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電影和電視紀錄片對視頻網站的輸出,這是傳統電視臺紀錄片和中、小成本紀錄片生存下去的重要方式,如2016年在央視首播的文化類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起初通過傳統媒體的播出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度,但隨后通過社交視頻網站等新媒體形式播出后大受網友歡迎和熱捧。如今,從電影或電視大屏轉向手機小屏的趨勢催促著紀錄片行業要更加注意到媒介融合趨勢的到來,盡快實現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以及旗艦頻道和地方電視臺的互動融合。
五、結論
媒介技術的革新與應用深刻影響并改變著我國影視行業的發展,國產紀錄片歷經時代變遷如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雖有很多不足,但整體來看,無論在政策、平臺和作品上,還是在創作理念的更新、產業化的加強等方面,我國紀錄片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紀錄片作為傳達社會價值觀的影視藝術形式,在對國家形象和中國文化的內、外宣傳方面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它是一個國家形象和文化底蘊的重要傳播渠道,這就要求紀錄片制作人要用世界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將國產紀錄片發揚光大,走出國門。同時,對我國紀錄片作品還要繼續嚴格把關,不僅要做精做細,更要積極拓展紀錄片發展市場,把握新媒體時代下紀錄片的傳播特性和變革,找準發展需求點,力爭開拓出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