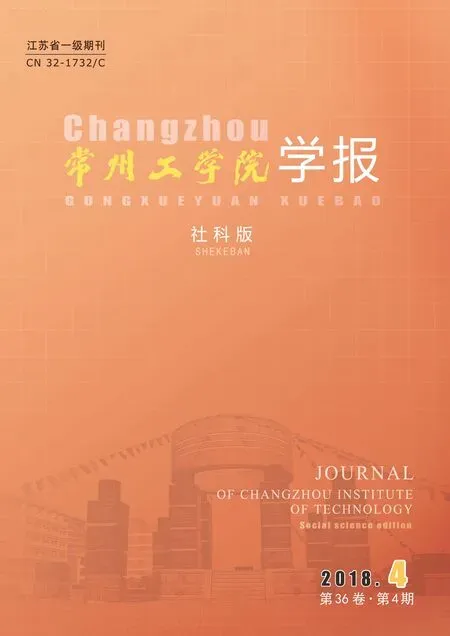論中國民間故事的審美層次
周彬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蕪湖241002)
故事是人類對歷史的記憶,記敘和傳播著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講故事是人類最古老且最基本的話語方式,是人類生活中一項不可少的文化活動,不講故事則不成其為人。”[1]民間故事作為民俗的一部分,在引導社會性格的形成,構建社會文化形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民間故事種類豐富,類型多樣(本文所涉及的民間故事是廣義上的民間故事,包括神話和傳說在內)。德國學者艾伯華說:“除了中國以外,大概不會有任何一個地方能使我們看到在一個時間跨度大而又順利發展的民族文化中有如此完整的民間故事。”[2]中國民間故事真實體現了中國最底層民眾的痛苦與快樂、愿望和祈盼,反映了中國民眾豁達、幽默、敢于反抗的精神追求。它也是民眾從另一個角度對社會的審視,體現了廣大民眾對生活的敏銳感知,對美的別樣追尋。“民俗藝術審美它的審美觀照可以分為不同層次,這是一個從生理、心理到意義、精神的動態把握過程。”[3]說故事作為民俗藝術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故而民間故事的審美也有不同層次,也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淺層到深層的過程。
一、形式觀感——民間故事審美的表層基礎
民間故事審美的第一個層次是形式觀感。它是民間故事審美的初級層次,是由民俗藝術的感性形式所引發的審美活動,依賴于人的感官。按照心理學的分析,“感覺是對事物個別特性的反映,如對事物的色彩、線條、聲音、質地的感官印象,是通過感官與對象的直接接觸而獲得的”[4]。民間故事屬于口承語言民俗,作為一種口述文學形式,民間故事由故事文本、作者(講述者)、讀者(聽眾)以及講述語境等諸多要素構成。美國學者理查德·鮑曼將口述文學視為一種情境中的表演形式,倡導在講述表演中對口述文本進行全面把握和欣賞。一個民間故事得以傳承,發揮它本身具有的教化作用,讓不同層次的受眾得到相應的審美感受,除了故事本身所蘊含的價值,講故事人的演繹就顯得至關重要。所以,“故事講述者大多是當地德高望重者,他們是一群了解本地掌故傳說的人。他們見多識廣,有著比其他人更為深刻的生活閱歷和生活經驗。經由他們之口,那些聽故事的人慢慢了解現在的生活是對過去的延續,從而對當下的生活牢牢把握”[5]。故事講述人在講述故事的時候通常不以特定的時間、地點、人物、時間作為講述對象,其中的時間大多被敘述為“從前”“很久很久以前”等,這些詞或者句子能夠瞬間把人拉進故事的情境之中,距離我們很遠的時間所發生的事既古老又帶有神秘感,這樣的開場講述形式讓受眾有一種穿越時空之感,未知的世界神秘而且奇特,容易讓受眾更為專注地聽下去。地點包括“有個地方”“有個村子”“大山腳下”“某某河邊或者海邊”之類的不確定地點。人物大多都有虛構的名字,這種安排形式更貼近生活,與生活緊密相關,人物性格關系也一目了然。作為口承語言民俗,它給人以最直觀的感受,是一個直觀的視聽過程,講故事的人也是表演者,怎么讓表演深入人心呢?蘇聯的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要學習、觀察、傾聽、熱愛生活。”每一個講民間故事的人不可能學習過系統的表演理論,他們的故事是從祖輩那兒來的,是從生活中來的。曾經的他們也是聽故事的人,所以優秀的傳承者在每次講故事前都會預先深入研究人物形象及其生活邏輯,依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為故事增添新的情節和內容,因此同一個故事在不同區域流傳,其內容和情節會有些許變化,這也是民間故事在不同區域得以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抑揚頓挫的口頭語言配合著肢體語言以及臉部表情,在故事中還有熟悉的俗諺,這些俗諺既幽默又生動。在講述故事過程中有的還穿插一些當地的民謠或者歌謠,使講故事變成了說唱故事。例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人講故事,凌純聲稱其“像漢人的北方大鼓,南方蘇灘,他們的說法和漢人說大鼓書一樣,說了一段,唱了一段,而后再說”[6]。這樣的形式,視聽結合,讓聽故事的人聽得津津有味。這樣的形式讓民眾方便交流與講述,作品也容易被民眾所理解。
馬林諾夫斯基提出:“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來的是一種缺乏環境的非生活的東西……我們還必須記住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娛樂傳奇的社會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相當明顯的,故事是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并非紙上。”[7]故事的講述是一種表演形式,對于不同類型的故事,講述過程也是不同的。例如在講述魔寶類型的故事時:“故事中的角色(特別是主角)和故事的聽眾,往往在魔寶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就被告知了魔寶的功用,而故事中的角色也都在得知魔寶功用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去使用魔寶,以得到預期的效果。”[8]湖北的民間故事《水桃》[9]講述的內容是:一位公子打水打上來一個水桃,水桃其實是龍王三太子變的,在公子答應將他放生后,水桃送給他兩樣寶物——扇子和帽子,并告訴它們的使用方法和功用,最后公子利用這兩樣寶物收獲了美滿的愛情,獲得了仕途的成功。還有流傳很廣的《獵人海力布》[10],海力布在得到能聽懂動物語言的寶石時,龍王就對該寶物的使用和禁忌作了說明。這種形式既能讓受眾清楚魔寶的功用,也為后續故事情節的發展埋下了伏筆。但是在識寶類的故事中,一般先不介紹寶物的功用,而是以賣關子、慢慢揭謎底的形式來講述,這種形式不僅在識寶類的故事中經常使用,在其他故事中也屢見不鮮。在求好運的故事中,主角一般都有著誠信并且助人為樂的品質,面對故事中出現的難題,他總是先幫別人解決問題,但是輪到自己時由于規矩的制約就沒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正當聽故事的人為主角著急的時候,殊不知,他在幫別人解決問題的同時也解決了自己的難題,最終取得一個圓滿的結局。這類的故事有很多,如四川民間故事《范丹問佛》[11]294-296、青海民間故事《西天問如來佛》[12]、新疆民間故事《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13]等等。
明末清初文學家、批評家毛宗崗在評《三國演義》時曾說:“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這句話不僅道出了《三國演義》故事情節起伏的特點,同時也指出了受眾對于文學的審美趣味。這對民間文學也同樣適用的。我國著名劇作家胡可將毛宗崗的觀點更加具體化:“觀眾喜歡的是百歲掛帥而不是百歲養老。是十二寡婦征西而不是十二寡婦上墳,是武松打虎而不是武松打狗,是木蘭從軍而不是木蘭出嫁。”所以,越是不可思議和困難的事越能夠引發人們內心的興趣,勾起他們的好奇心,也越容易得到人們的喜愛。
二、心象體驗——民間故事由表及里審美的遞進
心象體驗是民間故事審美的第二個層次,是民俗藝術審美由表及里的開始。心象體驗超越了感性的形式因素,進入到形象之中,用心象體悟的方式感受民間故事內在的美。心象體驗是對作品有一定的理解,將自身的情感注入作品之中,進入作品的內部,從作品的內部來洞察作品,審視作品的藝術美。故事的講述者不僅對故事本身有自己的理解,而且有些生活體驗是他們所經歷過的,他們說的不僅是流傳下來的故事,還有自己與之類似的生活經歷。例如在解難題的故事中,生活中的一些難題主人公可以不借助外力,而依靠自己的智慧解決。如在四川民間故事《巧姑》[11]849中,老漢為了試探屠戶的女兒巧姑的才智,設下難題:買點皮粘皮、皮打皮、沒筋骨的瘦肉,沒有皮的肥肉。巧姑從容不迫地給老漢拿了豬耳朵、豬尾巴、豬肝和板油四樣東西,解決了難題。在這類巧女解難題的故事中,故事主人公大多利用自己對生活中許多事物的深度認識從而解決難題。從生活的角度去講述故事,讓受眾有真實感。
受眾的心象體驗大多因自身的境遇而產生共鳴,無論是民間故事的講述者還是民間故事的受眾都是廣大的普通老百姓,民間故事來源于民眾的生活,故事在祖祖輩輩中口耳相傳,表達的都是他們日常生產勞動和婚姻家庭中的瑣事,所以受眾在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很容易將自己的經歷和遭遇代入故事中,從而產生共鳴。故事中窮困主人公的境況正是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的真實寫照。故事中主人公因為得到幫助而發家致富,過上美滿生活,這正是社會底層民眾所向往的生活。我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時代,并且我國又是以農耕為主的農業大國,在中國民間故事中保留了大量關于農業社會生活的描述。例如:“有一個大戶人家,良田千頃,騾馬成群”[14]72,“從前有個老太太,丈夫早早死了,老太太整天在田里走來走去,吃了不少苦,養活三個兒子”[14]107,“在長白山里,有一個小堡子,堡里的人世世代代以農耕為主,過得是十分艱苦”[15],類似這樣的描述中都有關于農耕方面的描寫。中國經歷了漫長的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始終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民間故事也根植于農耕社會。受眾在聽到這些與他們相似的工作環境的描述時,自然會聯想到自身勞作的辛苦,會讓絕大部分聽眾產生共鳴。
這些故事在貧苦大眾中流傳比較廣,在我國每個地區都有,為什么有如此龐大的故事量?因為從古至今,貧困的勞苦大眾一直是社會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是他們共同的向往,當他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獨自一人時,許多故事會讓他們產生一種精神遐想。在精神上擺脫貧困,過上安定富足的生活,這是他們的一種精神慰藉,是他們在心象體驗中產生的“白日夢”。
三、意義追索——民間故事審美的意義所在
意義追索是民間故事審美的第三個層次,它的主旨在于實現民間故事所內含意義的還原和認知。意義追索是在前兩個審美層次基礎上探尋相關民間故事的起源。民間故事背后的意義不一,并且是以一個個類型出現的。上文提到,中國民間故事有許多描述與農耕有關,其背后的意義追索讓我們想到在農業生產中,民眾除了要付出辛勤的勞作,還必須要依靠自然界的風調雨順才能取得好收成,所以中國民間故事中關于自然界風雨雷電、山川河流的故事屢見不鮮。這正是民眾對他們生存環境的樸素認識和原始想象。有些故事有的是為了紀念祖先,有的是為了驅邪避兇,有的則是為了祈福平安。“民間故事是一代又一代勞動人民在漫長的社會生活中集體創造出來的口頭文學,它以歲月為筆,生活為墨,用時間蘸著空間一代代書寫下來。毫無疑問,民間故事是勞動人民哲學、美學、倫理、心理、宗教、社會歷史等各種思維情感的復合體。”[16]所以要想知道民間故事背后的意義,需要把它放到社會這個大系統中去進行多方面的綜合考察。例如民間故事中總是贊美和體現“善”這一理念,為什么會如此?因為在民間故事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體現了勞動人民的審美理想以及審美追求。審美本身就包含著道德,而道德評價又是審美評價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解難題類的民間故事,無論是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來贊美善,還是通過善與惡相互斗爭來贊美善,尋找幸福的人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均得到了應有的善報。在中國,“善惡相報”這一觀點雖然來自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但是它又與中國傳統的天命論相融通,和儒家的倫理相協調。因而“善”具有中國特色,它在中國的社會中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中國近現代流行的一種故事類型,劉守華先生將其歸納為“求好運”的故事類型。它們的突出特征是表現主人公積極進取,奮力與命運抗爭的精神。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苦人民,但是他們卻有著野草一般堅韌的個性,不向命運低頭[17]。在貧苦的環境下,他們依然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舊社會的底層民眾生活困苦,但他們又不安于現狀,與不幸的命運作抗爭。從一系列問佛求好運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代人問事有好報”這樣一個主旨。不論是在“求好運”這一故事類型中,還是在其他類型的故事里面,好人有好報也一直是民間故事所宣揚的主旨,這與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勤勞勇敢、熱心助人”有關。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倡導樂于助人,俗諺也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其淵源來自古代墨家的“兼愛”學說。任繼愈著的《中國哲學史》引述了《墨子》中關于“兼愛”的三句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18]民間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其生成的環境是真實的,這真實存在的環境不僅反映出民間信仰和道德意識,而且可窺見當時的社會背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崇尚誠信的民族。《說文》中說:“誠,信也;信,誠也。”[19]無論是誠也好,信也好,講究的都是真實無妄、信守承諾、言行一致。隋唐前后的思想家把“誠信”作為一個統一的道德規范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人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本,故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以欺詐為本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殞,善名不減;小人雖貴,惡名不除。所以,誠信觀念深深扎根于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成為指引人們行動的無形驅動力。在民間故事中,凡是守誠信的主人公,結局大都是美好的,不守誠信的,結局非死即傷。例如遼寧民間故事《謊張三》[20]中一向貪婪狡詐的地主本打算用難題來占有長工的勞動,但是自己精心設計的難題被長工巧妙破解之后,他只好按照事先說好的條件,把酬勞付給了長工。而在山西民間故事《“奇怪”崩大堂》[21]中,窮苦小伙子成哥在仙妻的幫助下一次次破解了縣官出的難題,但是縣官為了一己私欲,次次食言,而且一次次地變本加厲,違背了大眾所奉行的“誠信”原則,所以在民間故事所虛構的情境中,將違規者置于死地作為懲罰。
中國民間故事是從真實環境中產生發展的,例如我國流傳很廣的“孟姜女哭倒長城”“梁山伯與祝英臺”等故事的生成環境都真實可考。孟姜女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殘酷的徭役制度給普通民眾帶來的痛苦生活以及悲慘命運。民間故事可以說是一種虛構的真實,但是卻能從一種特殊的敘事角度去揭露真實。所以對于民間故事的意義追索其內容是豐富的,包含歷史、人文、思想等方面的內容。通過意義追索,我們可以發現民間故事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了一定的教育功能,這也是許多故事得以廣泛流傳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在中國各地區流傳很廣的機智人物故事,這類故事風格獨特,并且機智人物形象也豐富多彩。羅永麟專門就機智人物故事的功能顯現作了概括:“機智人物故事的社會意義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歷史的意義主要表現了豐富的民間文化內涵和階級社會人民群眾與敵對階級長期斗爭的歷史。現實的意義,就在于表現了機智人物的懲惡揚善,正氣凜然;扶弱濟貧,發揚人道;排難解紛,助人為樂;破除迷信,移風易俗。”[22]因此這些故事雖然是歷史的遺跡,但是有些現象至今仍常出現于現實生活中,發人深省,對于改變社會風氣,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
四、結語
存活于中華各民族民眾口頭心間的民間故事,總是能不約而同地配合時代的環境結合自身的境況,通過樸實單純的敘說,展示出富有象征性的文化意蘊以及層次分明的審美觀照,不僅具有娛樂教化的作用,還具有不同層次的審美功能,達到生活與哲理的巧妙融合,對后世有一種難以替代的教化作用。中國民間故事的審美層次是從民俗藝術審美的角度來剖析的,通過剖析,讓我們對民間故事的美有了具體的理解,無論是從審美的內容上,還是從審美層次上,都讓受眾對民間故事的美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細化的過程中能更好地把握民俗藝術審美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