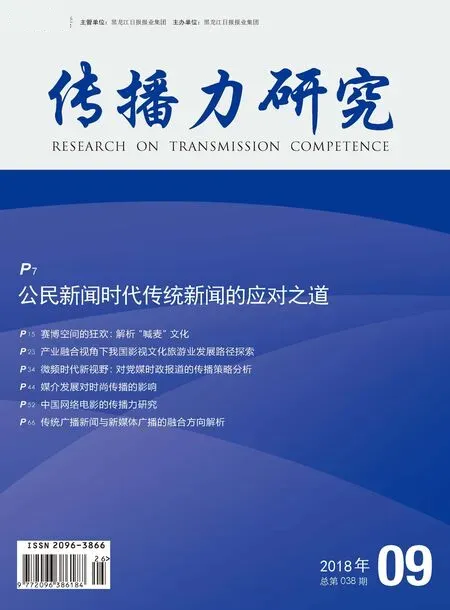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廣州珠村乞巧民俗文化三元結構解讀
唐滌非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
珠村是廣州市的城中村,是一個有著八百多年歷史的古村落。這里的文化底蘊深厚,尤其是近些年來。乞巧民俗文化活動開展得十分火熱,被文化部連續授予“中國乞巧文化藝術之鄉”,“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的稱號,成了“廣東省歷史文化名村”,馳譽海內外。
乞巧,是一種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動,萌芽于春秋戰國時期,到西漢,才在民間普遍形成,延續到各朝各代,遠播海外漢文化所及的國家和地區。直到上世紀,雖然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兩次洗劫,幾乎毀滅。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從上世紀末開始,又再度勃發生機。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古樸的民俗文化活動,能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如此幅員遼闊的國度里,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能如此和諧地融入現代社會生活,玄機何在?秘笈何存?或許,瑞典學者Andrejanson能給我們一定的有益啟示。他在《媒介空間一致性》中提出了社會空間三元結構的理論。他認為,空間生產的復雜性取決于三個維度:一是感知空間,二是構思空間,三是生存空間。三者相互依存,緊密融合,由此而推動空間生產的持續穩定的發展。既在繼承中發展,又在發展中繼承。
一、感知空間——美質呈現
感知空間,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們可以認知,可以辨識,可以感悟,可以審美。那么,作為被我們感知的乞巧文化活動究竟會呈現怎樣一種景象呢?著名作家歐陽山在《三家巷》中有一段真實的情景再現:
到了天黑掌燈的時候,八仙桌上的禾苗盤子也點上了小油燈,掩映通明,區桃把她細巧供物一件一件擺出來。有丁方不到一寸的釘金繡花裙褂,有一粒谷子般大小的各種繡花軟緞高低鞋、平底鞋、拖鞋、涼鞋和五顏六色的襪子,有玲瓏輕飄的羅帳、被單、窗簾、桌圍,有指甲般大小的各種扇子、手帕,還有樣式齊全的梳妝用具,胭脂水粉……還有四盆花,都只有酒杯大小,一盆蓮花,一盆茉莉,一盤玫瑰,一盆夜合,每盆有花兩朵,一盆真的,一盤假的。可是任憑大家盡看盡猜,也分不出哪朵是真的,哪朵是假的。(《歐陽山文集》第五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
從擺出來的巧物來看,這里擺的是“小七娘”。“擺七娘”有“小七娘”與“大七娘”之分。“小七娘”是在自家或幾家置辦的貢案上擺出。“大七娘”,規模大,規格高,是以族群的方式擺在大祠堂或公共場所,擺出的貢物,品種、樣式更加豐富,更加精美,所有物件都要按一定次序擺在一個五米見方的八仙桌上。除了各種精巧的貢物,還必須有村牌坊,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鵲橋,還要插上六面刺繡的戰旗。
除了擺貢案,還要搭戲臺,唱“七娘大戲”。“六國大封相”,“楊門女將”,“花木蘭”,“劉備過江招親”,都是必演的劇目。
不管是“小七娘”還是“大七娘”,都是濃縮的美質呈現。
意美。“擺七娘”、“拜七姐”,所擺出的各種貢物,如牛郎織女、禾盆、五谷塔、羅帳、花裙、果樹、花園,等等,無一不透出女性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自身才智的提升,美滿婚姻的實現,家庭生活的幸福,五谷豐登的喜悅,青山綠水的愜意,等等,值得關注的是,在琳瑯滿目的貢案上,毫無例外地要插上六面戰旗,都會有穆桂英、花木蘭的形象出現,這是為什么?六面戰旗所代表的是“齊、楚、韓、燕、趙、魏”六國,所表達的是六國聯合抗擊秦國入侵。之所以要重提這段歷史,就因為一千多年后,八百多年前,南宋同樣遭受金兵入侵,珠村一帶的先祖,才從中原遷徙至此的。這兩段歷史,一明一暗,融入女性乞巧活動中,從而向世人宣示,“巾幗照樣不讓須眉”的抗擊入侵的愛國情懷與英雄氣概。何其壯美!
形美。貢案上的每件貢物,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是制作者們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制作出來的精品。或以精求美,精細則美。譬如芝麻梅花香,長80厘米,直徑3厘米,通體布滿朵朵梅花。這是巧女們用巧手將芝麻尖對尖,頭對頭,四粒構成一朵梅花,一粒一粒貼上去的。或以假亂真,美真等同。譬如花朵,兩朵并插,一真一假,讓人真假莫辨。還有荔枝,楊桃等,逼真的程度,無不令人稱奇。或縮大見微,小中見大。譬如七巧鞋,一雙繡花鞋,不足一寸;七娘衣,用各色彩紙做成,大小如同三四歲孩子穿的衣服,甚至更小。不管造型多美,制作多精,都必須凸顯牛郎織女鵲橋會主線;都必須從原汁原味的生活與生產中取材。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價值取向,才能符合大眾的審美愉悅。
創新,新穎才美。流傳了2000多年的乞巧文化,極易沉淀成固態的審美形態。如造型、工藝、材質,等等。譬如廣繡,是我國四大名繡之一。因為種種原因,日漸式微。這些年來,融入乞巧活動,創作出像《百鳥朝鳳》、《報曉》、《愛的祈愿樹》等一批又一批優秀作品,不僅使古老的工藝重獲新生,又為乞巧民俗文化活動增添異彩。再譬如“擺七娘”,自古以來都有固定的場所,近年來卻增加“七夕巡游”,貢案設在花車上,穿行在大街小巷,由原來靜態展示變成了動態觀光表演。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才是當今傳統文化活動的大勢所趨,才有如此五彩繽紛美質呈現。
二、構思空間——乞巧導向把握
構思,人們一般理解為文學藝術創作中的選材立意,布局謀篇。其實任何一種社會活動,要達到預期效果,都要構思,其中包括設計、策劃、組織、引導、調控,等等。即如乞巧民俗文化活動,一般都帶有一定的約定性,自發性,地域性,還摻雜了求神拜佛的迷信活動。要使這類活動上規模,上檔次,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除了精心策劃,精心組織之外,關鍵在于旗幟鮮明地把握導向。
政策導向。幾乎沉寂了半個世紀的乞巧民俗文化活動,從半公開到公開,從小到大,從自發到有組織開展,規模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巧物越來越精美。十來年,其規模,其檔次,都是任何朝代所無法比擬的。究其原因,就在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放寬政策的同時,特別注重了導向把握,國家主席習近平著重指出:“對于傳統文化中適合調理社會關系和鼓勵人們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展,賦予其新的涵義。”(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4年9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宣部、民政部等五部委也聯合出臺了《關于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正是因為有習近平主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做指引,有政策做支撐,珠村一代的乞巧活動才有領導、有組織、有序地開展起來。往日“乞巧”節只是“拜七姐”、“擺七娘”,“拜”與“擺”并重,而現在的“乞巧”節卻是通過比賽、評獎、表演、巡展等方式,突出“擺”而淡化“拜”,使活動更加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立健全民間文化機構,如民間文化藝術協會,文化工作站等,加強對乞巧活動的領導與掌控。舉辦乞巧手工培訓班,創建“乞巧工作室”,提升乞巧活動的品味。還逐年投入一定的資金,修建和維護乞巧活動的場地和設備,拓展活動空間。
輿論導向。報紙、電臺、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的及時介入及時報道,對推廣和宣傳乞巧活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廣州乞巧文化節”官方微信、“廣州乞巧文化節”官方網站、新浪微博、一點資訊、網易自媒體、企鵝媒體平臺、今日頭條等新媒體傳播,讓乞巧民俗文化滲透到公眾生活和工作的角落,極大增強了乞巧民俗文化活動的覆蓋面與影響力。新媒體運用的青少年喜聞樂見的網絡語言、表達方式傳播乞巧文化;對涉及廣州乞巧節的網上熱點的快速反應,理性發聲,解疑釋惑,等等,都很好地引導了輿論。尤其是一些深度報道,對活動中出現的某些問題或者某種傾向,也常常會引發社會輿論。這些,都起到了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
理論導向。隨著乞巧活動的開展,同樣激發了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他們從歷史,從地域、從民俗、從工藝、從社會、從經濟、從文化、從傳播,等等,展開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全方位的研究,涌現了大批的學術論文和著作。如《從田野到講壇——廣州民間文藝理論探索》、《城中村的民俗記憶——廣州珠村調查》、《纖云弄巧擺七夕》、《廣州“城中村”研究》、《村落的終結——羊城村故事》,為廣州市的小學編寫鄉土教材《我們的乞巧》,如此等等。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不僅為廣州珠村一帶的乞巧民俗文化尋到了文化根脈,更為重要的是為這種民俗文化夯實了厚重的理論基石。既增強了地位認同,又提升了文化自信,為乞巧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理論導向。
三、生存空間——乞巧價值定位
生存是第一需要,需要決定價值。波蘭人類學家馬琳諾夫認為,文化源自人類的需要。(轉引自(《從田野到講壇:廣州民間文藝理論探索》,曾應楓,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1,p161。)乞巧文化是一種傳統的女性文化,首先必須適應女性的需要,并由此而衍生出社會多方面的需要。
首先是確認女性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需要。自從我國從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進入男性社會以來,便漸次演化成“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夫為妻綱”,“嫁夫隨夫”的傳統倫理觀念,以至“女子無才便是德”竟然也成了評價女性的標識。如何確認女性的社會地位與身份,確保女性權益,便成了古今中外共同的社會話題。乞巧活動,或許是充分表達女性訴求,展示女性才智最便捷的方式。其中“拜七姐”,乞求織女星神賜智巧,賜姻緣,只不過是借助神力,增強人們認同的可信度。“擺七娘”,擺出婦女們巧手制作的精美巧物,以此展示她們的智慧與才華,獲得社會的認可,這才是她們真實的話語表達。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城市的發展,珠村一帶的農村婦女,成了城中村的居民,他們雖然離開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卻獲得了土地補償,再加上自主創業,生活富足了。因此,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時,中老年婦女重新找回傳統的地域記憶,自發組合起來“擺七娘”,自娛自樂,聯絡友情,這同樣是一種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時至今日,女性就業仍然存在性別歧視,“剩女”現象,也在困擾著部分年青女性,因而,乞巧活動便成了她們秀才華,秀顏值,溝通情誼的難得機遇。如今廣州珠村一帶的乞巧民俗活動,雖然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其實卻是以傳統的方式演繹當代女性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乞巧文化,也是創建新型文化業態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養新型文化業態。”實踐證明,這些年來隨著乞巧民俗文化活動的蓬勃開展,這種新型文化業態在廣州珠村一帶,已初具規模,初見成效。乞巧活動中的“拜七姐”、“擺七娘”,雖然是傳統的方式,但其內涵卻是彰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和核心價值觀,成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各類貢品巧物的制作,在手工制作基礎上,引進了現代技術,其作品更加精美,更符合現代審美情趣。乞巧活動,原本是女性的民俗活動,現在卻是大眾共同參予,既有領導干部,又有平民百姓,還有專家學者,農民工等。除了本地居民,還有外地游客,甚至還有不少外國朋友專程趕來,目睹乞巧盛況,如此等等,既調和了社會關系,又促進了社會和諧。過去只供展示或收藏的乞巧作品,已開始與市場營銷接軌,譬如廣繡、珠繡,這些年來都遠銷至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中東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旅游業也同樣獲得了商機,珠村還特地為游客開設了旅游專線。既繁榮了市場,又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正是因為上述各端,才在廣州珠村一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新型的文化業態。
綜上所述,古老的乞巧民俗文化活動,時至今日,仍然還能在廣州珠村一代如此生機勃勃,盛況空前,自身的美質是根本,正確的導向是關鍵,社會需要是源泉。三者融合,乞巧文化才能在繼承中得到發展,在發展中獲得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