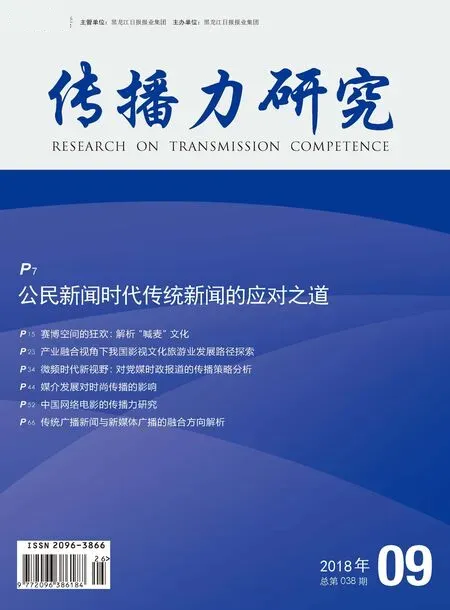新語境下文化類綜藝節目蘊藏的美學價值分析
王欣穎 哈爾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2016年年底,黑龍江衛視推出文化綜藝節目《見字如面》,基本上也可以算是我國文化類綜藝節目的一個派系代表,節目主要以一些著名人物的書信為載體,聘請著名明星在電視上予以朗讀。從其開始出現在銀幕上開始,就一直被冠以“文化”“純美”等各種各樣的標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它都占據著我國電視節目排行榜中的前幾名。《見字如面》將傳統的文化節目表現形式打破,用全新的面貌迎接觀眾,在表達文化的同時具有自己獨特的美學風格,它的出現給文化類綜藝節目開闊了一片新天地,同樣《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等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1],本文將以《見字如面》為代表重點剖析其在新語境下的美學價值。
一、美學價值分析
(一)“集體記憶”的歷史重現之美
“集體記憶”的過程是重構集體情感、集體心理的活動,不一定是史實本身。“集體性”是指社會歷史進步中所必須經歷的階段,并非每個人都經歷過,而是這段記憶是人們所共有的。重讀信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標尺就是真實性[2]。例如,除了一些老革命者,戰爭對于現在的國人來說是一個感覺離我們很遙遠的事情,這種歷史感悟是我們中鮮有的,正像節目中讀到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句話就體現出在那個時代書信作為通訊工具的重要性,這句話一讀出來,就能立即在觀眾的心里起到作用,使其產生了一種情感移植體驗,把觀眾迅速引進了戰火紛飛的年代以及共同的人類情感[3]。
書信對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記憶重構的載體。而電視媒介又是大眾傳播的載體,它具有豐富的視聽語言,并且在節目中對信件文本也進行了二度創作,這樣便成為了信件內容傳播和重構集體記憶的重要媒介。書信不僅能還原性展現歷史文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復現出一些動人的故事和情感,它們極大程度上再現了歷史,重構了觀眾的“集體記憶”。
(二)“共情渲染”的情感維度之美
情緒和認知的加工是共情中兩個加工過程,兩者的發展軌跡和機制有所不同。其中,情緒共情不是后天得到的,而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讀信的演員將自身在朗讀書信的過程中帶入角色中,知覺其情緒,與寫信人產生一種情感共鳴。并且在現場的觀眾作為接受個體受到演員讀信時語言傳達和情感的渲染[4],觀眾自身會不自覺的產生一種與寫信人類似的情緒喚醒活動,情緒共情包括兩個方面:對朗讀時演員所傳達信息的情緒共情和對寫信人寫信時所表達信息的情緒共情。例如蔣勤勤在《見字如面》第九期的朗讀,她所朗讀的是共產黨員趙云霄給她女兒啟明寫的信,信中有一句“流淚書成”,蔣勤勤感悟了寫信人寫信時的情緒,硬是在一邊流淚一邊朗讀。在這里蔣勤勤徹底融入到寫信人的角色中去了,融入到趙云霄這個悲劇人物中去,為了共產主義信仰,趙云霄最后選擇了慷慨就義,在訣別之際,她把這封飽含滿滿母愛的情感置于這封信中,毫無疑問,蔣勤勤在朗讀時也產生了與啟明母親一樣就義前的情緒共振,同樣這封信也喚醒了蔣勤勤心中偉大的母性。在節目現場,演員的演繹及情緒的傳達誘發了觀眾的情緒共情,也是紛紛留下了嘆息的淚水。每一期節目所傳達的情感各有不同,實現了自身情感和歷史人物情感的情緒共振,在不斷思考中讓人獲取感知認同。
(三)“間離效果”的結構敘事之美
“間離效果”最早是被這樣定義的:針對表達的事情,讓觀眾具有一個分析和評判該事件的立場。同樣的,在《見字如面》節目現場,根據節目節奏的變化,主持人、特邀專家和演員可以建立有效的間離,在演員的讀信環節中最能體現這一點,演員不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中,而是需要演員自我的再創造。說的更加直觀點就是在同期節目中出現兩次同一個朗讀演員,并且是朗讀不同的書信。從觀眾對演員的經驗認知和期望方面來說,在誦讀不同的信件中,同一個演員必須來回切換所需沉浸的場景和情感“幻覺”,以此形成從認識到批判的審美過程。
演員在第一現場進行朗讀,主持人在第二現場與專家對信件進行拆解、討論和點評等內容。這兩個現場的切換設置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時空間離,適時將一種陌生化效果帶給觀眾。制造陌生并非“陌生化”的最終目的[5],而是使用陌生化方法,給予觀眾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解,讓觀眾跟隨第一現場的讀信演員進入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投入情感和釋放情感。相反,第二現場的點評又把觀眾拉回到現實世界,將其審美經驗和審美情緒喚醒,能夠理性的思考和認知第一階段的審美活動。
二、結語
綜上所述,現如今的文化類綜藝節目還是存在著諸多的美學價值,文化綜藝節目的依托肯定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但在這類節目的發展過程中,仍然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傳播潛力如何發揮、如何創新傳播方式等,這些問題值得每一位電視從業者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