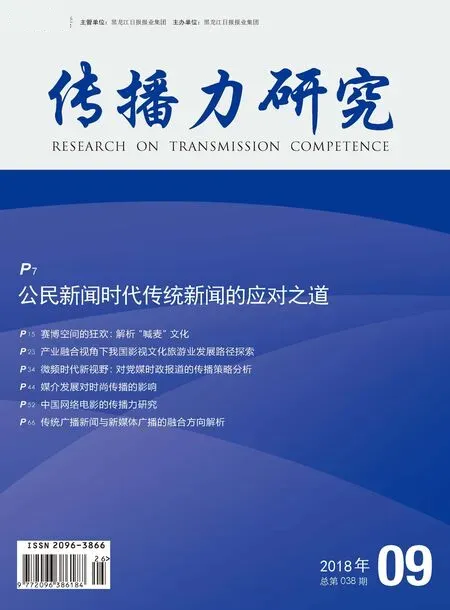由“后真相”的分歧談大眾情緒及媒體對策
郁芬 新華日報社
一、后真相,傳播痛點還是空穴來風(fēng)
后真相指什么?牛津英語詞典的官方解釋是,“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
英國媒體人馬休·達(dá)安科納認(rèn)為,所謂“后真相”,強(qiáng)調(diào)的并不是謊言、杜撰或欺騙,而是公眾對此的反應(yīng)——相較事實和證據(jù),公眾的情感共鳴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我國的《2017年傳媒倫理問題研究報告》一文指出,所謂“后真相”并不是一切都是假的,而是“橫看成嶺側(cè)成峰”,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產(chǎn)生了不同“事實”,當(dāng)真相被懸置,事實的重要性就被態(tài)度和情感所代替。
相關(guān)解釋有很多,盡管措辭不同,但是很多研究者的解釋并沒有逃脫牛津官方釋義的范疇。
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認(rèn)為根本不存在“后真相”現(xiàn)象,宣揚(yáng)“后真相”是十足的空穴來風(fēng)。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教授劉建明在《后真相論的執(zhí)迷與幻覺》一文中說,“在后真相時代,立場已赤裸裸地壓制了事實,人們被假新聞、立場和情感所蒙蔽,這些都是僵化的觀念”,是“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無視真相,歪曲和限制了民眾對事實的解讀”。以特朗普當(dāng)選美國總統(tǒng)、英國公投脫歐為例,劉建明認(rèn)為,特朗普當(dāng)選、英國脫歐,并不是謠言、情感戰(zhàn)勝事實和真相的結(jié)果,而是絕大多數(shù)網(wǎng)民和傳統(tǒng)媒體的受眾權(quán)衡利弊,從自身最真切的感受、最關(guān)切的利益出發(fā)投出的票,這就是最大的真實,最根本的事實,媒體說的話他們未必相信,媒體“代替”他們說出的話也未必是他們的本愿。劉建明斥情緒大于事實這一判斷反映了精英、媒體的愚蠢和高傲,不僅不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把錯誤推到大眾的“情緒”上。
二、失控的情緒危害社會公共利益
學(xué)者對后真相時代的擔(dān)憂不無道理。情緒大于事實,不安、憤怒、謾罵等情緒比新聞本身傳播得更快更廣,確實是當(dāng)下傳播生態(tài)的一個痛點。盡管一些專業(yè)媒體機(jī)構(gòu)也存在新聞業(yè)務(wù)不規(guī)范的操作現(xiàn)象,導(dǎo)致了嘩眾取寵、賣弄情緒等倫理失范的問題,但是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繁榮發(fā)展后,它們對情緒的渲染更加失控,在傳播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這也是近年來情緒大于事實這一議題引起重視的原因。
分析原因不難發(fā)現(xiàn),情緒戰(zhàn)勝事實有技術(shù)基礎(chǔ)。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為自媒體的營生提供了可能。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使得信息的發(fā)送方和接收方合二為一,專業(yè)媒體機(jī)構(gòu)新聞發(fā)布的壟斷地位一去不復(fù)返,信息傳播的門檻降低,很多公號成了情緒的操盤手。社交屬性與新聞傳播交織在一起,觀點與事實混淆,也讓信息的傳播更加復(fù)雜,成了病毒式的裂變傳播,情緒感染性更大、傳播更廣更快。
再者,情緒戰(zhàn)勝事實也是社會撕裂的一個表現(xiàn)。《后真相本質(zhì)上是后共識》一文說,“后真相”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更根本原因,是社會共識的瓦解,當(dāng)一個社會失去對基本價值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共識,觀念傳達(dá)與接受之間就會短路,其結(jié)果是,人們只能根據(jù)自己的立場有選擇地相信事實,或者拒絕真相,或者相信“另類事實”。而當(dāng)下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收入層次不一,立場不一,利益不一,社會各階層逐漸撕裂,熊孩子、壞老人,相親女、鳳凰男,被貧窮限制想象的底層、焦慮的中產(chǎn)階級,壞政府、好公民等一些被固定標(biāo)簽的、對立的社會角色輪番成為自媒體的寫作對象,現(xiàn)實中的社會撕裂成了爆款網(wǎng)文中的戲劇沖突,很容易觸到人們情緒的興奮點。
三、傲慢的媒體忽視了理性的情緒
以劉建明為代表的學(xué)者對后真相這一概念的駁斥也頗有啟迪意義。狂歡的大眾不一定是烏合之眾,他們的情緒包含理性。
如果把大眾情緒的爆發(fā)比作一次社會集體運(yùn)動,那么那些認(rèn)為進(jìn)入后真相時代的人與法國思想家勒龐、美國社會學(xué)家斯梅爾塞頗為相似,他們在對集體行為參與者的動機(jī)的理解上達(dá)到了一致,他們都認(rèn)為,第一運(yùn)動的參與者是非理性的,第二情感在運(yùn)動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
但后來的學(xué)者對勒龐和斯梅爾塞的觀點進(jìn)行了駁斥,他們強(qiáng)調(diào)運(yùn)動的參與者是理性的,說他們非理性僅僅是一些旁觀者站在自身立場上的偏頗看法,這些旁觀者因為對集體行為不認(rèn)同,就認(rèn)定參與者是非理性的。這些后來學(xué)者的觀點與劉建明的觀點比較接近。
聯(lián)想某些學(xué)者持有的“三個輿論場”的觀點,“三個輿論場”分別是體現(xiàn)黨和政府意志的輿論場,由新聞實踐構(gòu)成的媒體輿論場,民眾從自身利益、情感和意愿發(fā)出并形成的民間輿論場。經(jīng)常出現(xiàn)前兩個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不一致的情況。尤其是當(dāng)媒體所謂的“輿論”與真正的民間輿論不一致時,媒體應(yīng)該反思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而不能不負(fù)責(zé)任地認(rèn)為媒體的觀點是精英的、正確的,大眾的情緒就是非理性的、低智的。出現(xiàn)這種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樣的,有外界的,也有自身的。外界的原因比如地方政策、政治的原因;迫于商業(yè)和政治利益,一些媒體把宣傳等同于新聞等等。
在自身的原因方面,以2017年王志安“局面”報道江歌案為例來分析。該欄目以20多則短視頻的形式,報道了江歌案中江歌母親和江歌朋友劉鑫的見面。“局面”的初衷是“促進(jìn)溝通,彰顯理性”,拒絕謾罵,回歸到事實中來。而據(jù)傳播學(xué)研究者方可成的觀察,該節(jié)目微博下方的評論仍然集中在劉鑫身上,對其謾罵、充滿怨恨。方可成分析,“局面”欄目溝通與理性的初衷未能實現(xiàn),甚至走向了反面,因為曾經(jīng)主導(dǎo)輿論場的傳統(tǒng)媒體不再擁有把關(guān)的權(quán)力,這種權(quán)力部分回到了大眾手中,部分則被極其善于攫取注意力的營銷號自媒體拿走了。在江歌案的報道中,王志安的“局面”欄目可能未能理解“轉(zhuǎn)型時代媒體”和“復(fù)雜現(xiàn)實困境”的問題,帶有傳統(tǒng)媒體精英的思維模式,對大眾的反應(yīng)估計錯誤。所以方可成建議專業(yè)媒體尤其傳統(tǒng)媒體要反思,該用新的眼光來審視轉(zhuǎn)型中的所謂媒體權(quán)威、所謂把關(guān)人、所謂引導(dǎo)。
四、面對大眾情緒,專業(yè)媒體該如何應(yīng)對
首先必須確認(rèn),情緒是輿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無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媒體都應(yīng)該如實反映,找出背后的問題所在。
面對大眾不安、憤怒等負(fù)面情緒,專業(yè)媒體要繼續(xù)堅守新聞專業(yè)主義,挖掘負(fù)面情緒背后的真相,消除大眾的不安,更深層次的,就要適當(dāng)?shù)靥岢錾鐣栴}的解決辦法,抑或是提升大眾的媒介素養(yǎng)。正如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副院長史安斌認(rèn)為的那樣,在各類“話題”“爆款”“網(wǎng)紅”層出不窮的當(dāng)下,新聞媒體的專業(yè)性、權(quán)威性和公信力反而成了能夠產(chǎn)生最大價值的“稀缺產(chǎn)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后真相時代”的到來,為傳統(tǒng)主流媒體實現(xiàn)“浴火重生”提供了難得的契機(jī)。
當(dāng)大眾的注意力和情緒被某些自媒體帶入娛樂化領(lǐng)域,專業(yè)媒體要舍棄對流量的迷戀,不忘媒體公器屬性,要堅持嚴(yán)肅新聞,避免泛娛樂化傾向。例如,政治議題是自媒體較少涉及的領(lǐng)域。在今年“兩會”期間,一向愛蹭熱點的自媒體很少發(fā)聲,而當(dāng)部長通道上紅衣女和藍(lán)衣女的黃色新聞一下子撓到眾多自媒體的癢處時,很多自媒體一哄而上。而專業(yè)媒體與自媒體不同的是,它們?nèi)吸S色新聞發(fā)酵,還是牢牢抓住了部長答記者問的新聞核心,把大眾的注意力牽引到嚴(yán)肅新聞上來。比如俠客島就發(fā)表了《其實,今天那場引起熱議的采訪,干貨還是蠻多的》一文,顯示了專業(yè)媒體的水準(zhǔn)。
前文提到,各種情緒的爆發(fā)是社會撕裂的果。當(dāng)今社會提倡多元,但不等于提倡撕裂,和而不同是永遠(yuǎn)的追求,一些根本的、底線的價值觀就是“和”,媒體在凝聚共識、維護(hù)社會公共利益上有不可推卸的責(zé)任。新華日報評論部公眾號“江東觀潮”撰文指出,所謂“同心圓”就是事實和共識,當(dāng)發(fā)生了偏離或者出現(xiàn)偏離苗頭的時候,就需要傳播者警醒并采取措施。這也就是為什么新聞導(dǎo)向的重要性一再被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然,引導(dǎo)輿論并不意味著一定是走向輿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