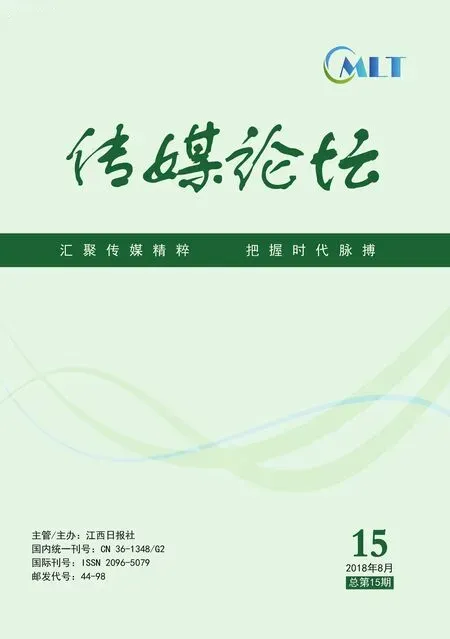《魯拜集》的譯介傳播,以及郭、黃譯本對比
(譯林出版社,江蘇 南京 210000)
一、引言
《魯拜集》是一部經典詩歌,在我國擁有眾多讀者,至今版本在五十種之上。波斯詩人千年前創作的這部詩歌集,為何魅力如此巨大?它是如何走出波斯,直至在中國廣為傳播的?對此,菲茨杰拉德著名的英譯本,以及近百年來層出不窮的中譯本可謂功不可沒。本文將對《魯拜集》及其譯介傳播作簡要介紹,并著重對比其中大受贊揚的郭沫若和黃克孫兩譯本,以期對翻譯傳播實踐有所促進。
二、《魯拜集》及其譯介、傳播
(一)《魯拜集》及其作者奧瑪珈音
“魯拜”是一種波斯詩歌形式,每首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韻,第三行大抵不押韻,和中國的絕句很類似。波斯有很多詩人都作有魯拜詩,最為有名的就是大詩人奧瑪珈音的《魯拜集》。他的魯拜多為感嘆人生變幻無常、倏然而逝,故當飲酒高歌、及時行樂之作。
奧瑪珈音(1048~1131),著名數學家、天文學家。除《魯拜集》外,他還留下多部科學著作,如《代數》《歐幾里得幾何難題》《論印度平立方根的求法》《金銀比重》《天文表》等。波斯于1079年頒布的歷法就是由他領導考訂的。奧瑪珈音的主要興趣是天文和數學,創作魯拜不過是旁及的活動。
(二)英譯本及其傳播
奧瑪珈音的《魯拜集》共750首詩,它們隨時光湮沒,漸漸被人們忘卻了。直到幾個世紀之后,英國學者、詩人愛德華·菲茨杰拉德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看到了波斯文《魯拜集》,立刻愛上這部詩集,并著手翻譯。菲茨杰拉德前后花費26年,完成了共計101首,發表為《奧瑪珈音的魯拜集》。譯本第一版默默無聞。它的命運在1860年出現了轉機,D.G.羅塞蒂首先發現了這部譯詩的好處,接著詩人斯溫伯恩同霍頓爵士也大力稱贊。菲茨杰拉德的譯本因而免于沉淪,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廣為流傳,大受贊揚。
美國作家、前國務卿約翰?海伊(1838~1905)評論菲譯本:“那些迷人的詩行美輪美奐,完美無瑕,那里頭的哲學深刻,生命的知識豐富,勇氣是那么無畏,直面終極的生死問題。讀者的好奇心被點燃,很多對東方文學一無所知的人,如我輩,都想去探索,去發現。我常常想,在11世紀,在遙遠的霍拉桑,真有這么一位文學巨人活著?后來我讀到《魯拜集》的一個‘忠實’譯本,我才明白,菲氏譯詩的最顯著特點之一恰恰是對原作的忠實。簡而言之,奧瑪珈音是菲茨杰拉德的前身,菲茨杰拉德是奧瑪珈音的投胎轉世。”
(三)在中國的譯介、傳播
奧瑪珈音的波斯文《魯拜集》已經少有流傳,中譯本多是從英文轉譯的,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從菲譯轉譯。《魯拜集》因大有魏晉風骨,契合了中國文人的情懷,因此大受推崇,譯本多達數十種。這里簡要介紹影響較大的譯本。
胡適在“五四”前夕譯有第7與第99兩首魯拜,將之稱為“絕句”,收入《嘗試集》中。它們成為最早譯成新詩的外國詩。隨后,郭沫若譯出了菲譯的全本,發表于1922年10月的《創造季刊》1卷3期上,隔年又以《魯拜集》為名推出單行本。聞一多讀了郭沫若的譯詩后,在該刊2卷1期發表文章,對其作出中肯評價,并在文后附上了自己翻譯的幾首魯拜。
此后,三四十年代,又出現了不少對菲譯本的漢譯,包括吳劍嵐、伍蠡甫于1935年發表的全譯本,孫毓棠于1939年發表的韻體新詩譯本,以及李意龍于1942年發表的舊詩譯本。1942年,潘家柏又發表了無韻新詩翻譯的《柔巴依集》,他的底本是另一位譯者的英譯。另外,1934年,朱湘發表了15首零星的魯拜譯詩。
四十年代,李霽野譯出整部詩集(但由于特殊原因,多年后才得以發表)。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陸沒有出現新譯本。八十年代,黃杲炘出版《柔巴依集》(1982)。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從波斯文直接翻譯的譯本:1986年張鴻年的《魯拜集》,以及1988年張暉的《柔巴依詩集》。九十年代,柏麗于1990年以七言、語體兩種形式的譯文出版了《怒湃譯草》。在臺灣,黃克孫在啟明書局出版了七絕譯本(1956),晨鐘出版社在同一本英漢對照本內推出孟祥森和陳次云的兩種譯本(1971),此外還有虞爾昌載于《中外文學》月刊的譯本(1985)。
正如黃杲炘所說:“無論是奧瑪珈音的原作,還是菲氏的英譯,更像是璀璨的鉆石,而每一個譯者就像是工匠,各自在這鉆石上打磨出一個有特定角度的反射面。譯者越多,這樣的反射面就越多,鉆石也就更光華四射。這些反射面還有折射作用,能夠折射出一些文學和非文學現象,折射出詩歌翻譯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在本文中,我們討論對比兩個廣為流傳的中譯本:郭沫若的自由詩體譯本和黃克孫的七言絕句譯本。
三、郭譯與黃譯《魯拜集》分析對比
(一)郭沫若的中譯本
1923年,郭沫若以菲譯為藍本,翻譯完成《魯拜集》,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近百年來,郭譯經久不衰。郭沫若本人是杰出的詩人,他的譯詩為自由詩體,用詞準確,節奏輕快,富有韻律感,風格明麗優美。郭譯秉承了其一貫的浪漫色彩,形神兼備,飄逸灑脫,很好地傳達了菲譯本的神韻。
(二)黃克孫的中譯本
黃克孫(1928~2016),詩人、翻譯家、麻省理工大學物理學教授。他與奧瑪珈音一樣,既是科學家,作為旁及活動的詩歌創作也極為出色。黃譯為七言絕句,每首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韻,第三行大抵不押韻的特點與魯拜相似。黃譯既保留了波斯原詩及菲譯的格律之美,又傳達了高逸的神采,可謂譯筆神來。黃譯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錢鐘書評價說:“黃先生譯詩雅貼比美Fitzgerald原譯。Fitzgerald書札中論譯事屢云‘寧為活麻雀,不做死鷹’(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況活鷹乎?”
下面我們就以第12首魯拜來說明郭譯和黃譯各自的特點。
郭譯與黃譯《魯拜集》第12首對比:
菲譯原文: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 – 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郭譯:
“樹蔭下放著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點干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伴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黃譯:
“一簞疏食一壺漿,
一卷詩書樹下涼。
卿為阿儂歌瀚海,
茫茫瀚海即天堂。”
郭譯和黃譯都在文本上忠實于菲譯,在意境中再現了原詩的風采。然而,它們又各有特點。
郭譯是散體詩,風格自由灑脫,帶有很強的節奏感,表現了浪漫隨性的生活情趣。譯詩中最為傳神的是三個“一”字:“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 “一點干糧”。一點干糧,生活儉樸,樂趣不在珍饈佳肴;一卷詩書,精神高遠;當然,盎然的興致中少不了美酒。讀者們仿佛看到一個正在濃濃的樹蔭下斜倚著樹干、微微敞開衣襟的詩人,正凝神傾聽美人的歌聲,詩章已然滑落,唇邊還掛著酒珠。而遠處的背景則是突兀的荒原,這更突出了詩人自得其樂的浪漫情懷。一個“歡”字,是畫龍點睛之筆,詩人超脫物外,與美人讀詩、飲酒、高歌,盡享歡樂的形象躍然紙上。
黃譯是工整的七言絕句。絕句是古詩的一種形式,相對格律詩而言,絕句對平仄的要求不是那么嚴格。這種稍微自由的形式,能夠表達《魯拜集》將及時行樂作為人生寬解的襟懷。絕句一、二、四行押韻,與魯拜詩在形式上契合。而七言絕句字數較多,能夠承載豐富的信息,表現出詩歌的深刻含義。“涼”字烘托出了全詩的意境。茫茫的荒漠,熱氣灼人,這個“涼”不僅是因為詩人坐在樹下,更寫出了其清凈的心境。正是這樣的心境,讓詩人滿足于“一簞疏食一壺漿”的簡樸物質生活,能將荒漠當作天堂。將荒漠譯為瀚海,表現了荒漠的廣闊,背景更加雄渾、深遠。
(三)關于黃譯中的中國文化特色詞匯
黃譯將大部分的波斯特色詞匯譯為了有中國古典特色的專有詞匯,或是加進了一些中國文化的詞匯。比如,在第9首中將alchemist譯為“葛洪”。alchemist意為煉丹術士,而書中注葛洪是“晉人,好神仙術,赴交趾煉丹,丹成尸解”。甚至在幾首詩中不僅存在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也存在波斯特色的詞匯。比如,第一首的中文譯文是“醒醒游仙夢里人,殘星幾點已西沉。羲和駿馬鬃如火,紅到蘇丹塔上云”。這首譯詩中既有中國神話中的太陽神羲和,又有波斯的君主蘇丹。這樣是否合適?會不會使讀者產生疑惑?這種“中西結合”會不會影響詩歌的意境?每個人的見解是不一樣的。黃譯的廣為流傳似乎說明了很多人能夠接受,甚至是欣賞這種處理手法。畢竟,黃譯不是對詞句的轉換,其本身就是經得起推敲的好詩。
四、總結
《魯拜集》因為菲茨杰拉德的翻譯而廣為流傳,成為文學經典,這是翻譯史上的一段佳話。《魯拜集》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這從眾多的譯本可以看出來。每位譯者都有自己的體會、理解和翻譯特色,都為《魯拜集》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對這些譯本流傳過程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文學的傳播,對文本的對比有助于加深對翻譯的認識,更好地進行翻譯傳播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