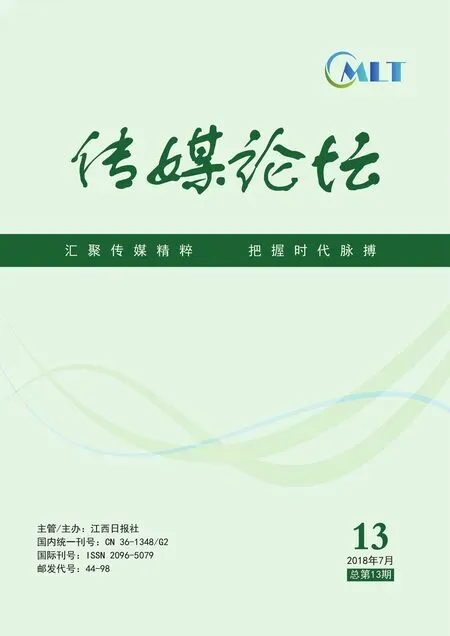論佛教文化對《聊齋志異》人物塑造的影響
(重慶財經職業學院,重慶 402160)
蒲松齡一直以為他是和尚的轉世靈童。在《聊齋自志》中,曾經說過:“在三塊石頭上,我明白了原因。”那么,蒲松齡對他前世的看法是什么?在文章中他說,在他出生前夕,他的父親夢見一個胸前有胎記的瘦僧,直奔臥室。當蒲松齡出生時,他和父親有著同樣的夢想,胸前有一個胎記,這不能不讓他相信他是一個修道士的轉世靈童。除了他艱苦的生活經歷和艱難的生活條件,一個真正修道之人和貧窮的和尚也沒有什么不同。更有說服力的是,他相信僧人的轉世。可以看出,蒲松齡確信他是僧侶的轉世靈童。在清代,著名的玉谿庵是由蒲松齡的父親建造的。可以看出,他堅信他是僧侶的轉世和家庭的傳統,崇拜佛陀,蒲松齡信仰佛教也就理所應當了。
一、聊齋故事中佛教文化的推崇
在《聊齋志異》的許多故事之中,無不體現出佛法無邊,以此來展現對佛教文化的推崇,其體現方式主要包括:看佛經、看佛號、看佛像、故事發生地點等。
(1) 看佛經。在《林四娘》篇,因遭國難死后十七年難以托生的林四娘,在認識陳寶鑰后,“每夜都起念準提、金剛經咒”,僅僅三年就托生王家。至于其原因,正如女所說“閻王認為我出生前無罪,死后還不忘經咒,才讓我投生于王家”,可見佛經作用之大。
(2) 念佛號。在《江城》篇,篇中的江城可謂忌妒忤逆之極,不但不尊重公婆,甚至對自己的親生父親也毫不客氣,最終導致父親被活活氣死。對自己的丈夫高蕃,江城更是飽受折磨,不但動輒打罵,更因丈夫和婢女說了幾句話,就“把婢女肚子上的肉用繡花剪剪掉”。高蕃父母倍感無奈之際,高蕃母親一晚夢到神人諭示:每早起床,虔心誦佛號百遍,一定會有效果。
二、佛教故事對人物塑造及人物性格的影響
(一)佛教文化對人物塑造的影響
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明白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真諦。在《顧生》的一篇文章中,顧生被邀請進入一座巨大的房子看戲,他在途中有點晚了。當他順原路而進入,之前的嬰兒已成為頭發蓬亂駝著背的老太太,年輕王子下巴下已經長出一尺多的胡子了。一眨眼,年輕人已老,時間是無情的,這是作者的生活經歷。
(二)佛教因果觀念對人物性格的影響
佛教一直推崇所謂的“因果循環”及“業感緣起”學說,這些在《聊齋志異》的故事中屢見不鮮,如王六郎以仁慈之心造化世人最終修成正果,最終被玉帝封為一方土地,造福鄉里;穆生因貪財忘義、恩將仇報,最終也未逃脫應有的報應,如此這般的故事不勝枚舉。而我們所要講的主要是《聊齋志異》中的人物性格及形象是如何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的。佛教文化中講究的是前世今生、六道輪回、靈魂不滅、飛天遁地,這些理論為蒲松齡的作品創作提供的廣闊的想象空間及創作靈感。《聊齋志異》許多故事中人物都因為前世今生的種種因果,今世所種的惡果,今世沒有報應,也會在來事承受,而且對于一些道行高深的人是可以自由行走在天、地、人三界之間的。這些佛教元素不僅對故事的情節進行了渲染,而且讓人物的形象被刻畫得更加栩栩如生,并且完美地表達了作者想要傳遞給讀者的思想。如《連城》中,連城和喬大年因積德行善,所以可以在人間與陰曹地府之間自由出入,而且還可以同生共死、死而復活,這正是在佛教的轉世觀的基礎上進行改編創作的,這也讓《聊齋》中的故事發生在了天地人三界,也包括了人物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大大加強作品的玄幻色彩。
(三)以佛教特有的僧侶觀念塑造人物形象
《聊齋志異》創造了許多閃亮而逼真的人物,包括與僧侶活動相關的約四十部小說。大量的佛教人物,佛祖、得道高僧,有不同的面孔,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他們充滿了佛教文化。這些佛教人物的成功刻畫,顯示出獨特的佛教文化觀念對人物形象形成的深遠影響。在《聊齋志異》中,許多正面的僧侶,反映了佛教獨特思想對蒲松齡創作的直接影響。例如,長清僧就是這些僧侶的代表,這位和尚是長慶縣一名70歲的得道高僧。在他去世后,他的靈魂與一位已經去世的鄉紳的兒子聯系在一起。仆人將帶他到他家,面對美麗的妻子和家里的美酒以及萬貫家財,長清僧絲毫不心動,卻堅持回到長清縣的原始寺廟,在那里繼續他曾經的修行。
三、結束語
總之,蒲松齡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佛教文化的啟發及影響,其中有因為自身家族傳統的影響,有來自的那個歷史時代的影響,也有來自于個人生活感悟及生活閱歷方面的影響。而在《聊齋志異》作品中,許許多多的人物形象的創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這不僅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豐滿,也更加貼合那個時代讀者的喜好,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靈活現,更對在此之后的文學創作的藝術形式及創作技巧產生了一定的指導意義,并且其作品也得到了廣大讀者的一致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