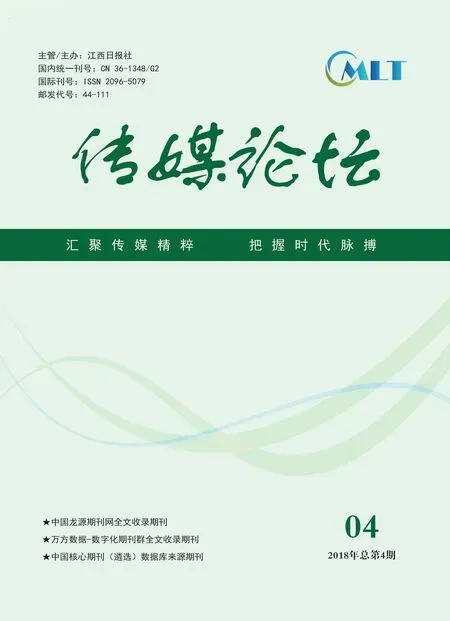以《故宮100》為例探析微紀錄片創作及意義
戚 箏
(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微紀錄片興起
(一)新媒體與媒介融合
石磊在《新媒介概論》中對新媒體技術的定義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全面的傳播促使各種媒介間的交融互通,傳統媒體上的創作形式向新媒介移植。
(二)微文化的興起
新型媒介生態的變化使創作形式、內容和傳播方式發生了改變,新媒體受眾接受方式體現出碎片化、即時性和隨機性的新特征。微紀錄片作為微電影的雙胞胎兄弟和微電影一樣最早來自于UCG(用戶原創內容),隨著微概念的深入人心,其中的商機被發掘。微紀錄片從個體非專業創作的紀錄短片走向了更專業化的商業作品。
二、微紀錄片創作特點——以《故宮100》為例
相比長篇紀錄片篇幅,微紀錄片就只能算是超短分集。微紀錄片不能拋棄紀錄片的本質,將傳統紀錄片的內核與新特征相融合才能產生優質的微紀錄片作品。
(一)平民化
新媒體時代的環境為受眾提供了豐富多元的信息,平民化越來越成為紀錄片創作的追求。平民化趨勢體現在兩點:第一,選材、內容和創作形式貼近平常百姓生活,從平常人的生活中提煉出樸素的哲學和普世價值觀;第二是選擇普通人的視角、平等的態度與觀眾進行精神溝通,讓觀眾自身對內容進行判斷和思考。第67集《海棠依舊》以永壽宮為背景,講述“貍貓換太子”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最后將落腳點放在明孝宗一生只娶一后、過尋常百姓夫妻生活上,引起觀眾共鳴,喚起對深宮斗爭殘酷的無限唏噓。
(二)切口小
微紀錄片的短小篇幅要求作品在敘事上盡量簡單,首先,微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觀察事物視角的小切口,以小見大。選題要從細節出發,在創作上較為靈活;作品不會為了整體敘事而舍棄部分細節和主題。《故宮100》圍繞著北京故宮為中心,以紫禁城的建筑物為切入點,選取一百個具體主題來描寫故宮。攝制組捕捉到很多常人難以察覺的細節,將其放大成篇。
(三)視角新
《隱形的歷史》一集故宮是現代與歷史的交匯點,袁世凱稱帝、尼克松訪華等重要歷史事件中,故宮是沉默的背景,也是時間流過后唯一留下的實物,它既是見證者,也是傳承人。這種特殊的視角在傳統紀錄片并不常見。
(四)娛樂性強
據微紀錄片的制作人說,此次《故宮100》的拍攝是為了吸引更多年輕觀眾。制作組在創作上特別加入了娛樂性因素,第7集《威猛銅獅》中,采取了擬人的方式,“我是百獸之王,也曾叫狻猊。我是龍的兒子,也是佛的坐騎……我本來自西域,東漢才到這里……身影并不孤單,伙伴就在附近。”一段解說詞讀起來押韻,介紹銅獅的來源和使用目的。
(五)傳播知識
傳播知識也是微紀錄片的一大任務。微紀錄系列片可以用多集、每集一個小點起到教育功能,《故宮100》正是秉承這一點,如第14集《金磚漫地》里,展示傳統制磚技藝,同時將金磚的價值與當時官員俸祿和糧食價格對比,讓觀眾對明清時期物價有所了解。
三、微紀錄片的意義
(一)制作上可能產生的問題
微紀錄片的制作數量逐年增加,不少平臺如梨視頻等推出了自制的微紀錄片作品。其中不乏制作上乘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是反映社會中難以窺見的角落。
微紀錄片發展到今天,存在的問題已經開始顯現。一是內容淺薄化。一些微紀錄片制作專注于敘事和拍攝技巧,并沒有深度挖掘故事內涵;二是制作欠缺。微紀錄片之微不應反映在本身的制作上。篇幅的縮小更應該提高創作水平,在微縮題材里用文本和鏡頭語言表達創作者的構思。
(二)傳播渠道
在新媒體融合的大趨勢下,網絡和電視都不能作為微紀錄片傳播的單一平臺。臺網聯合成為微紀錄片制作推廣的必然趨勢,專業的電視團隊加入新媒體平臺,制作出精良優秀的微紀錄片作品。網絡平臺的自制節目輸入到電視,電視臺會選擇與網絡平臺網站合作,將專業的技術、團隊輸入微紀錄片制作中。
四、總結
微紀錄片是適應新媒體平臺和媒介融合背景而誕生的產物,不少人說微紀錄片是屬于草根,是屬于年輕人的。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并不全面,優秀的創作形式應當是被社會大部分成員認可并接受的,不能為了迎合部分觀眾而放棄紀錄片制作的基本原則,讓社會看見微紀錄片因“微”而優,不是因“微”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