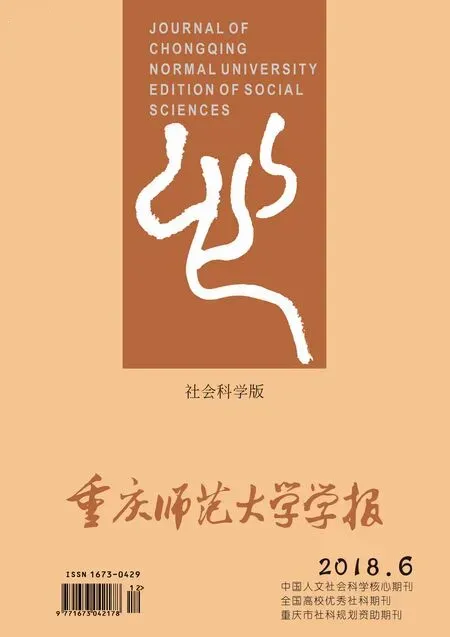張竹坡評點《金瓶梅》動因論析
曾志松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上海 200234)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緣由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揭示《金瓶梅》中的文法。張竹坡盛贊《金瓶梅》的文法“針線縝密”“千針萬線,同出一絲”“曲曲折折不露一線”,而“圣嘆既歿,世鮮知者,吾將拈而出之”[1]212。另外一種說法是寄托說。張竹坡族人張省齋提出:“道深……曾批《金瓶梅》小說,隱寓譏刺”。[2]88隱寓內(nèi)容,則語焉不詳。至于是否含有寄托,張竹坡的表述則前后抵牾,《第一奇書凡例》:“作《金瓶梅》者,或有所指,予則并無寓諷。”[3]1476《竹坡閑話》說:“然而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梅》也哉。”[3]1482評點的動因會對評點的結(jié)果產(chǎn)生重大影響,鑒于“知人論世”的批評傳統(tǒng),學界對這一問題涉及較多,但多泛泛而談。筆者僅見楊楊的碩士論文“從具體的客觀條件和事實來分析張竹坡評點背后的心理結(jié)構(gòu)”[4]12,對這問題給予了較多關(guān)注,但可繼續(xù)深入的空間還有不少。
一、 家世巨變,借評點遣悶懷
張竹坡出生于一個官宦之家。伯父張膽、張鐸入清后都做過高官。其父一生不仕,在家奉養(yǎng)母親,正因為這一點,張竹坡家受到伯父們的資助,少年時代張竹坡家境寬裕。張竹坡自己在詩作也說“少年結(jié)客不知悔,黃金散去如流水”[5]261(《撥悶三首》),表明日子過得非常殷實。據(jù)吳敢先生的考證[2]64-89,與他們家族有交游的文化界的名人有:陳貞慧、李漁、尤侗、侯方域、張玉書、戴名世、張潮等等。如此盛大的交游圈也是張竹坡家族鼎盛的一個旁證。
十五歲是張竹坡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張竹坡父親去世,他的生活走向貧困。張竹坡在他二十六歲那年評點《金瓶梅》。在評點的過程中,他寫了一首《乙亥元夜戲作》,有句云:“歸來雖復舊時貧,兒女在抱忘愁苦。”[5]260其間“舊時貧”表明他的境況已經(jīng)很久了,他說“忘愁苦”,實際上卻表明他忘不了。《金瓶梅》的評點使他“才名日振”[1]212,但名聲的擴大并沒有使他擺脫貧困。張竹坡在二十七歲秋冬之際參與了《幽夢影》的評點。《金瓶梅》和《幽夢影》的評點在時間上接近,可以大致認為《幽夢影》的一些評語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體現(xiàn)了他內(nèi)心的狀況。在《幽夢影》評點中,張竹坡不止一次提到貧病的窘困。《幽夢影》第23則原文是:“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張竹坡評曰:“我幸得極雅之境。”[6]40第69則談及著新書注古書均是千秋偉業(yè)。張竹坡評云:“注書無難,天使人得安居無累,有可以注書之時與地為難耳。”[6]84他在第122則評曰:“無益之心思,莫過于憂貧;無益之學問,莫過于務名。”[6]129他雖然認為“憂貧”“務名”是最“無益”的,但是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憂貧”“務名”的深層心理。
少年富足與失怙之后生活上的落差,使張竹坡較早感受到人情的冷暖。他十九歲時作《烏思記》感慨:“至于人情反復,世事滄桑,若黃河之波,變幻莫測;如青天之云,起滅無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7]129張竹坡的伯父張膽、張鐸功名顯赫,張竹坡卻處于“久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的境況。“孤立”心理的產(chǎn)生,應該與來自伯父一支的“人情反復”相關(guān)聯(lián)。張竹坡在《幽夢影》第93則的評語也指向此:“求知己于兄弟亦難。”[6]103張竹坡有親弟弟張道淵,從張道淵為張竹坡立傳及傳中贊語的情況來看,他們兄弟是知己。據(jù)王汝梅先生考證,張道淵在張竹坡死后曾經(jīng)主持過張評本的復刻修訂[8]106。因此,張竹坡的這則評語不是針對他的胞弟張道淵而言的。考慮到他在《烏思記》所說的“人情反復”“白眼窮途”之語,他這句話所指是他父輩的兄弟或者他的堂兄弟。
張竹坡在《金瓶梅》的評點中表現(xiàn)出對兄弟倫理的呼喚,《竹坡閑話》:“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3]1480-1481張竹坡視父子兄弟等“倫常”為“天下最真者”。相應的對“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予以批評,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富貴金錢對倫常的沖擊作用:“將富貴,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3]1481聯(lián)系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前后的相關(guān)文字——上文提到的《烏思記》和《幽夢影》中的評語——我們認為,張竹坡這段針對財富顛倒倫常的議論是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如果說這里的議論是在借議論小說《金瓶梅》而隱藏自己的鋒芒,那么在《竹坡閑話》的結(jié)尾則跳出評論,直指現(xiàn)實:“邇來為窮愁所迫,炎涼所激,于難消遣時,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3]1482由此看來張竹坡有借《金瓶梅》這一部“世情書”來感慨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的直接訴求。
正是因為張竹坡在《金瓶梅》的評點中隱藏了對族兄的不滿,才會導致張省齋指出張竹坡“批《金瓶梅》小說,隱寓譏刺”卻又語焉不詳。張道淵則避而不談。張竹坡既想挑明,又想掩飾,從而前后矛盾。
二 、久困棘圍,借評點暢心志
張竹坡早慧,六歲時即能即興對出“河上觀音柳,園外大夫松”[9]73的佳句。據(jù)張道淵《仲兄竹坡傳》記載,張竹坡有“讀竟復誦,只字不訛”[2]246的過目不忘的神奇智慧。
張竹坡的父親雖然自己不愿出仕清朝,但寄希望于早慧的張竹坡,希望他早日取得功名。張竹坡自己也極度自信,有“壯志凌宵志拂云”[5]261的抱負。但現(xiàn)實人生卻是非常不幸:“五困棘圍,而不能博一第。”[2]247十五歲的張竹坡首次參加鄉(xiāng)試落第。十八歲再次落第。他性格中盼望出人頭地的一面開始以凄厲的形式出現(xiàn),作于十九歲的《烏思記》云:“矧予以須眉男子,當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奮鵬飛,奉揚先烈,槁顏色,困行役,尚有何面目舒兩臂系五色續(xù)命絲哉。”[7]129他認為不能在功名場上揚眉吐氣,便連“舒兩臂系五色續(xù)命絲”的面目都沒有。二十四歲,張竹坡第四次落第。那年冬天,張竹坡特意北游京師,訪長安詩社,“登上座,竟病分拈,長短章句,賦成百余首。眾皆壓倒,一時都下皆稱竹坡才子云。”[1]211張竹坡此舉意在表現(xiàn)他文學方面的才華。他的愿望得到了實現(xiàn):“一時都下皆稱竹坡才子云”。但是名聲的獲得沒有幫助張竹坡擺脫貧困,也沒有幫助他獲取功名。他在《乙亥元夜戲作》稱“歸來雖復舊時貧,兒女在抱忘愁苦”,“歸來”指的是長安詩社奪魁歸來,其生存狀況依然是“舊時貧”。
二十七歲,也就是評點《金瓶梅》的那年秋天,張竹坡第五次落第。他對科舉、君主乃至天命都開始懷疑,但對自己才華的自信仍在,在《幽夢影》的兩則評語反應了這一心態(tài)。《幽夢影》第63則原文:“十歲為神童,二十三十為才子,四十五十為名臣,六十為神仙,可謂全人矣。”[6]79-80對于這一全人的人生模式,張竹坡云:“神童才子,由于自己,可能也;臣由于君,仙由于天,可不必也。”[6]80這一評語中表現(xiàn)出了對“君”“天”的不信任。第180則原文:“寧為小人所罵,毋為君子所鄙;寧為盲主所摒棄,毋為諸名宿之所不知。”[6]184張竹坡評道:“后二句少足平吾恨。”[6]184張竹坡將那批掌管科舉路徑的“主”斥為“盲主”,對自己才華信心滿滿的言外之意便相當明顯了。
即便五次落第,張竹坡依然尋找著建立功名的機會,“眼前未得志,豈足盡平生”[5]261。在張竹坡人生的最后兩年中,先是貧病客居于蘇州,之后北上,效力于“永定河工次”。清廷甚是重視治水,借此獲得富貴者不計其數(shù),僅張竹坡一族就有道源、道溥、道汧等取譽于此。同族兄弟的成功之道必定給張竹坡巨大刺激與希望。在久困棘圍之后,張竹坡為自己找到了一條通向“男兒富貴”的道路。在“永定河工次”,張竹坡“雖立有羸形,而精神獨異乎眾,能數(shù)十晝夜目不交睫,不以為疲憊”[1]212,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熱情。不幸的是在永定河工程竣工的時候,“嘔血數(shù)升”而亡,所留遺物“惟有四子書一部,文稿一束,古硯一枚而已”[1]212。 “四子書”即四書。從張竹坡的遺物來看,張竹坡在永定河工程上依然在準備科舉考試,表明他對科考獲取功名并沒有完全絕望。
張竹坡把自己對科考既失望又保持希望的復雜心態(tài)帶到了評點中。《金瓶梅》中西門大宅里是“一片淫欲世界”[3]1512,眾多婦人中唯有孟玉樓有較好結(jié)果:再嫁給李衙內(nèi),夫妻敬愛有加。張竹坡把孟玉樓的好結(jié)果歸因為“寬心忍耐,安于數(shù)命”[3]1500。孟玉樓因“寬心忍耐”而獨有結(jié)果,恰好符合張竹坡久困棘圍而依然盼望成功的心境。所以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特別重視孟玉樓,認為作者寫玉樓是“自喻”:“至其寫孟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jīng)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3]1486《金瓶梅》作者是否有意識地在孟玉樓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寄托,這是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張竹坡在孟玉樓身上投注了寄托則是毫無疑問的,他主張將《金瓶梅》的題目更換為“奇酸記”:
……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結(jié)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3]1488
張竹坡“含酸”“抱阮”云云,是對“高才被屈,滿腹牢騷”[3]1495的孟玉樓的內(nèi)外處境的一種總結(jié)。他在《竹坡閑話》中說得更清楚:“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3]1480以“奇酸記”來命名小說就相當于將孟玉樓設置為全書的中心人物,將西門慶、潘金蓮等設置為背景元素。張竹坡將一個相對次要的人物看成是最重要的人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孟玉樓最后有了一個好的結(jié)果。《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最后一則亦云:“以玉樓彈阮起,愛姐抱阮結(jié),乃是作者滿肚皮倡狂之淚沒處灑落,故以《金瓶梅》為大哭地也。”[3]1513我們也可以說張竹坡的“滿肚皮倡狂之淚沒處灑落”,所以借《金瓶梅》中的玉樓來抒發(fā)他內(nèi)心對待功名既失望又有希望的復雜心理。
文章開始時說過,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緣由之一是揭示小說中的文法。這是事實。《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開列了108則“讀法”,在數(shù)量上遠遠超過金圣嘆給《水滸傳》開出的15則。需要指出的是張竹坡從整體結(jié)構(gòu)和細部伏線等方面開列出108則讀法,其目的不僅僅是“喜其文之整密,偶為當世同筆墨者閑中解頤”[3]1476,其性質(zhì)與詩社奪魁一樣,是表明自己在文章方面才華出眾,當下功名未就僅僅是時運不到而已,這也是他對自己功名尚保持希望的一種證明。
三、 奉揚先烈,借評點推崇孝悌
張竹坡家族篤守孝道,張竹坡的父親就以奉養(yǎng)母親而不出仕。張竹坡的家庭重孝道最為突出的例子是胞妹張文嫻“算取花剪割股”[2]72偷偷地放在藥鼎之內(nèi),以求父親病愈。兩年后,張竹坡十五歲時,張父去世,張竹坡“哀毀致病”[1]211。盡孝,奉揚先烈,甚至成為張竹坡追求功名的內(nèi)在動力之一:
偶見階前海榴映日,艾葉凌風,乃憶為屈大夫矢忠、曹娥盡孝之日也。嗟乎,三閭大夫不必復論。彼曹娥,一女子也。乃能逝長波,逐巨浪,貞魂不沒,終抱父尸以出。矧予以須眉男子,當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奮鵬飛,奉揚先烈,槁顏色,困行役,尚有何面目舒兩臂,系五色續(xù)命絲哉![7]129
曹娥是東漢有名的孝女,《后漢書》有傳。十九歲的張竹坡將曹娥與屈原并舉,可見曹娥所代表的孝在張竹坡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張竹坡認為“當失怙之后”,就應當“一奮鵬飛,奉揚先烈”,即獲取功名光耀祖宗。
二十六歲,已是四次落第的張竹坡,在《乙亥元夜戲作》稱:“男兒富貴當有時,且以平安娛老母”,[5]260“娛老母”依然是他重要的職責。張竹坡做過一篇《治道》[2]243-245,寫作年份不可考,但可以看作是他為“帝王師”的人生理想而撰寫的一份施政綱領。在這篇綱領性的短章中,他認為“三代以上為政易,三代以下為政難”[7]127,其原因在于“人心不正,風俗以頹”[7]127。正人心淳風俗的關(guān)鍵在于“古人生而孩提之時,即教以父母之當孝也,兄長之當敬也”[7]127。孝悌儼然成為張竹坡“治道”中最為根本的一環(huán)。
在生活中,張竹坡篤守孝道。在《金瓶梅》的評點中,張竹坡也特別重視挖掘小說中“孝”的因素。首先,他認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一個孝子。《竹坡閑話》中云:“《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3]1480這樣就把《金瓶梅》理解為“孝子悌弟”的發(fā)憤之作。其次,張竹坡認為《金瓶梅》寫作的動機是表達作者作為孝子的苦楚。他專門寫了一個專論叫《苦孝說》:
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結(jié)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馀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3]1488
張竹坡從他認定的作者是孝子出發(fā),認為《金瓶梅》應當命名為《苦孝說》,其目的也在于突出孝。張竹坡對“孝”的重視在《第一奇書目》[3]1477-1479中表現(xiàn)得相當突出。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中有一種重要的文法叫“兩對章法”[3]1493,所謂“兩對”即每一回中主要敘述兩件事。具體參見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第8則。張竹坡將每一回目的兩個關(guān)鍵詞抽出,組成了《第一奇書目》,這實際上可以看做是整個小說的大綱。張竹坡對這大綱式的“目”,一共添加了9條批語。為了論述方便,筆者將其按順序摘錄如下,并添加序號:
1, 一 回 熱結(jié) 冷遇 〇弟字起。
2, 十 回 充配 玩賞 〇金、瓶、梅三字至此全起。
3, 廿一回 掃雪 簪花 〇金、瓶、梅三人至此暢聚。
4, 廿九回 冰鑒 蘭湯 〇全部結(jié)束
5, 四十六回 走雨 卜龜 〇兩番結(jié)束
6, 五十八回 打狗 磨鏡 〇孝子著書之意在此,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此回以一個“孝”字照應一百回孝哥的“孝”字。
7, 七十五回 含酸 撒潑 〇是作者一腔憤恨無可發(fā)泄處。
8, 九十七回 假續(xù) 真偕 〇一部真假總結(jié),照轉(zhuǎn)冷熱二字。
9, 一百回 路遇 幻化 〇孝字結(jié)。
這9條評語中,第2、3兩條是指人物的出場、會聚、及其活動,第4、5兩條是預述人物命運,即為書中人物“遙斷結(jié)果”[3]399,這四條評語的關(guān)注點在于書中的人物。明清之際的小說批評家都重視人物,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與本題無關(guān),此從略。“人情冷暖”的感慨和“高才被屈”的窘境分別由第7、8條來承擔。強調(diào)孝則有第1、6、9條,占三分之一強,可見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對孝的重視[10]。
張竹坡在生活中篤守孝,在治國理念中強調(diào)孝,在小說評點中突出孝。張竹坡于孝,真正做到了知和行的統(tǒng)一。對于自視甚高卻又終未釋褐的張竹坡來說,孝不僅僅是儒家的一種道德規(guī)范,還是一種人格上的精神支柱。
評點《金瓶梅》是張竹坡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小說批評史上的一件大事。評點《金瓶梅》讓他名垂千古,但他志不在此。張竹坡寫過三首題詠古人的詩,分別題詠“留侯”“酂候”“淮陰侯”[5]263,詩歌中對張良“終得騁其志,功成鬢未絲”、蕭何“授漢以王業(yè),卓哉人之雄”的成功人生表示了無比的艷羨,其間也有著自比張良、蕭何的成分,在他內(nèi)心有著“作帝王師”(《留侯》)的人生理想。對于武功赫赫最終被誅的韓信,則頗有微詞:“既然用武善,為甚識機遲”(《淮陰侯》)。他寫過《治道》一文談論如何治理天下。但他最終沒有成為“帝王師”,反而貧困交加,飽受人情冷暖。張竹坡評點《金瓶梅》屬于“發(fā)憤著書”,與李贄、金圣嘆評點《水滸》一樣都是有所寄托的,他在《金瓶梅》評點中所蘊含的寄托不僅僅是張省齋所說的“隱寓譏刺”,還包含了更為廣闊的生活態(tài)度以及人生追求。吳敢先生指出:“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把自己的家世遭遇情緒感觸擺進去”,[11]17洵為的論。但是,張竹坡評點時主觀情緒過于強烈,以至于他所闡釋的主旨多與此相關(guān),這就要求我們在接受張竹坡留下的這份珍貴遺產(chǎn)時需要冷靜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