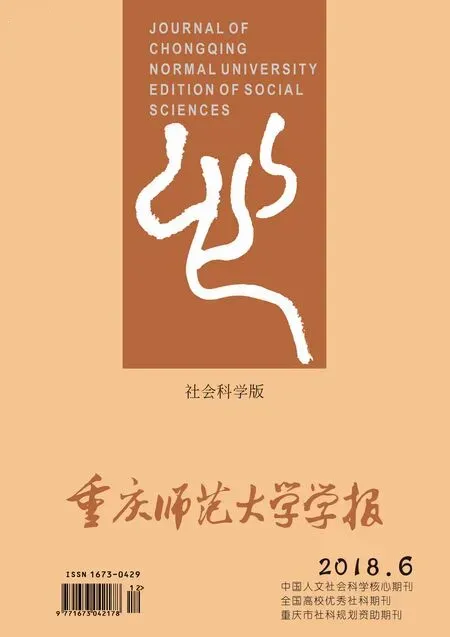抗戰時期重慶反法西斯音樂的創作、會演及對外交流
艾 智 科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抗戰文化研究所,重慶 404000)
抗戰全面爆發后,反法西斯音樂成為音樂界發展的一個主流。戰時重慶的音樂工作者在音樂創作、交流等方面普遍體現了反法西斯主題,這是當時中國與世界最為相近的音樂旋律。學界對抗戰時期的音樂有不少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如陳子昂的《抗戰音樂史》,介紹了戰時不同階段、不同區域的音樂作品和音樂運動;王續添的《音樂與政治:音樂中的民族主義——以抗戰歌曲為中心的考察》則從民族主義的視角探討了抗戰音樂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同時分析了抗戰音樂對構建民族主義的影響。也有針對音樂家的專題研究,如湯斯惟的《重慶時期的李抱忱音樂教育思想探析》一文討論了著名音樂家李抱忱在重慶時期,就音樂師資培養、課外音樂活動、音樂教材編訂、音樂教具創制、音樂督學制度、音樂學會創設等方面所作的探索和貢獻。另外,還有一些關于戰時音樂的回憶錄或其他史料整理,在此不一一贅述。縱觀這些成果,有關戰時音樂對外交流的研究并不多見,但這恰恰是反映戰時中國音樂發展的重要內容。從文化交流史的視角來看,戰時音樂對外交流對音樂自身的融合、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在反法西斯宣傳上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重慶是抗戰時期大后方重要的文化陣地,大量音樂家、音樂組織都聚集在此,他們開展反法西斯音樂創作和對外交流,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
一、譜寫反法西斯樂章
中國音樂界在反法西斯音樂的創作上起步較早,“九一八”事變之后,就有黃自作曲的《九一八》《抗敵歌》《旗正飄飄》等,聶耳作曲的《大路歌》《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逃亡曲》《打長江》等,洗星海作曲的《半夜歌聲》《流民三千萬》《青年進行曲》《救國軍歌》《黃河大合唱》《太行山》《到敵人后方去》《熱血》等,呂驥作曲的《中華民族不會亡》《自由神》《示威歌》《九一八小調》,閻述詩作曲的《五月的鮮花》,張定和作曲的《流亡之歌》,孫慎作曲的《救亡進行曲》,張寒暉作曲的《松花江上》,任光作曲的《漁光曲》《打回老家去》。隨著全國性抗戰的到來,大批音樂人和音樂團體遷聚在重慶,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下,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音樂創作持續繁榮,產生了大量反法西斯音樂作品,它們與同一時期的世界反法西斯音樂交相呼應,共同構成了東西方音樂創作的主要內容。這些作品一經誕生,就被不斷傳唱,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就世界范圍來看,這一時期反法西斯戰斗處于僵持階段,各地戰斗異常激烈,戰爭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破壞,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蘇聯方面,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亞歷山德羅夫的《神圣的戰爭》、馬特維·勃蘭切爾的《喀秋莎》等,美國反法西斯作品《時光流轉》《老兵不死》等,以及意大利游擊隊歌曲《啊,朋友再見》等,都廣為世人傳唱,成為世界樂壇開展反法西斯斗爭的經典之作。在中國,廣大音樂工作者投入到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洪流中,掀起了極高的創作熱情。在此影響下,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音樂界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描寫死守上海的《歌八百壯士》、敘述湘北大戰的《勝利進行曲》、表贊山西鄉寧縣殲敵的《歌華靈廟》、電影名曲《中華兒女》,端木蕻良作詞、賀綠汀作曲的《嘉陵江上》,江村作詞、張定和作曲的《嘉陵江水靜靜流》,沈群作詞、王云階作曲的《東北是我的家鄉》,楊友群作詞、汪秋逸作曲的《夜夢江南》,韋瀚章作詞、中和作曲的《白云故鄉》,潘孑農作詞、劉雪庵作曲的《長城謠》,賽克作詞、賀綠汀作曲的《全面抗戰》,老舍作詞、張曙作曲的《丈夫去當兵》,賀綠汀作詞作曲的《游擊隊歌》,麥新作詞、孟波作曲的《壯丁隊歌》,胡然作詞、江定仙作曲的《打殺漢奸》,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的《高粱紅了》,莫耶作詞、鄭律成作曲的《延安頌》,蕭三作詞、洗星海作曲的《打倒汪精衛》,光未然作詞、夏之秋作曲的《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朱光作詞、呂驥作曲的《慶祝抗日軍勝利》,等等。抗戰時期,各類音樂工作者創作的歌曲多達數千首,至今仍難以全面統計。1939年底,國民黨中宣部考慮到抗戰時期歌曲繁多,“選出內容平妥及有利抗戰之歌曲73首”,同時又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委托中國文藝社選出軍歌7首,前后共80首定名為《民族歌聲》,由中國戲曲編刊社發行(《編選抗戰歌曲集》,《中央黨務公報》,1939年,第1卷第22期,第26頁)。1958年,音樂出版社曾搜集抗戰歌曲編成三卷出版,共收錄146首。不同時期的研究者對抗戰歌曲都作了整理,但由于資料的局限,以及個人所持觀點和知識結構的不同,歷次抗戰歌曲選編都有較大的不同,它們都只能代表了抗戰歌曲的一部分,反映了戰時音樂創作的局部。
除此之外,重慶還有一些民間創作的反法西斯音樂,戰時也較為流行。據《抗戰大后方歌謠匯編》所收錄的歌謠來看,戰時大后方創作的反法西斯歌謠超過600首。其中,在重慶《新蜀報》《商務日報》《國民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掃蕩報》等報紙和出版物上刊載的歌謠超過330首,包括《總動員歌》《寒衣曲》《防空歌》《出征歌》《征兵歌》《送郎投軍》《殺敵小調》《霧季》《山城小唱》《抗戰八年勝利到》等。“這些歌謠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品種繁多,旋律清新優美,感染力與號召力極強”“抗戰民歌與民謠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和凝聚力,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堅定了中華民族贏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決心和信心。”[1]1
結合20世紀30—40年代的國際形勢來看,反法西斯是中外音樂界共同的主題,中國抗戰音樂的產生和流傳,構筑起近代中國音樂史上的經典豐碑。在最為艱難的條件下,重慶的音樂工作者用實際行動奏響了反法西斯的強音,創作出大量促進戰時中國對外交流的音樂作品。
二、舉辦和參與音樂會演以聲援抗戰
音樂是一種跨越語言、國家和地區的藝術表現形式。戰時重慶的音樂界常常通過開展音樂會演等具體的活動,來與國外同行互動,引發他們在反戰、救亡上的共鳴,進而開展抗戰募捐,支援前線。例如,1939年12月22—23日,中央廣播電臺的管弦樂隊應基督教學生聯合會、重慶市基督教女青年會、美以美會社交會堂之邀,與“圣誕合唱團”聯合舉行圣誕音樂大會,先后演唱2天。“圣誕合唱團”由李抱忱從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國立音樂學院、南開中學選拔優秀歌唱者約70人組成。第一天的音樂會由基督教學生聯合會主辦,目的是“為募款救濟歐洲戰區學生”。演奏曲目包括:圣誕聯曲、大提琴獨奏《匈牙利狂想曲》、小提琴獨奏《馬利亞頌》和《小夜曲》、鋼琴獨奏《搖籃曲》、混聲合唱《圣誕頌》和《哈利路亞》、管弦樂合奏《水仙花序曲》《漫游詩人》等[2]21。23日則由重慶市基督教女青年會與美以美會社交會堂發起,主辦“圣誕音樂會”,并為負傷將士募捐。李抱忱、王文杞指揮,演唱圣歌多首。其中罕得爾的《哈利路亞》等由中央廣播電臺管弦樂隊伴奏。另有金律聲指揮管弦樂合奏,黃源禮之大提琴獨奏,張洪島之小提琴獨奏,范繼森之鋼琴獨奏等。這次音樂會共募集義款4000余元[3]37。類似的音樂會演在重慶并不少見。1940年12月28日,國立中央大學基督教青年會在南開中學大禮堂主辦國際音樂大會,“參加演奏者有七、八國籍人士,我國音樂界名流馬思聰、金律聲、洪達奇諸先生均有表演。”[4]1943年9月5日,駐華美軍總部舉行音樂茶會,專為招待之前中美文化協會舉辦“美國軍人月”時宴請該部官兵聚餐的主人和陪客。同時,還決定今后每周日下午三時舉行音樂會,以便招待其他中美文化協會會員[5]。1944年6月1日,中英文化協會為響應獻金運動,在勝利大廈舉行音樂歌詠大會,請中國歌唱家斯義桂和英國歌唱家鄭鑒思等歌詠《蝴蝶夫人》等曲[6]。
值得注意的是,中華交響樂團作為一支專業音樂團體,在抗戰時期的音樂會演活動中十分活躍。1940年,中華交響樂團致函重慶市政府,請在國泰戲院舉辦每月音樂演奏會,其目的在于“供給市民高尚娛樂及藉雄壯歌聲提高大眾抗敵情緒以輔助抗建宣傳”[7]。1942年2月,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社會部民眾動員委員會及重慶市動員委員會聯合主辦了文化界國民月會,中華交響樂團受邀表演[8]。當年6月3日,中華交響樂團為慶祝成立兩周年,在嘉陵賓館舉行音樂演奏會,特邀宋慶齡、孔祥熙、孫科以及美、蘇、英大使和軍事代表團人員約300人到會。曲目有韋伯的《自由射手》、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等。音樂演奏會現場對美廣播,“收音異常清晰,十分圓滿。”[9]同年12月23日,由重慶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組織的圣誕音樂會在民眾大戲院舉行,為募集男女青年會學生公社建筑基金,組織者特邀各國使節前往,并開展百人大合唱,曲目有《彌賽亞》《圣母頌》等世界名曲18首[10]。不難看出,戰時重慶的音樂會演十分頻繁,不少會演或由中外文化組織共同發起,或邀請外賓參加,或由中外音樂家一起演奏完成,這對當時駐重慶的外國使節、記者、文藝工作者以及隨行人員等都產生了較大震撼。有些演出活動還通過國際廣播電臺對外廣播,將音符和旋律通過聲波直接傳送給外國聽眾。中外音樂界的這種互動,無疑是在同仇敵愾的語境下,為著反法西斯的勝利而得以實現的。
三、開展與國外音樂界的通信聯絡
在對外通信聯絡方面,重慶的音樂界與前蘇聯往來較多。由于中蘇文化協會發起了中蘇文化工作者的互致信函往來運動,戰時重慶的音樂界與前蘇聯同行的溝通顯得較為頻繁。《新華日報》曾對中華交響樂團與前蘇聯同行的聯絡、溝通給予了肯定,認為:“該團自成立以來,除致力于推動國內音樂運動及提高音樂水準外,復與蘇聯音樂文化界取得密切聯絡,以求溝通兩國文化。”[11]1940年9月,中華交響樂團又致信前蘇聯音樂界,向他們介紹戰時中國音樂的發展情況,告訴他們中華交響樂團的發起、成立經過和工作進展[12]。除了中華交響樂團外,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作為戰時音樂界的最大團體,也通過書信、廣播積極開展對外聯絡。1940年9月29日,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在致前蘇聯音樂界的書信中說:“現在國內的音樂機關、團體,以及刊物等,不僅在數量上比抗戰初期時多,在質的方面也比較以前進步。一般音樂工作者,雖在艱難困難的環境中,仍永遠堅韌不拔地繼續努力,這種令人敬仰的毅力,也許就是中國音樂的成功及中國抗戰勝利的基礎。”這封對前蘇聯音樂界的書信還說:“劉雪庵的《中國組曲》、賀綠汀的《晚會》、馬思聰的《塞上舞曲》《牧歌》,及陳田鶴的《夜深沉》等,各曲曾先后向貴國廣播,均兼具中國風味與西洋的技巧,為中國劃時代的新音樂作品。”[13]
此外,戰時重慶的音樂家也常常以個人名義與前蘇聯音樂家通信。1940年,作為樂團總指揮,馬思聰單獨致信前蘇聯音樂家杜納埃夫斯基、馬良、郭凡爾等人,稱:“關于中蘇文化協會所發起的(中蘇)通信運動,給了我這可欣喜的機會和你通信,我覺得非常榮幸。”馬思聰希望兩國音樂界能保持通信,經常介紹雙方音樂界的動態。同年10月23日,馬良、郭凡爾等從莫斯科回信給馬思聰,表示希望中國介紹更多的音樂組織、音樂家和作品給他們,并稱自己在創作一些關于中國的音樂作品,今后前蘇聯作曲家協會可長期向中國寄送他們的交響樂譜[14]。1940年11月29日,劉雪庵給前蘇聯作曲家協會寫信,不久劉雪庵收到回信。前蘇聯作曲家協會在信中說:“你在這信里表現了現代進步知識分子最優秀代表們的思想和感情。和我們的中國同業們一樣,我們蘇聯作曲家也深信進步力量對于反動勢力的勝利,文明對于納粹野蠻的凱旋。……你對于建立中國與前蘇聯音樂節間的密切聯系的愿望完全和我們自己的愿望一致。現在我們由蘇聯對外文化聯絡會中轉寄給一些樂譜,并渴望你也寄些給我們。”[15]毫無疑問,戰時重慶音樂界與前蘇聯同行的通信聯絡,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增加了用音樂開展反法西斯斗爭的共識,有助于形成音樂界的反法西斯戰線。
四、推介和宣傳中國反法西斯音樂
戰時重慶的音樂工作者不斷克服困難,采取各種方式積極向國外推介中國的反法西斯音樂作品。1939—1940年,國民黨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請李抱忱等人選擇一批抗戰歌曲并將其譯成英文,以利于傳播。選歌時,以“流行”與“優良”作為標準,劉雪庵、賀綠汀、陳田鶴等都參與進來,最終選定12首(見下表)。但音樂的翻譯十分講究,其文法、發音、抑揚、頓挫、節奏和旋律都要有所考慮,既要譯得得體,又要便于傳唱。李抱忱等人還請一些在渝美國、英國友人相助,才得以成稿。這些歌曲編譯后,“在香(港)印刷,在歐美各大雜志逐首刊載。從此我國抗戰歌聲,將遍傳在海外了。”[16]1944年,國民黨宣傳部又請李抱忱補充了1939年之后的抗戰歌曲10首,這“大概是因為這本集子通過介紹戰時中國歌曲創作,發揮了向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宣傳抗戰的作用,受到歡迎的緣故。”[17]45

表1 國民黨國際宣傳處向國外推介的中國抗戰歌曲信息表[18]83-85
除了從國內譯介音樂向外推送,一些音樂家還走出國門,直接到國外傳播戰時中國的反法西斯音樂。據音樂指揮家劉良模回憶,他1940年夏去美國,發現美國人雖然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但并不了解具體情況。于是,劉良模就用音樂傳播中國的抗戰聲音。最初,劉良模通過接觸美國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向美國推介《義勇軍進行曲》。保羅·羅伯遜還特意錄制了一套中國抗戰歌曲和中國民歌,唱片名字就叫《起來》[19]41。1941年3月26日,全美助華聯合總會在紐約舉行第一次助華宴會,威爾基、賽珍珠、胡適等兩千余人與會。期間,旅美華人臨時組成合唱團,由劉良模領唱了《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在全美廣播[20]。此外,劉良模還在美國各地,從商會到人民團體,從大學到中小學,不斷地講中國抗戰,并利用各種機會把中國的抗戰歌曲唱給美國民眾聽。1943年,他將《黃河大合唱》介紹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合唱團,由合唱團譯成英文,在美國傳唱[21]。另一位在美國傳播中國抗戰音樂的重要人物是王瑩。據當時與王瑩一同赴美的謝和庚回憶,1942年,蘇、美、英等國家在華盛頓召開世界青年學生代表大會,王瑩作為中國代表參加,并作了演講,演唱了《盧溝橋》。會后,王瑩又借著巡回演講的機會,到美國各地唱中國抗戰歌曲。在賽珍珠的幫助下,王瑩等人在美國創建了“中國劇團”。這個劇團由中美兩國演員參加,經常到各城市演出,大量抗戰歌曲在演出活動中得到傳播。事實上,抗戰時期,由于海外華人的努力,包括《黃河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長城謠》等在內的不少歌曲得以在異鄉傳播。例如1942年2月,緬甸華僑戰工隊在緬甸曼德勒云南會館演出,之后又到眉苗、叫脈、錫波、臘戍等城鎮進行巡回演出。《黃河大合唱》《團結起來》《黃花曲》等均被傳唱,“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并對戰后緬甸華僑愛國歌詠運動的廣泛開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22]407
隨著中國反法西斯音樂影響的擴大,一些同盟國的音樂家主動介紹、改編、演奏中國音樂。據《新華日報》載:“蘇聯名歌曲家、詩人,編譯我國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最受歡迎,蘇聯著名歌曲家克里曼蒂克基馬利夫,已將中國抗戰歌曲十五種,編制樂譜,有數種業已制成留聲機片,行銷甚廣。名曲中,最受歡迎者為《義勇軍進行曲》及《流亡曲》等,其詞意都由名詩家沙諾夫、阿爾托森等人譯為俄文。”[23]1943年9月20日,英國鋼琴家海斯在倫敦阿爾柏特大廳演奏,由布爾特爵士指揮之英國廣播公司交響樂隊伴奏。此次演奏,是克里浦斯所主持英國援華募款委員會開展的活動之一。一些中國歌曲被事先編入活動進行演奏,此外還有英國國歌,及莫扎特、貝多芬、舒曼等人作品。到會各國貴賓及聽眾約3000人[24]。此外,由于中國抗戰音樂在美國的不斷傳播,美國作曲家古爾德等將《軍民合作》等改編成交響樂。這些改編的樂曲還曾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管弦樂隊演奏,并向全美廣播[25]。可見,通過音樂交流,國外音樂界對中國戰時音樂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們譯介、改編和演奏中國音樂無疑使之具有更好的傳播效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抗戰的正義聲援。
五、引介戰時西方音樂
隨著戰時中外音樂交流的不斷推進,西方音樂實際上進一步延續了戰前對中國音樂界的影響。戰時中國音樂界對世界反法西斯音樂作了大量引介,這顯然有利于促進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國民黨對于前蘇聯音樂的引介比較積極。1939年國民黨中央電臺時常播放前蘇聯音樂,其中名家音樂包括杜納也夫斯基的《故鄉》、可列斯尼夫的《哥薩克的斯大林歌》、予拉迭利的《獻給領袖》、伊得克維赤的《前奏》、司片甲洛夫的《歌劇阿爾比斯特的進行曲》、布倫的《卻派耶夫卡牙曲》、索洛維約夫的《騎兵曲》、可瓦略夫斯基的《空軍城影的前奏》、堤可夫的《英雄組曲》、披克拉斯的《假如明日有戰事》等[26]。另外有《熱情進行曲》《鐵路工人進行曲》《共青號機關車》《怎能不唱呢》《體育進行曲》《坦克手進行曲》《雄心曲》《女力士》《騎兵進行曲》《紅海軍進行曲》等[27]。還有前蘇聯民族音樂,包括東岡民歌、三達旅進行曲、奇基茲古戀歌、民間戀歌、民間抒情曲、奇基茲進行曲、哥薩克民歌、柏爾圖魯戀歌、塔吉克戀歌、卡巴爾金古民歌、喬治亞民歌、亞治伯贊民歌、阿賽樂之萊茲更女人等[28]。與此同時,中蘇文化協會對于前蘇聯音樂的引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蘇文化協會與前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展開聯系,介紹中國音樂和音樂家給對方的同時,也在中國推送前蘇聯音樂。為此,前蘇聯方面向中國音樂界贈送音樂作品,并通過各種形式宣傳展示。1943年初,中蘇文化協會就接到前蘇聯方面運送的大量作品,有“蘇聯各民族歌劇曲譜,交響樂譜等。”[29]當然,除了介紹和播放前蘇聯音樂外,考慮到戰時重慶有不少美國人,國民政府的中央廣播電臺也于1942年12月7日開始,特設美國音樂時段,每晚播放半小時,音樂唱片由美軍司令部提供[30]。
抗戰時期,中國音樂界對提升音樂演奏技術的探索并沒有停止。中華交響樂團在成立時便將“提高我們音樂的技術理論同人民的音樂認識的水平,介紹西洋的音樂”[31]作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事實上,從樂器使用上講,抗戰時期的中華交響樂團、國立音樂學院實驗管弦樂團、國立實驗劇院實驗樂團、中央廣播電臺管弦樂隊等都是典型的受西洋音樂影響的專業組織,他們的演奏多依賴于對西方音樂器材的使用。在戰時重慶,這些音樂組織主辦或參與了眾多演出活動,其中不少曲目便是外國作品,這在客觀上是向中國聽眾直接推送西方音樂及其演奏技術。1940年11月9日,中華交響樂團在嘉陵賓館舉行音樂會演,邀請馮玉祥、孫科等兩百余人參加。此次演奏會除演奏《荒山之夜》《夜曲》《我的祖國》等作品外,還演奏了俄國音樂作品,“實為我國音樂界演奏俄國作曲家作品之綴始”[32]。1941年3月5—6日,由中華交響樂團、國立音樂學院實驗管弦樂團和實驗劇院交響樂團組成的三大管弦樂團聯袂在國泰大劇院演奏。演奏團共80余人,由吳伯超、馬思聰、鄭志聲擔任指揮。兩日演奏曲目完全相同,為9支世界名曲: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馬思聰的《思鄉曲》《塞外舞曲》、韋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美奴愛特舞曲》、羅西尼的《威廉·退爾》序曲、門德爾松的《小提琴協奏曲》、穆索爾斯基的《荒山之夜》、得法拉的《巫者弄情》。1943年,中華交響樂團“為加強民眾音樂教育,決定以后每星期舉行‘星期音樂演奏會’一次,假銀行業同仁進修社禮堂舉行,節目有貝多芬的《第一交響曲》、韋伯《自由射手》及莫扎特弦樂四重奏等名曲。”[33]當然,之所以介紹西洋音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音樂在掀起民族主義、開展反法西斯救亡運動中有著巨大作用,這實際上超出了音樂交流、借鑒本身在技術范疇上的意義,與戰時特殊的環境不無關系。
六、結 語
中國有著悠久的音樂文化傳統,但中西方音樂領域的交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并不多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由于受到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西方音樂在教會儀式、軍樂演奏、學校教學、酒吧舞廳以及家庭生活等場合不斷產生其作用,對中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漸加深,以“左翼”音樂運動為先導,一批反映救亡圖存、革命進步的歌曲不斷涌現,它們一方面將新的音樂技術、手段或特質運用其中;一方面把音樂與普通大眾的心理融合起來,具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特色。抗戰全面爆發后,音樂的發展和交流進一步延續和彰顯了這種特色,反法西斯音樂的創作和交流也更加繁榮。與此同時,受戰爭局勢的影響,大批文化人和機構紛紛內遷,近代中國音樂發展的空間版圖完全改變。此時,重慶市救亡歌詠協會、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重慶市普及民眾歌詠運動委員會、中華交響樂團、中國音樂學會等相繼在重慶創立,還有中央訓練團音樂干部訓練班、國立音樂學院等也在重慶創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音樂在堅持抗戰、爭取民族獨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4]。在對外交流中,戰時重慶的音樂界以反法西斯為主題,通過舉辦演奏會、通信聯絡、譯介作品、在國外改編和傳唱歌曲等多種方式與美、蘇、英等國同行頻頻對話,有的還走出國門,與當地音樂界和民眾互動,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這有助于宣傳中國抗戰精神,爭取國際支持,構筑文化界的國際統一戰線,同時也為推動近代中外音樂文化交流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