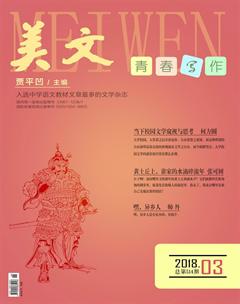泥土情深銅城記憶
在繁雜的城市中生活,吃遍了城市的地溝油食品,每天在各種電子產(chǎn)品間看得眼花繚亂。每當(dāng)靜下來卻還是深感靈魂深處的空虛,在這個不愁吃不愁穿的年代,卻依然無法填充人們精神上的貧瘠。如果有人問我最想去哪里,最想要什么?我的回答一定是一片寧靜而肥沃的黃土地。縱然只是20多歲的年紀,我的內(nèi)心卻蘊藏著一顆渴望寧靜的心靈,它渴望一方淳樸寬厚的黃土地,來放置它的不安。它也需要一處肥沃泥濘的黃土地,來灌溉它疏漏的靈魂。年歲漸長,我越來越想念那片養(yǎng)育我的黃土地。
我的家鄉(xiāng)在銅川,從地理上來說位于陜西中部,屬關(guān)中地區(qū),典型的黃土地貌、溝壑縱橫。當(dāng)很多人因為它的煤礦污染與縱橫的山川而熟知她時,在我內(nèi)心深處,她有的是獨特而溫暖的寬厚和堅強,與城市喧囂外格外寧靜的蟲鳴。小時候我的生活幾乎從未離開過黃土地,在泥土中摔倒,在泥土中爬起來,在泥土中喜怒哀樂,泥土就像我童年的搖籃,讓我感到舒適而又安全。吃飯的時候,新磨的面粉里總會充滿清新的麥香,剛下過雨的菜園里,從濕漉漉的瓜藤上扯兩根碧綠青翠的黃瓜,瓜蒂上還有未脫落的小黃花,母親嫻熟地把它們擺在案板上,只聽“砰砰砰”,再撒上榨好的蒜末,一盤“拍黃瓜”就大功告成。爽口的脆黃瓜,還夾雜著些許淡淡的泥土香;在我摔倒的時候,地上軟軟的泥土就像一雙寬厚的大手,接著我;春天的時候,黃土地蓋上一層綠油油的毛毯,其中夾雜著各類小花。一群孩子扯著一個金魚風(fēng)箏瘋似地亂跑,大家的眼睛都只關(guān)注天上的風(fēng)箏,根本顧不上看腳下的路,因為即便是摔倒了也無大礙,松軟的泥土總是那么舒適地接著落地的我們。那時的快樂真簡單,一整天一群孩子跟在一個稍大點兒的孩子后面,看他是如何放起風(fēng)箏,又是如何快速收線,在風(fēng)箏降落之前將它接住。
俗話說,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記憶中小時候在家鄉(xiāng)這句話似乎是不存在的。每年到了三月,狂野的大風(fēng)開始席卷整個黃土大地,泥土灰塵被卷起籠罩著天空,灰蒙蒙一片,偶爾還夾雜著幾只顏色鮮艷的塑料袋在空中飛舞。那時候的我還上小學(xué),不知出于某種情懷,總喜歡在大風(fēng)刮起的時候,跑到后山的山頂,看眼底蒼穹一片混亂。山下的選煤樓還在哐哧哐哧響個不停,蒸汽式的鐵皮火車鳴叫著呼嘯而過,而我只是在淺薄地感知大自然的奇妙,感受著這個城市不可言說的一種情懷與溫度。之后看《平凡的世界》,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這段童年的記憶總在我的腦海里反復(fù)浮現(xiàn),仿佛我就是那個孫少平,這種物象景觀的深刻印象也令我對孫少平多了一份認識與理解。而今想來,不論是我的童年,還是孫少平的童年,雖然都已經(jīng)在記憶里逐漸模糊,但是它們卻像那個年代的標(biāo)志一樣,永遠駐守在屬于它們的時代里,為我固守內(nèi)心的一份感動。
那一年,從我兒時起就高高佇立的那座選煤樓倒下了,被夷為平地,再也聽不到哐哧哐哧的聲音。呼哧呼哧的蒸汽火車也不見了,一條條水泥路鋪了起來,樓房多了起來,綠化帶也蜿蜒在城市的每條馬路邊。當(dāng)我終于明白過來的時候,一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20世紀就在這些悄然的變化中向我們說再見,而我卻全然不知。我喝水的水壺上依然寫著“1997”,畫著紫荊花,我?guī)е@個水壺在這個慌亂的時代,乘著時代的快車走進了21世紀。我來不及說再見,來不及給果園的蘋果樹說再見,看它們被連根拔起;來不及給黃土地說再見,走進了所謂的小康新農(nóng)村,條條水泥路通門口;來不及給童年的風(fēng)箏說再見,失去了風(fēng)箏也失去了童年的自由;來不及給山腰里的酸棗樹說再見,它們曾是我最美味的零食。再見了,他們說21世紀是那么美好,是多少人日日夜夜念想?yún)s終究沒能跨過來的時代。
恍惚如夢初醒,滿街的水泥路,突然看到前方有一條蜿蜒的小土路,興奮地跑過去,踩在上面軟軟的,微潮的小路散發(fā)著泥土的清香,仿佛剎那忘記世間繁雜,獨自沉浸于自己的桃花源,平靜又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