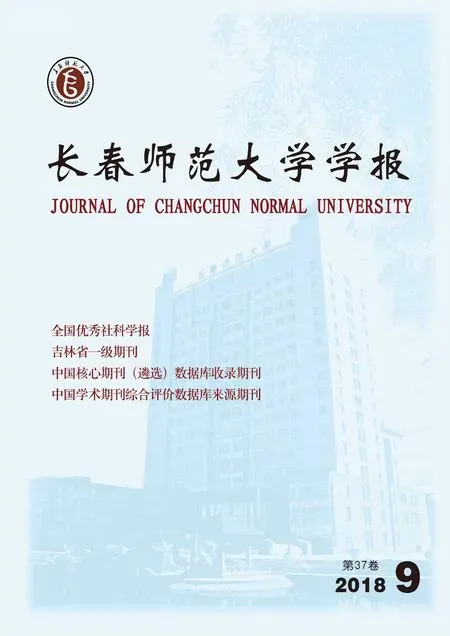生態哲學視域下的綠色構建:生活方式與發展范式
劉 旭
(菏澤市委黨校,山東 菏澤 27403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綠色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人民幸福、國家興旺、民族振興的重大戰略任務。就其發展要義而言,生態文明是以均衡發展、節約發展、循環發展、全面發展為基本宗旨的社會形態。構建這種社會形態必須首先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充分認識綠色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轉變綠色發展模式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發展范式上持續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逐步推進產業結構、空間結構、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與此同時,堅持綠色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還必須解決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加快構筑尊崇自然的生態體系,謀求環境質量效益,讓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成為主流的社會形式,引導大眾形成正確的出行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使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空氣常新,讓人民群眾在良好生活環境中生產生活,為子孫后代留下一片藍天。
一、作為發展范式的文明形態
美國社會學家曾經提出過“三次浪潮”的概念,即從發展角度對世界意識形態進行劃分,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這三種文明分別對應不同的發展方式。在農業文明下,由于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相對低下,生產方式必然以刀耕火種為主。在這種勞動趨向中,追求經驗傳統和物質積累成為時代的主要特征。與此相適應,對生活目標的追求也主要以自我生存的滿足為限,任何脫離這種現實的幻想都被認為不合時宜而遭擯棄。到了工業時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極大改變,大工業生產和新科學技術革命的到來使過去認為不可想象的目標變成了現實,這極大激發了人類的勇氣和自信,使人類在倍受鼓舞的同時也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世界圖像。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理性脫穎而出,并因在改造世界中所展現的巨大力量而受到普遍歡迎和認可,工具理性一時成為人類最重要的改造手段,并依靠它的出色發揮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人類奇跡。但人類在得到充分滿足的同時,也愈發認識到毫無節制的物欲消耗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大自然正在經歷著不可承受的污染之重。在人類精神世界方面,良好的生活在單向度的發展中似乎與我們最初的設想漸行漸遠,異化像無形的幽靈一樣時刻纏繞著現代人的精神家園,使他們在漂泊不定中尋尋覓覓,又在東奔西尋中變得意志消沉、情緒低落。這就是工業文明的特點:改造與反抗并存,異化與糾纏并在。與工業文明崇尚工具理性、過度依賴人類中心主義不同,生態文明從人與自然的雙向角度出發,在追求自我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目標下,大力提倡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榮共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工業文明是現代性的,而生態文明是后現代性的。當然,生態文明對工業文明的“撥亂反正”并不意味著對一切現代性成果的否定,生態文明仍然強調發展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意義,仍然以人類的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旨歸。它只是跳出了人類原有的視域,將自然的內在價值納入改造思維,基于更廣泛的基礎,實現社會發展理念的突破。從哲學意義上來看,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揚棄,而不是完全的拋棄,它繼承了工業文明的發展目標,卻拒絕了工業文明實現目標的方式。所以,生態文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新形態,體現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
二、發展理念與生活方式的統一
生態文明的提出切合時代的發展需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這一發展綱要說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變革、產業結構的調整、增長方式的改變,還應包括生活方式的重塑。這是第一次將生活方式和發展理念統一在文明形態的建構上。因為現代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消費的拉動,消費在推動經濟增長、調整市場供給方面具有重大的引領作用,而且消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后者的變化對構建新文明形態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塑作用。以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為例,兩者其實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構建生態文明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必要前提,沒有生態文明的引領,就不會有綠色發展理念的產生,反之亦然。這種邏輯關系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為無論是生態文明還是綠色發展,最終都要落實到人的發展上,都要落實到人的具體生活層面上。這樣一種關系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即社會研究必須放在人類歷史發展維度下開展。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現代化建設的快速階段,我們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些機制體制的弊病。以發展理念為例,我們一直秉持支配自然的觀念,將大自然作為改造的客體和對象,想盡一切辦法,盡其一切能事使自然臣服于人類。雖然這種發展使人類從自然的盲目崇拜中擺脫出來,但這種發展的片面性也使現代人患上了物質依賴癥,喪失了人的自由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如不及時校正發展方向,就有可能使社會發展陷入停滯,最終演變為一場發展危機。這也正是造成生態危機乃至人的生存和發展困境的根本所在。
三、現代生活方式的內在邏輯缺陷
現代性生活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迷信科技力量,過分依靠工具理性,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這種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生活方式必然是單向度的生活,即人對自然無限支配和改造的想象。但知識是一把雙刃劍,在人類尚不能完全控制自然的情況下,過度的改造勢必會引起過度的報復。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告誡我們的一樣,“不要過分地陶醉于我們人類對于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會對我們進行報復。”[1]據《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6)顯示,全國超過68%的河流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812個市(縣)級城市土壤污染嚴重,每年城市傾倒的固體垃圾多達8.2億噸,足可繞地球三圈;東北地區、華北地區全年霧霾天數平均多達87天,約占全年的四分之一。面對這些環境危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現有生活方式開始反思,對我們過度的物欲膨脹和惡性消費開始有所覺醒,對資本快速擴張所帶來的重復生產和科技革命所導致的工具主義的泛濫也開始有所省悟。雖然現代生活方式仍然是眾人追求的目標,但不可否認,很多人對它的態度已發生了重大改變,從以前的盲目崇拜、一心謳歌轉成了冷靜的審視乃至尖銳的批判。[2]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上:一是過于凸顯的人類中心主義。現代性預設了這樣一種前提,即將人類作為世界的主宰,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生物無非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存在,或者為了人的需要隨時隨地可以作出犧牲。這種價值判斷忽視了自然的內在價值,只看到了人的需要。二是消費主義盛行。將人生意義完全等同于對物質的占有和對財富的追求,信奉消費至上,不斷追求時尚潮流,強調消費能力決定生活品質和人生高度。從哲學角度來看,這種生活方式的內在邏輯依然是主客二分的,物質對于人來說仍然是占有與被占有、改造與被改造、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在這種關系視域下,單向度的生活必然會對多元文化產生沖擊,同質性追求也會扼殺社會思維的活躍性,權威、整齊劃一成為時代的關鍵詞,順從則成為一個人必備的素質,甚至被說成優良美德。人不得不被同一性鉗制住自由全面發展的可能,束縛于精神的牢籠而動彈不得。[3]這種同一性是對現代人類的最大戕害,要突破它的思維局限就必須從生活上突破主客二分、物我有別的哲學分野,徹底實現人類生活理念的轉變。
四、生活方式變革的實質是人的發展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生活方式作為人類實踐的基本形式,被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生產關系的變革或社會形態的更迭,實質上是人的生活方式亦即人的存在方式的變遷。[4]這一哲學觀點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人的存在方式與眾不同。自然界除人之外的一切生物,其存在方式都是預存性的,即本質規定在原因和結果中包含的一樣多。以種子為例,一顆種子包含了成為大樹的所有規定性,唯一不同的是種子是潛在的,大樹是顯現的。也就是說,人之外的一切生物都是本質先于存在的。但人不一樣,人是在不斷實踐中確證自己的,是通過生活來拓展自我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技能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人是存在先于本質的,而這種存在就是現實生活過程。因此,如何生活、怎樣生活體現了人的基本存在。二是生產與生活的變革具有同步性。在馬克思語境中,作為現實主體的人總是處在活生生的社會關系中,生產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其主體仍然是現實中的人,主體的一致性意味著變革的同步性。一個人怎樣生活與其發展息息相關,有什么樣的發展就有什么樣的生活。同樣,什么樣的生活也反映了什么樣的發展。一言概之,生活方式與發展方式具有同步性,生活方式是生產發展的直觀體現。譬如,在工業社會中,人的生活主要依靠能源來維持,而工業社會的發展以蒸汽機和發電機為標志,這兩個都是能量的裝換裝置。同樣,當代社會主要以信息產業作為發展方向。與此相適應,我們日常生活交流也都以信息為主。由此看見,生活方式與社會發展在主體和內容上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和一致性。
綜合上述兩種觀點,人存在具有先天的特殊性,同時,人的生活方式與發展狀況具有同步性。人的特殊性要求人超越自我規定和活動范圍的局限,通過不斷實踐來確證自身。另一方面,同步性要求人的發展必須依賴社會的總體進步,必須將人的發展與人類整體文明相結合,通過社會的總體變革引領個人的自由發展。縱觀歷史,人類每一次進步都體現了自身的進步,體現了對束縛的解放、對自由的發展、對自我的肯定。以近代歐洲思想家為例,他們以理性為口號,在“我思故我在”和“知識就是力量”這兩面旗幟下,開啟了新時代思想啟蒙運動。前者否定了上帝,重新樹立了人的存在;后者則肯定了理性力量的偉大,造就了以物質交換為基礎的社會繁榮,并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所以,資本主義社會是人發展的歷史性契機,使人的個性得到了最好的延伸。但我們也要說,這種發展總體上是畸形、片面的,特別是物化意識對人的影響成為現代社會普遍異化的根源。
五、物化意識是人發展片面性的根源
如上所述,人的本質存在必須通過對象化活動來加以確證,勞動產品作為人的對象化產物,必然是人本質的體現。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人不僅存在著被自己勞動產品異化的可能,也存在著與他人相互異化的可能。這樣一來,勞動產品成為終極目標,占有勞動產品則被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人與人之間關系變成了簡單的物化關系,人類活動也變成了簡單化的物化活動。與物化關系、物化活動同時產生的則是物化意識。作為一種意識狀態,它已經內化于人的思想之中,并以其強大的控制力驅使思想結構同化為物質結構,使之成為人必須遵循和服從的東西。在這種強烈意識支配下,重物質占有便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就是拜物教產生的歷史根源,也是人片面發展的思想原點。因為把物質占有看得高于一切,實際上就等于扼殺了其他方的人性需求,把發展的全面性給忽略掉了,從而成為單向度的人。所以,馬克思說:“只有當社會進入自由人聯合體,物質生產過程成為人的自主活動,才會揭掉勞動產品的神秘面紗,從而終結拜物教。”[4]
另一方面,重物質占有必然導致享樂主義,享樂主義既是人片面發展的極端化證明,也是物化意識的具體呈現,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徹底物化。以當今中國消費為例,據加拿大皇家銀行(RBC Europe LTD)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消費者為歐洲奢侈品牌的銷售貢獻了35%的比重,Chanel、Gucci、LV等一些國際知名品牌仍是中國消費者的最愛。這種奢侈之風與當前社會盛行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遙相呼應,直觀揭示了中國人對物質占有的迷戀,以及通過物質占有來體現人生理念的價值扭曲。正如前述所言,消費問題不單是生活方式的問題,而且與人的獨立自由和全面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生活方式的變革必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把消費作為最基本、最原初的變革點,也必將為生活方式的變革提供內在動力和根本目標。綠色生活就是這一理念變革的產物,它的實質就是要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過去以高消費、高消耗為主的消費方式勢必要讓位于健康、適度的消費模式,并通過這種消費方式的引導和促進生產方式的變革,調整產業經濟結構,建設生態文明體系。
六、新時代與后現代的理念差異
有學者認為,新時代生活方式內在機理仍然是現代性的,而打破這一結構性弊端的最好途徑就是從現代性轉變為后現代性。后現代性用詩意取代了理性,用碎片化取代了中心化,用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取代了冰冷的宏大敘事。福柯曾說:“人們為什么將一張桌子、一棵樹當作藝術對象,而卻不把生活本身當成藝術對象。”通過他的話不難理解,生活方式及其生活態度的轉變是破除現代性的最好起點,是突破自我約束和自我封鎖的最佳方式。[5]但這是否意味著可以把“新時代”理解為“后現代”?筆者覺得兩者還是不同的。其實,后現代在對現代性猛烈沖擊的同時,也毫無保留地把世界圖式撕得粉碎,從而使世界歷史走向了虛無。無論現代性還是后現代性,都無法跳出線性思維的窠臼,也無法規避因主客兩分而產生的世界認知方式以及橫亙在上面的巨大思想鴻溝。正因為如此,后現代性在批評現代性自身缺陷的同時,也暴露出了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我們的“新時代”則有所不同,它并不像大多數后現代主義者想象的那樣,一味強調去除人類中心主義,見到“現代性”的東西就反,見到所謂文明成果就視為古董而棄如敝履。其實,任何生活方式都是人的生活方式,無論是現代人對健康、時尚、環境的苛刻追求,還是對生活品質的高標準嚴要求,歸根結底都反映了人的訴求和偏好,映射了人的需要和沖動,這是人與世界關系中始終伴隨、揮之不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世界歷史就人類存在和主宰世界的歷史。因此,任何試圖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的作法都無異于癡人說夢,至少從這一點來看,現代性預設有一點是正確的,就是文明的價值是人所賦予的,任何脫離人的評判或與人無涉的自然平衡都是荒謬的自欺欺人。后現代者就是在這一點上犯下了錯誤,一味地強調自然的自為自主性。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使得他們固執地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要么是以人的勝利而告終,人在對自然無節制的改造和滿足中實現對自我能力的確證;要么是毫無余地將人類欲望斬除殆盡,從工具理性的霸權中抽逃出來,走向歷史的反面。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透露出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思想傳統。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思維方式正是現代性的杰作,后現代主義者用一種現代性的方式來反駁現代性,這恰恰說明了后現代性的自欺和虛偽。
其實就解決方案而論,中國傳統智慧中的“天人合一”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解決方案。這種“和合”思想反映在生活層面,就是追求一種和而不同的處事原則,它主張包容、共生、以己度人,卻又拒絕物我兩分、人我有別。這種形式融合既消解了現代性所造成的主客分離的窘境,又拒絕了后現代性者簡單地將人加以拋棄的虛妄作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人合一”思想接受了后代性的變革目標,卻拒絕了后現代主義者實現目標的手段。可以說,它是對后現代性的一種揚棄而不是拋棄,這正是新時代與后現代理念的差異。
七、傳統智慧對綠色生活的啟示
“天人合一”的思想蘊含著古代中國人對生態文明的深刻思考,集中體現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中。莊子說過:“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齊物論》)人與自然萬物變成了對象化的改造關系,有了主體,自然也就有了客體,有了自我意識,同時也開始了異化,與物的對立意識也產生了。這樣一來,原本渾然一體的狀態不復存在,剩下的僅有人的欲望和被重新理解的是非偏私。莊子認識到人類“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繕性》),人們因為“物”而喪失自然本性,導致“與物相刃相靡”(《齊物論》),出現相互戕害、爭奪、欺詐等種種罪惡與異化。所以,莊子提出一條人類擺脫困境的途徑,就是恢復人的自然本性以及人與天地的自然和諧。可以說,莊子是從人的生命這個人本主義角度來關注自然的,是從人自身的發展角度來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這就是獨特的東方智慧。
事實上,東方智慧對和諧的追求體現在三個層次:社會發展的自然方式、生活方式的道德文明、人類內心世界的天人合一,從生活、生產、生存三個層面上來體現人的本心本性,通過人本質的回歸來化解人與自然的對立。筆者認為,這恰恰為現代生活跳出歷史困境提供了一副良藥。眾所周知,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有一種重新回到人存在上的沖動,我們稱之為“存在論”的轉向。為什么要回到人的存在上來?就是要解決人的本質異化問題。強加在人身上的枷鎖不僅有肉體的痛苦,還有精神的游離。阻礙人類行動的不光有腳下的羈絆,還有來自內心的恐懼。那些早已習慣現代生活方式的人,對任何改變都麻木不仁,少有膽量和勇氣去嘗試,哪怕是輕微的吶喊也少得可憐。在他們看來,現代生活方式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工業文明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文明形式,任何試圖顛覆、改變現狀的人都應該被無情批判。這種責任感的缺失與其說是過度物化的后遺癥,不如說是面對未知世界的內心恐懼。其實,現代生活方式的華麗外表下已經布滿了千瘡百孔,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也不愿撕去那件“皇帝的外衣”,因為現代生活不僅帶給了他們富足的物質和便利的消費,還有那羈絆人們勇往無前的腳鐐和枷鎖。所以,要為現代生活方式尋找出路,恢復人類對生態文明的理念共識,就必須跳出傳統西方世界的思維方式,從中國傳統智慧中汲取精華,從“天人合一”的思想中錘煉出適合現代發展的綠色理念和生活態度,從而為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