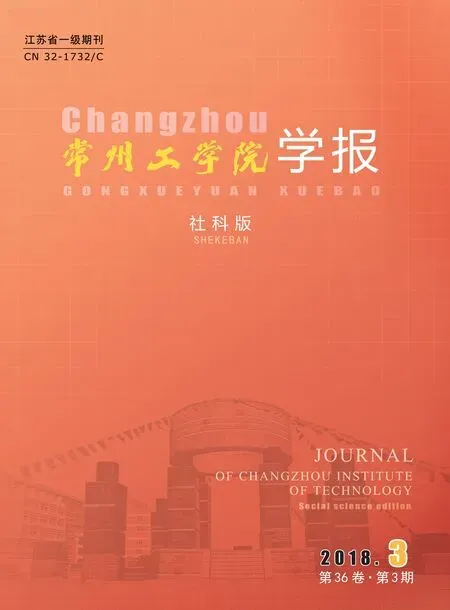“世界華文文學”教學改革探析
計紅芳
(常熟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江蘇 常熟 215500)
2017年“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好事甚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了大豐收,其中重點項目1項,一般項目7項,青年項目2項,西部項目1項;另外,比較文學領域的華裔文學研究獲得了4項!雖說是“世界華文文學”方向,但選題涵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如:兩岸新生代作家比較,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抗日敘事和民族創傷記憶研究,21世紀華裔美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等等。從這些新的動向可以看出當今國家層面的學術平臺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的高度重視以及他們宏闊的視野。不僅如此,這一領域國家基金項目的大豐收給一直在教學和研究第一線的筆者極大的鼓舞,更加堅定了在學校中文師范專業開設“世界華文文學”這門課程的信心。但是如何在有限的課堂教學空間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對于任何一個教師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一、自覺開放的學科意識和宏闊視野
所謂“世界華文文學”,一般來說是指臺港澳暨海外的華人作家、以漢語作為書寫表達工具而創作出來的文學。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經過了近40年的發展,經歷了命名的探討、對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的確定、世界各地區華文文學發展歷史和區域性特征的探索、海外華文作家文化身份的建構、對如何編撰世界華文文學史的研討,乃至對“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歷史的描述和學科理論的建設,取得了累累碩果。世界華文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基本同步,成績也不凡,可是和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二級學科相比,“世界華文文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但也正因為“新”,一方面招致“大家”的質疑和不待見,另一方面它卻具有越來越旺盛的生命力和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長期以來,“世界華文文學”(也即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一直是包含在二級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世界華文文學”碩士、博士招生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向。有感于“世界華文文學”的蓬勃發展和巨大的學術研究潛力,2003年2月,南京大學的中青年學者劉俊教授代表專業和學科,向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申報和陳述,申請設置“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學科點,順利獲得通過,這是國內第一個“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意義非凡!從此,在南京大學“世界華文文學”不再附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而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了。南京大學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方面雖然沒有暨南大學、汕頭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范大學等南方高校起步早,但是在二級學科學位授予點上走在了前列,從2003年至今,該二級學科博士點已經培養了數量頗為可觀的博士生,他們如今在各大高校或科研機構逐步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新生力量。2012年9月,該學科點開始培養“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后。2013年5月,“南京大學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正式掛牌并開始運作,至今已經舉辦了很多重要的學術活動,影響深遠。這些都說明了全國范圍內的世界華文文學二級學科的建立為期不遠了。
再者,世界華文文學的跨區域、跨文化特點越來越受到比較文學學科的關注。1996 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的總結發言中曾預言,海外華文文學是比較文學將要去拓展的新領域。時隔3年,在1999 年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六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外華人文學的研討成為會議的一個熱點,之后歷屆年會都十分重視海外華人文學的研究。2011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比較文學學科的高層不僅把“世界華文文學”納入他們的視野,設置了“流散文學與海外華人文學”等議題,而且還邀請了大量“世界華文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共同探討這一議題,筆者有幸受邀參加,印象深刻。他們的這一行為本身不僅說明了“世界華文文學”具有跨學科、跨文化的重要特點,它能拓展比較文學的新領域,而且也證明了“世界華文文學”越來越受到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其實,不僅是比較文學領域,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也有很多學者自覺地把嚴歌苓、虹影、張翎等海外文學大家列入研究和教學觀照的范圍,甚至有些學者認為,不僅是臺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陳思和在2016年第一屆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上的總結發言中明確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說:“我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中國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種原因出國了,他們的創作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就像當年郁達夫、郭沫若他們的創作一樣。”①在陳思和的學術框架中,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或者比較文學的一部分。當今為數不少的學者認同陳思和的看法,筆者也特別贊同他的觀點,這是一個有膽識、有遠見、有視野的大學者經過對中國新文學(某種意義上也即中國現當代文學)長期深入研究思考得出的結論。在當今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課堂教學中,許地山描寫印度生活風情的《綴網勞蛛》、白先勇描寫美國留學生生活的《芝加哥之死》、嚴歌苓描寫大陸戰爭年代弱者生存的《小姨多鶴》等等大多進入主講老師的授課范圍,我們有什么理由壁壘分明地把現當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區別開來,各自劃定勢力范圍,有時甚至進行非善意的學術爭論呢?更何況,像嚴歌苓、張翎、虹影等在海外新移民文學領域影響巨大的作家,他們的一半時間在大陸,很多創作題材也是關于大陸的,我們如何把她們的創作和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當代文學區別開來呢?
延伸到“世界華文文學”在大學中文師范教育的課程設置,我們應該逐漸擯棄把它看作可有可無的選修課的做法,而應該像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那樣把它作為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同一級別的必修課來設置。這門課程的任務是使學生通過老師傳授和學生自學討論,了解世界華文文學在臺灣、香港、澳門各地區以及海外各地的生存狀態,掌握完整、立體的世界華文文學版圖,培養學生對全球范圍內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審美鑒賞能力、宏觀和微觀的綜合考察和比較的研究能力,來共同傳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如果我們有了自覺開放的學科意識,那么目標的實現就為期不遠了。
二、講授研討與小組匯報相結合的授課方式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雖然只有近40年,但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涵蓋了臺港澳地區的新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內容如此龐大的“世界華文文學”要在一個學期32課時的課程設置中完成有相當大的難度。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有選擇性的講授,其余靠學生自學,并且要在網絡教學平臺上進行師生互動探討。課堂講授方面,筆者所采取的方案是面與點的結合:“面”就是世界華文文學幾大文學板塊的史的梳理,如臺港澳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歐美澳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等;“點”就是對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專題教學,如設置鄉土小說的旗手——陳映真,現代派小說的代表——白先勇,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余光中,意識流小說的先驅——劉以鬯,迷墻內的抒情圣手——陶然,詭異言情小說家——李碧華,馬來西亞微型小說代表——朵拉,泰國“小詩磨坊”的召集人——曾心,新移民文學三駕馬車——嚴歌苓、張翎、虹影等教學專題。
在實際講授過程中,一般采取講授和討論相結合的方法。“世界華文文學”到目前為止是針對中文師范專業高年級的選修課,學生們已經有了比較堅實的理論功底和現當代文學專業知識,學習世界華文文學就不再滿足于老師在課堂上侃侃而談,而是希望能與老師在同一平臺上對話,這對老師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開學之初,筆者就會把要講授的專題作家告訴學生,讓他們按照教學進度提前1~2周做好準備,參與課堂教學討論。其次,給學生分組,采用自選和老師最后審定相結合的辦法,設置一些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和作家進行小組PPT課堂匯報,一方面鍛煉學生制作PPT的能力、提高課堂教學的技巧,同時也作為本門課程的考核內容。比如:學生們開展了鄭愁予、席慕蓉、李昂、瓊瑤、金庸、趙淑俠、譚恩美、曹桂林、嚴歌苓、張翎、虹影、余澤民等作家作品的小組合作匯報展示,經過多次實踐,筆者發現這樣的課堂教學效果相當不錯,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研究興趣,也能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合作能力。長此以往,就會有一批又一批摯愛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生,畢業后他們或做教師,或進一步深造,或在其他崗位工作,他們再以自己的興趣和行動影響別人,如此一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肯定后繼有人。
三、圖像時代多媒體手段的綜合運用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日新月異,教學中運用各種多媒體手段已經成為教師的必備技能,但是真正能熟練并得心應手運用的恐怕還不多。一方面是教師自身多媒體課件制作學習與更新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與學校自身的軟硬件設備跟不上以及和學生自身的素質也有極大關系。未來教室、虛擬學校等等在目前以及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常熟理工學院很難實現,我們可以做的是把相關的音視頻教學資料、參考資料等放到畢博網絡教學平臺,供學生預習、復習、測試,并提供師生課外互動平臺、小組討論空間等以彌補課堂教學課時有限所造成的內容含量的不足。
另外,中文師范專業是在應用型本科院校框架中僅存的幾個師范專業之一,屬于本二層次,學生不可能有像“985”或者“211”高校學生那樣擁有較高素質和旺盛的求知欲,教師的教學目標也不是培養學術性研究人才,而主要是培養中小學教師。因此,認清楚這個目標對教師的課堂教學設置與安排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教師不能像作學術報告那樣只展示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看法,而必須師生互動,共同探討。然而,在當今浮躁的讀圖時代,已經很少有人甘坐冷板凳去研讀一部部文學作品,特別是那些長篇巨作,而由作品改編的電影、電視劇等由于能夠帶給觀眾感性、直接的視覺形象沖擊卻很受學生喜歡,《北京人在紐約》《少女小漁》《小姨多鶴》《喜福會》《金陵十三釵》《上海王》《刮痧》《推手》《唐山大地震》等等由于其豐厚的跨文化內涵、激烈的文化沖突、對人性的思考、對終極價值的追尋等等吸引著學生的眼球,有些甚至促使學生去尋找相關文學作品作進一步深度閱讀和思考,從而使得影像的文化性、視覺性和文學作品的審美性、文學性有機結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這些教學過程中的點滴經驗激發筆者在文學作品的教學過程中,常常配以精彩的影視片段進行輔助教學,這樣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在指導學生做小組專題匯報的時候,也要求他們圖文并茂,配合音視頻材料。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在選擇影視材料片段的時候,要注意文學經典、社會熱點和學生興趣的結合。對于那些作品改編成影視劇較多的作家,在選擇重點影視材料片段進行教學的時候,可以運用一些編輯軟件比如“愛剪輯”等進行重新編輯處理,使課堂教學緊湊而又有活力。
正如艾爾雅維茨所說,“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自身在當今都已處于視覺成為現實主導形式的社會”②。因此,運用必要的影視手段進行多媒體教學,能夠給“世界華文文學”教學增添光彩。
但是必須牢記的是,文學的教學以文本欣賞為主,影視片段只是輔助手段,而且兩者本身不屬于一個范疇,前者是文學范疇,后者則屬于藝術范疇,為了獲得好的市場效果,很多影視作品會對原著進行改編和刪減,兩者往往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教師在插入影像資料進行輔助教學的時候,一定要回到原著本身進行審美范疇的欣賞與品味,這樣才能實現文本與影像的互補提升。
總之,“世界華文文學”的教學任重道遠,課堂教學的改革需要教師具有自覺開放的學科意識和宏闊視野,pan>擺脫把課堂當作學術講座的教學模式,采取講授研討與小組匯報相結合的授課方式,并在可能的情況下綜合運用圖像化的多媒體手段,以保證課堂教學的高質量和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注釋:
①陳思和:《華文文學流轉的空間——2016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總結發言》, http://mp.weixin.qq.com/s/3SEjTFNDMB1lL_XaguWO_g ,2017-03-02。
② 阿萊斯·艾爾雅維茨:《圖像時代》,胡菊蘭、張云鵬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頁。